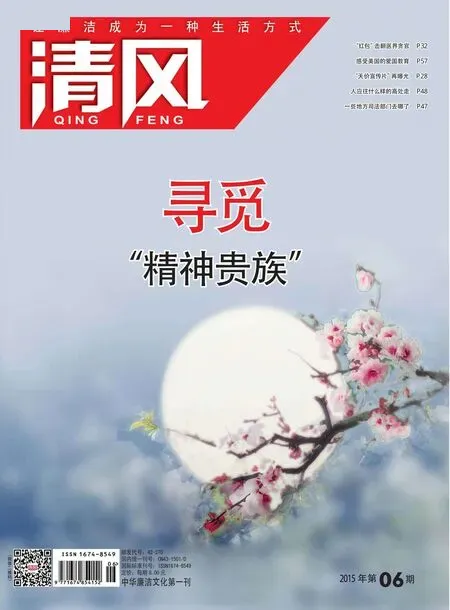“美”是由內到外的精神氣質
文_本刊記者
“美”是由內到外的精神氣質
文_本刊記者
一直以來,從事美學創作的人,對于精神氣質的追求有種超乎尋常的狂熱,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對于自然美、心靈美的發現與揭示,使得這個群體有種優雅質樸、高貴圣潔的文人情懷。他們熱衷美,尋找美,塑造美,用美中散發的精神氣質影響人,感化人,陶冶人。他們是實至名歸的“精神貴族”。
繪畫是修身的法門之一
“傳統知識分子的理念是廣泛學習研究傳統文化,以士志于道的標準要求自己。”

身為齊白石門下弟子,王廣然對國畫藝術有異乎尋常的偏愛,也正是這種異常的偏愛,使得他在國畫藝術創作中非常投入,獲得業界諸多認可。同時,作為中國國畫創作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名人名家書畫院院長、中國國畫藝術創作研究院名譽院長的他并沒有因此而滿足,他將國畫藝術與中國傳統的風水學理論體系和道家、儒家、釋家思想結合起來,開創了“會意水墨畫”“中國風水禪意畫”,并因此被業界熟知。
“作品的創作過程,對于創作者來說既是精神氣質的塑造過程,也是藝術的再創作與提高過程,對此我深有體會。”王廣然告訴本刊記者,他的會意水墨畫和中國風水禪意畫傳達的既是一種博愛與普度的情懷,也是一種和諧的理念;更是一種物與環境共生的理念,它告誡人要關愛生存環境,關愛那些同樣具有思想和情感的生靈,達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共存、共處目的。
長期的國畫創作使王廣然深刻地領會到,單憑個人的想象力和實際操作力是遠遠不夠的,傳統藝術在創作之前需要創作者具備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比如具備儒釋道經典理論和思想以及現代土木工程建設等諸多要素與素材。同時,傳統藝術的氣質還需依托毛筆、宣紙以及水墨等多種元素的結合,進而從整體上展現創作者的精神境界。
王廣然告訴本刊記者,“傳統知識分子的理念是廣泛學習研究傳統文化,以士志于道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國畫的創作過程中也不例外,亦即繼承前人國畫創作經驗,通過臨摹提高自身的能量,再通過寫生完成創新,通過自身的文化修養為作品注入內涵,影響外界。
“繪畫不只是藝術,更是修心。”在平時的生活和藝術創作中,王廣然除了注重提升技法之外,他還特別注重自身文化修養,通過長期“參禪”,悟出了自己的“禪”,因此,他開創了“中國風水禪意畫”。王廣然喜歡“參禪”,也具有了“禪心”,生發了“禪意”,他本身就是一個畫家,所以他成了名副其實的“禪畫家”。他習慣于將國畫與音樂、儒釋道經典思想等相結合,進而從中感知國畫的優雅和高貴。
作為一名具有社會責任擔當和傳統價值追求的藝術人,王廣然說:“藝術人應具有良好的傳統美德和為中華民族文化發展與國家復興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通過多年的廣泛學習和研究,王廣然將國學中對人格美的詮釋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來,在他看來,一個人的文化底蘊與修為,集中表現為人文關懷,而繪畫就屬于這種人文關懷的外在表現形式之一,這也是國畫的價值所在。
做傳統文化的捍衛者
中國美學學會副會長,東南大學教授張道一在評價蔡曉嵐時說:“將花窗搶救出來是別具慧眼的,留住了蘇州之窗,也開啟了蘇州之窗。”

一個人的選擇與其說取決于外界客觀因素的合力,倒不如說是自身性格與文化素養使然。蘇式花窗博物館館長、收藏家蔡曉嵐就是如此,數十年前的一個決定使他成為蘇州當地收藏界的新寵。“當時由于蘇州城市的發展需要,老民宅的大量拆遷使相當一部分的明清家具、古典門窗日漸流失。”蔡曉嵐告訴記者。
擁有文人氣質的古豐閣主人蔡曉嵐在目睹文化遺產日漸流失的慘狀之后,他決心投身于蘇式花窗的收藏和保護。據他回憶,通過日積月累,走街串巷,他付出了大量的汗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財力。至今古豐閣已收藏了各種款式的明清家具共千余件,古典門窗三千余扇,蔡曉嵐也因此成為收藏明清家具和蘇式花窗的國內第一人。中國美學學會副會長,東南大學教授張道一在評價蔡曉嵐時說:“(蔡曉嵐)將花窗搶救出來是別具慧眼的,留住了蘇州之窗,也開啟了蘇州之窗。”
蔡曉嵐坦言,收集的花窗越來越多,修得也越來越多,而場地、資金的問題也接踵而來,這困擾了他十多年,但他堅守著自己的信念——保護傳統文化,不讓文化出現斷層。在他看來,蘇式花窗藝術背后是古人精致優雅的審美文化,這也是時下浸泡在忙碌商業文化中的人們所缺少的,“我想守住這片凈土。”他說。
蔡曉嵐立志要將蘇州古豐閣打造成為蘇式花窗的傳承創新企業。他也明白傳承必須靠人,靠專業技術人員,為此,他還請來了孫成祿、邱鴻明兩位非遺傳承人。孫成祿于新中國成立前開始學木工手藝,幾十年木匠活沒問題,蔡曉嵐三顧茅廬,懷瑞保護蘇州傳統老手藝的誠意,才打動他出山,“如今86歲的他,已在古豐閣從事木工、漆工工作20余年。”
蔡曉嵐認為,蘇式花窗透出了很多文化、人文的信息,它的存在不僅僅只是一個透亮的功能,更是一種精致優雅的文化。“為什么蘇作工藝全國聞名?為什么蘇幫工匠能到北京去造故宮?就在它的精致。而當你和它打了十多年交道之后,你就會和它有了感情。”蔡曉嵐笑著說。他的生活已經不知不覺地融入花窗里面去了,花窗之美也由此與他結下不解之緣。
作為收藏家,蔡曉嵐收藏有中國最美的花窗,但不僅是收,他還研究。他表示,在此過往中他已經覺得自己的身份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轉變,原來在經營古玩生意的時候是別人出了大價他就要賣掉這些古玩,現在出再大的價錢他也不賣了。“那么多藝人的堅守,使他們的這份手藝能傳到我們的手上,如果我們不好好地去堅守,那這些優秀傳統文化可能就會斷送在我們這代人手上。我也希望今后的蘇州人能把堅守的精神發揚光大。”
在蔡曉嵐看來,一個人到這個世上來走一遭總要做點有意義的事,他只想留住蘇州的一些傳統文化。“從目前來看這些花窗是我的,但從長遠來講,這并不是我個人的,它是全世界全人類的,我僅僅是在這個時代當了一個臨時的保管者而已。”
藝術不止是追求視覺美
“在藝術中,我試圖通過真善美以及佛教中所講的因果輪回來啟發人對生活的重新審視。”

“畫筆再現真善美,寫出人間好春光。”這是外界對高級工藝美術師,湖南省陶瓷藝術大師許石斌創作風格的稱贊。許石斌自幼喜愛書畫,擅長油畫、雕塑。中國書畫大學國畫系畢業的他曾任美術教師,后由于對陶瓷藝術的鐘愛,1992年赴景德鎮從事陶瓷藝術設計繪畫數年,此間深受陶瓷世家余子富、馮通亮等前輩大師指點,并由此成為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研究院院士、景德鎮古窯名人畫院院士。
他將二十余年書畫功底與陶瓷藝術很好地結合起來,一直專攻花鳥、人物,在陶瓷創作中力求作品筆墨形神兼備、立意深遠。“藝術作品要求傳神,具有意境,這與作品創作者的精神追求和閱歷分不開,但首先必須好學。”許石斌告訴記者,閱讀古籍是藝術創作者提高精神境界的一個重要來源,他經常會購買和借閱一些經典的中國古典文學書籍如四書五經等來讀。
“《易經》是一本了不起的書,書中對于傳統文化中自然哲學的探討可以讓人重新認識自己。”許石斌說,在藝術創作中,《易經》給了他很多思考,他意識到這個世界的主宰不是人,人只是一個普通的生命體,把人從盲目自大的神壇上拉下來,讓人懂得謙卑,生活中要學會駐足,這樣才能感受別樣的美。
在藝術創作中,許石斌特別注重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在他看來,藝術的價值性來源于生活,保持對周圍生活的考察可以提升一個人對現實世界的關懷,“在藝術中,我試圖通過真善美以及佛教中所講的因果輪回來啟發人對生活的重新審視。”
在許石斌看來,陶瓷藝術的表現特征是其同時具備欣賞和實用兩種功能,這也是最貼近人類現實生活的一門藝術,是對于器物實用性的追求。但是,陶瓷又不僅僅是這些元素的集合,它還具有精神上的意義。尤其是它給人一種自然般的線條造型,包括器物外表裝飾圖畫所生發出的藝術魅力,讓人有合乎心象的傳神和意境美。
“這點符合古人講的真善美和所宣揚的天人合一自然法則,而意境就是怎么將真善美形象地表達出來,傳神就是要用所學的技能、手法將這些真善美簡潔、生動并以符合審美標準的方式表現出來,中國的藝術都講究這個。”許石斌告訴本刊記者,作為藝術創作者,他會將自己的社會情懷盡量巧妙地融于作品中,必須引發人們對生活或者自身行為和觀念的反思和重塑。
許石斌說,齊白石老先生用墨畫出一顆白菜,期間并沒有用其他色彩來渲染,“用淡淡的墨畫莖,用深色的黑墨畫白菜的葉子,隨后題字‘清白傳家’。”這幅作品不但畫得好,最關鍵的是字題得好,他不但給人以美,而且“教育人做人要清清白白,這超出了時空的界限,不管什么時候都受益。能畫出白菜的不少,但是能將這種真善美結合起來的則很少,這就是意境”。
誠然,藝術界的的確確生活著這樣一批人,生計對他們而言只是生命延續的手段,他們離不開它;卻從靈魂深處鄙視著只為生計而活著的這種活法。在他們的腦海中,人不能僅僅只是為了活著,高貴的氣質、寬厚的愛心、悲憫的情懷、堅韌的毅力等等,這些都是活著的價值,他們是當之無愧的“精神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