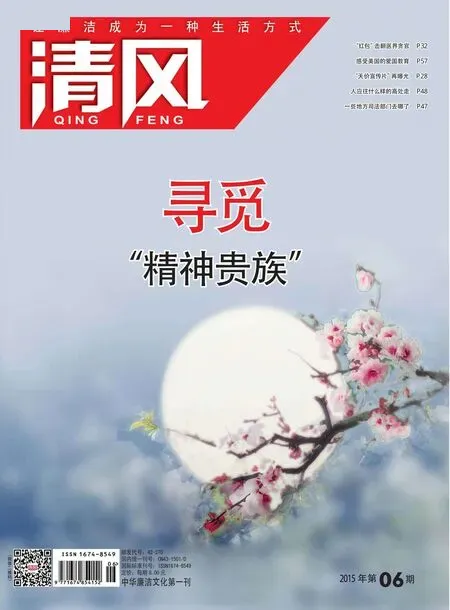尋訪醫界的“精神符號”
文_本刊記者
尋訪醫界的“精神符號”
文_本刊記者
醫生,因其肩負治病救人的神圣天職而被人稱為“白衣天使”。然而,我們無法回避的是,當下有關醫生的負面新聞卻也是接二連三地出現。在追逐金錢的浪潮中,不少醫生也未能免俗,“治病救人”成了他們掙錢謀生的手段,而不再是一種崇高的使命。于是乎,收紅包、吃回扣、只開貴藥、過度醫療等亂象自然也就層出不窮。
有人說,醫生也是人,是人就會有貪念。然而,醫療工作畢竟關乎人的健康、生死,它是一份“良心工作”,這個行業的從業者理應有著更高的精神追求。值得慶幸的是,重視榮譽與操守、堅守責任與良知的醫生還是大有人在,他們占有的物質財富或許并不豐富,但他們卻是真正的“精神貴族”。
不收紅包是底線
不收紅包是醫生絕對不能突破的底線。一個人生病了,其本身就需要錢來醫治,醫生再收紅包,是額外加重他的負擔,怎么也說不過去。
曾有新聞報道,某年輕醫生初到醫院工作,不愿收受病人家屬送的紅包,卻被同事視為異類。更讓他苦惱的是,他不收紅包,連病人都不放心讓他來做手術。按理說,這種現象是很不正常的,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
2014年,國家衛生計生委甚至還出過規定,從當年的5月1日起,醫患雙方必須簽署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此舉在當時還引發了不少爭議,不少醫生感到很委屈,他們認為“此協議的前提是認定了醫生會收紅包,這是挑戰自己的醫德”。的確,并不是所有醫生都愛收紅包,對病人認真負責原本就是醫生的職責所在,面對那些一定要用紅包來買定心丸的病人,很多醫生其實也很頭疼。
無錫市第八人民醫院主任醫師繆榮明醫術精湛,尤其在職業病矽肺的治療方法上有獨到見解,很多病人都慕名前來找他看病。也經常有病人要給他塞紅包,對此,他一律拒絕,有時候實在拒絕不了,他就只好先將紅包收下,回頭再將錢交給醫院的紀檢部門或者直接打回病人的賬戶。據不完全統計,他每年拒絕的紅包金額超過了4萬元。
在繆榮明看來,不收紅包是醫生絕對不能突破的底線,一個人生病了,其本身就需要錢來醫治,醫生再收紅包,是額外加重他的負擔,怎么也說不過去。繆榮明還對記者表示,他所在的醫院是一家二級醫院,并不是三甲醫院,很多病人特地來一家二級醫院找他看病,是出于對他的信任,如果收人家的紅包,顯然是對這份信任的辜負。
繆榮明不僅不收紅包,遇到那些經濟上確有困難的病人,他還會自己掏錢為其支付醫藥費。他不收紅包,但他對病人的關心卻一點都沒有少,每次實施大中型手術后,繆榮明都會住在醫院,24小時關注病人的病情變化。曾有一個直腸癌病人手術后出現應激性潰瘍,繆榮明在醫院守候了整整72個小時,直到病人脫離危險后,他才回家。
賈立群是北京兒童醫院超聲科主任、黨支部書記,我國著名兒科超聲專家。他堅守門診一線37年,接診患兒30多萬,挽救了2000多名危重患兒的生命,被譽為“為民愛民的好醫生”。
很多家長想給賈立群送紅包,但都被他拒絕了,患兒家長以為是他客套,就硬往衣兜里塞。來回撕扯,白大褂的兜都給撕壞了。于是,賈立群干脆就把兜給撕了下來。后來同事們說:“你這白大褂怎么沒兜呀,看著特像廚房大師傅。”他聽完后雖然讓護士長把兜縫回去了,但卻特意囑咐她把兜口縫死。再有家長塞錢的時候,塞不進去,就放棄了。他總是對患兒家長說:“您放心,我肯定給您做。您把錢用在看病上吧,我的兜都縫著呢。”
因此,賈立群也被人們稱為“縫兜大夫”,他縫住了口袋,也守住了一名醫務工作者的良好醫德,每個醫務工作者都應該向他學習。
基層醫生的責任與堅守
“醫生不是商人,醫生首先想到的要是病人,治病第一,救命第一,錢是放在后面的。”
孟凡珍是濟寧市任城區唐口街道一位普通的鄉村醫生,今年五一,他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而在此之前,他已經先后獲得“山東省十佳優秀鄉村醫生”“全國優秀鄉村醫生”等幾十項榮譽。
1986年,孟凡珍考入濟寧醫學院,臨近畢業,大多數同學都希望能進市里大醫院、鄉鎮衛生院等工作條件較好的單位,而孟凡珍卻選擇回到家鄉當一名村醫,這讓許多人很不理解。
而孟凡珍的理由卻很簡單:“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我對農村的情況比較了解:醫療條件差,缺醫少藥,所以立志當醫生,為老百姓解除病痛,因為咱本身也是老百姓。”
當一名村醫,經濟收入自然和大醫院的醫生沒法比,但是孟凡珍不在乎,他對本刊記者說:“醫生不是商人,醫生首先想到的要是病人,治病第一,救命第一,錢是放在后面的。”
家住濟寧市加河村的五保老人魏德平身患腰椎骨質增生多年,然而高昂的醫藥費卻使得老人的病沒能得到及時的治療。孟凡珍得知后,主動上門為老人診斷,并且免費為其治療。在治病過程中,孟凡珍還發現,老人還有高血壓,因此,孟凡珍對老人的飲食起居格外關心,他經常得空就去看望老人,給老人帶一些降壓藥,買些生活用品。老人常對人說,看到孟醫生,就跟看到自己的親人一樣。
“其實這也讓我很感動,咱做了一點小小的事情,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可,感覺自己做的事情很有價值。”孟凡珍說。其實像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孟凡珍扎根基層醫療一線近30年,他走村串戶,先后騎壞了十幾輛自行車,他免費救助農村五保、孤寡老人達百余人次,還經常自己掏錢幫助貧困家庭發展種植、養殖等副業。
去年,他拿出了自己幾十年積攢下來的全部積蓄100萬元,建立了“孟凡珍慈善醫療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免費救治低保家庭成員、五保老人等家庭貧困病人,解決他們看病難的實際問題。他的很多親朋好友對此都表示不理解,“如果你不幫我,我不幫你,這成了什么社會了?當年,咱窮的時候人家幫了咱,咱現在就應該幫別人,就是這么簡單。大家都互幫互助,社會才能和諧。”
像孟凡珍這樣的基層醫生,還有很多很多。湖北省宜昌市點軍區土城鄉席家村鄉村醫生劉祖林,從醫47年來,他共走了五六千公里路。只要村民一個電話,無論天晴下雨、白天黑夜,他都隨叫隨到,他每天差不多要走20多公里路,多的時候有30公里。一年要換3雙解放鞋、3雙涼鞋。他每年看病3000多人次,每人次平均藥費僅12元。說起這么多年的堅守,劉祖林坦言,這主要是鄉親們需要。“沒有人愿意來大山里,我可以一直干到干不動為此但如果一直沒人來,村民們有病怎么辦?”說起這些,劉祖林無奈嘆息。他希望能有人繼承鄉村醫生這個行業,繼續守護大山深處全村人的健康。

肖長江在問診
還要“醫人之心”
技不如先者不可為醫,心不如佛者不可為醫,醫生既要注重提升自己的醫術水平,也要有一顆慈悲之心,不能只想著錢。
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寫道:“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湖南省中醫藥研究院附屬醫院心血管內科、重癥醫學科主任肖長江教授就是這樣一位“大醫”。
對待病人,肖長江總是非常耐心,本刊記者對他的采訪原本約在下午4點,記者來到他辦公室門口時,他還有幾名病人需要診治,記者只好在門口等候,這一等竟等了1個多小時。因為肖長江看病不僅僅只是診病開藥,他還會根據病人的情況,非常耐心地與病人“閑聊”,這是他獨創的“話療法”,通過言語的開導,紓解病人的心理負擔,療效很不錯。
然而,和一個病人就聊那么長時間,一天下來看不了多少病人,收入也就大打折扣了,但肖長江并不在乎。在他看來,技不如先者不可為醫,心不如佛者不可為醫,醫生既要注重提升自己的醫術水平,也要有一顆慈悲之心,不能只想著錢。只有將物質的要求降到很低,才能夠更自由地去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
肖長江的志向不光是醫人之身,還要醫人之心,不光給人治病,還要給社會治病。為此,他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廣國學、推廣傳統文化。肖長江認為,傳統文化里面蘊涵了很多讓人不想貪的元素,可以凈化人心。“它讓我們明白,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同時,肖長江還非常熱心公益,并獲得了湖南省首屆“三湘好醫生奉獻公益獎”。
談到當前的醫患矛盾時,肖長江向記者介紹了他所在的心血管科病房的情況:每個禮拜四早上,醫護人員都會和病人一起誦讀《弟子規》,醫護人員也都能按照“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的態度去對待病人;對那些重癥晚期病人,醫護人員還會對病人進行臨終關懷。這些做法讓很多病人家屬深受感動,有的家屬還下跪致謝。肖長江笑著說:“《弟子規》講‘凡是人,皆須愛’,我們用儒家的仁愛思想以及佛家的慈悲思想去化解人們心中的障礙,讓醫學回歸人文本原,病人又怎么會拿刀去砍醫生呢?”
最近,中央也在大力推廣傳統文化,這讓肖長江很高興,他說:“習總書記講,人民有信仰,國家才有希望。不管是我們醫生也好,老師也好,政府官員也好,大家都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提升自身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上來,精神財富才是最寶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