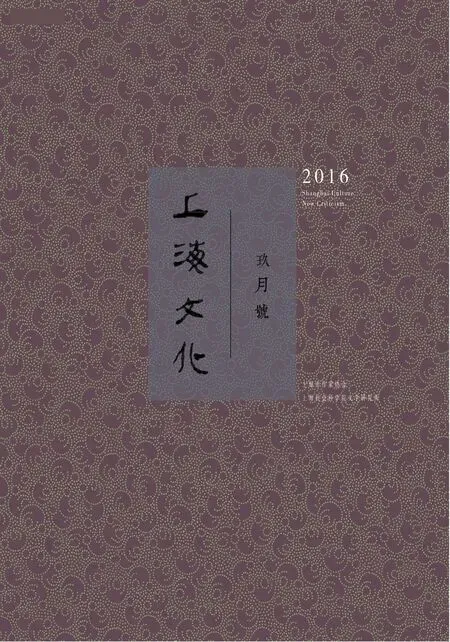詩歌中的非理性因素①
華萊士·史蒂文斯 著 李海英 譯
?
詩歌中的非理性因素
華萊士·史蒂文斯 著 李海英 譯
1
首先,“詩歌中的非理性因素”這種說法,似乎太過空泛而不具效力。但對其稍加思考就會發現非理性的意義展現于各處。然而,由于我們總被超現實主義者和超理性主義者所制造的喧鬧所困擾,再加上閱讀他們作品時太過專注,結果我們就被這些浪漫學者搞得困惑不已,于是便將其視為當今非理性的典范。當然,他們也確實體現了非理性的一面。不過就我而言,在我討論詩歌的非理性因素時,我心中所指的是——由詩歌所促發的現實和詩人感受力之間的交互活動。
2
我并無能力如哲學家那般去討論現實問題。我們都明白,客觀現實與主觀現實之間的置換意味著什么。現實與詩人感受力之間的交互活動也恰恰如此。感恩節前的一兩天,哈特福德剛剛下了一場小雪,雪白天融化了一些,到晚上又上凍,結成一層薄薄的透明的殼覆蓋在草地上,其時月亮滿盈。天亮之前曾有幾個小時,我醒著,躺在床上,聽著窗下雪地上貓跑過的腳步聲,聲音很小,幾乎聽不見。這種聲音的微弱與奇妙給我留下了一種印象,就是一個人解釋自己為何寫詩時最常用來作為理由的那種印象。我想在這種情形下,人就是在純粹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力。為何感受力的表達要采取詩的形式, 這是因為感受力能利用人賦予它的任何形式。詩人能夠給它以詩歌的形式是因為詩歌是詩人感受力的媒介。這一點不同于我們說一個詩人創作詩歌是因為他在寫詩,雖然聽起來像一回事兒。一個詩人創作詩歌是因為他是一個詩人,我們說他是一個詩人,說的并非是其詩人的身份,而是其具備的作為詩人的個人感受力。我不清楚是什么給予了詩人以個人感受力,不過這不重要,因為沒有什么人清楚。詩人會不斷地誕生出來,但卻不能被造就出來,恐怕,也不能被事先預定出來。如果詩人能夠被預先確定,從一種意義上講,他們可能早就被滅絕掉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能夠被預先確定,詩人或許早將今日的生活改造為他們喜愛的模式,或許還會設法大量繁殖他們自身。
3
當然,詩歌中非理性因素是有歷史的,不過從根本上看,這種歷史僅是藝術中非理性歷史的一章而已。此處思考的不是病理學意義上的非理性。比如,福塞利習慣晚上睡前吃生牛肉,以便他的夢獲得一種牛肉般結實的暴力,否則,就會認為缺失了此種力量。我們關注的不是此類事情,也不是因祈禱、威士忌、禁食、鴉片或成名的希望等手段所激發出的那些非理性。18世紀英國的哥斯特小說不再是非理性的,現在它們讓人厭煩。我們感興趣的是理性思維中的某一特殊進程,我們將意識中不明就里的發生過程視作非理性。或者,進一步說,我們感興趣的與其說是黑格爾的形而上學進程倒不如說是它帶來結果。如果從已形成為傳統的非理性歷史來看,可能我們還會生發出一個更明智的興趣。我們是理性的存在,是亞里士多德學派,不是野獸,用這種觀點很容易就將非理性棄置一邊。不過現在更容易的是,說我們是非理性的存在,說完整的非理性不是一個片段,說非理性尚未成為一個傳統的唯一原因是其傳統還在形成過程中。很久以前當我還在哈佛時就流行一種俗套之言,說,所有的詩歌已被寫完、所有的繪畫已被畫完。最先讓我們對非理性感興趣的可能就是這類東西。自那時起,弗洛伊德就成為世界偉人之一。雖然比起在別處的影響,他對詩歌的影響微乎其微,但他確實給了非理性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更為意義重大的影響是馬拉美和蘭波。
4
也許,我的題目可以更精準地表述為:詩歌中非理性因素的非理性表現,因為如果非理性因素是純粹的詩學能量,那么哪里有詩出現,哪里就有非理性顯現。顯現之一就是詩人個性的顯露。此種顯露不可能對于每個人都和對于詩人本人那樣清晰可見。過會兒我要讀給你們的第一首詩,思考的主題是大蕭條對藝術興趣的影響。我想直面一次這樣的世界——藝術想象的世界與實際生活中所是的世界。如果我碰巧走進一家畫廊,卻發現對自己所見之物毫無興趣,氣氛被焦慮和壓力所控制,那么看畫展就像今天下午在馬德里彈鋼琴一樣(無趣)。自然我也可以像別人那樣做點兒觀察或作些筆記,如果那是我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會那樣做。而我想處理的恰恰就是這樣一個主題,并且把它作為多少有幾分真實、現實與當代性的事物給挑選出來。但我想用詩的方式來完成,只要我能夠寫詩。明確地說,我要將我的感受力應用在某種完全真實的事物上去。產生的結果會成為我自身感知力或個性的一種揭示,就像剛才我說的,這當然是向我自己進行顯露。要讀的詩叫《老婦人和雕像》,老婦人是大蕭條時期那些苦難人的一個象征,雕像是藝術的一個象征。盡管《貓頭鷹的三葉草》(我準備讀的一本書)中有幾首詩,堅稱,雕像是一個變化多樣的象征。盡管這首詩里并無無意識的東西,不過,從“我想要什么樣的詩”這個意義上講,詩本身卻有無意識的一面,雖然在寫出之前我并不知道我想要的詩什么樣子,或者縱然在寫出之前我知道我想要的詩什么樣子。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生物機器,那么每個詩人就是一個詩歌機器。一定程度上,詩人的創作就是機械的:也即是,詩是非理性的,是他無力去改變的。或許,我的意思并非說完全無力去改變,因為詩人也可能會憑著意志的努力去改變它。按照這種思路,我的意思是,只要詩人還是詩人自己,就難有改變的可能性。這種情形發生在每一個詩人身上。
5
同樣,我認為主題素材的選擇也是完全非理性的行為,只要有詩人為自己留下任何選擇的自由。如果你是一個意象派詩人,你主題的選擇顯然是有限的。如果你是其他派別并且對之堅貞不渝的話,情況也同樣如此。但要是你決定保持自由,或周游世界去體驗那些你可能體驗到的一切——像大多數人做的那樣——盡管他們會矢口否認,那么,你主題的選擇要么是偶然的,要么是做出選擇的環境的特性是不易覺察的。抒情詩人被春天困擾,浪漫詩人被秋天困擾。當一個人熟悉了自己的詩,他的詩就成了陳詞濫調,于人于己皆是如此。據此可知,寫作中動機之一乃是更新。這一點對主題選擇的影響是毋容置疑的,就像它在韻律、詞語和方式的變化上的影響那樣鮮明。我們本能地變換韻律,這是基本的。 我們嘴上說我們在完善措辭,但我們不過是疲憊罷了。手法技巧并不能被完全解除不用。手法技巧并不是風格,而是作者的態度,與其說這是他的姿態不如說是他的主張。其姿態指向何物?并不特別指向什么,僅是展現其精神狀態。他聽見貓在雪地上。奔跑的腳步譜寫韻律。除了月夜雪地上貓的奔跑之外,沒有別的主題。慢慢地他對此事產生了徹底的厭倦,想換一個主題、思想、感覺,于是他的整個手法技巧隨之改變。所有這些事物都會進入到主題的選擇中。在一個人工教育中長大的人變得過度真實了。馬拉美主義者會變成無產階級小說家。這一切都是非理性的。如果主題選擇是可預測的,它就會是理性的。現在,就像一開始我們選擇了一個不可預測的主題那樣,被選之后其發展走向也是不可預測的。有的人總是在一首詩中同時寫下兩種事物,一個是“真實主題”,一個是“主題的詩意”,正是這二者產生了詩歌的張力特征。當詩人心中占據至高位置的是“主題的詩意”時,堅持“真實主題”就變得困難重重,這一點不言而喻。假若詩人讓“真實主題”占據至高位置,那么他僅需潤飾它就行了,因為主題自身會持續進行并有序發展。而假若是“主題的詩意”占據至高位置,“真實主題”就不能持續進行也不能有序發展。比如現代散文中,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就是這種情形。
6
關于一個人為何寫詩?我已陳述了一些理由。其中包括:因為他被自身感知力驅使著這樣做,也因為他疲憊于自身想象力的單調,于是開始尋找變化。十多年前,在法蘭西學院的一次講座中,布雷蒙先生闡釋了一種神秘動機并明確指出,他認為一個人寫詩是為了尋找上帝。對于這個問題,我想把它與理應被單獨加以思考的問題放在一起來思考,這也是詩歌中關于意義的問題。布雷蒙先生提出詩歌與祈禱的同一性,而且像柏格森一樣,最終信賴于信仰。布雷蒙先生將作為詩歌基本元素的理性排除開去,認為詩歌中非理性因素占主導地位的詩才是純詩。布雷蒙先生自己不允許闡釋純詩時有絲毫疏漏,他將純詩限定在一個非常小的詩歌團體中,如其所愿,如果他認可的那些詩行對他的精神來說是珍貴的,那么這些詩行對于它們呈現的樣子來說也是同樣珍貴的。不管布雷蒙先生怎么想,“純詩”這個術語已經發展為詩歌的描述方式了,亦即是“主題的詩意”占據至高位置、而非“真實主題”占據至高位置的詩歌。所有神秘主義者接近上帝都是通過非理性實現的。“純詩”兼具神秘性與非理性。如果我們放低一點高度,給純詩一個更為松散更為寬泛的定義,那么就可以這樣說,雖然純詩僅存在于我們極罕見的氣質之中——寫詩是為尋找上帝,但大家寫詩的目的多半是為了尋求善,而在柏拉圖的意義上,善與上帝同義。既如此,一個為了接近善而寫詩的人,就是在和諧與秩序中寫作。或簡單來說,一個人寫詩是出于置身于和諧與秩序的愉悅。如果最抽象的畫家畫出的鯡魚和蘋果是真實的,那么最急切地在世上尋找生命的認可、尋找那使生命如此奇妙如此值得活著的詩人,也一樣是真實的,這些詩人會從池塘里的一只鴨子身上或從冬夜的風里,找到自己的解決方案。這是可以想象的,一個詩人通過對某些抽象之物配置豐富的音樂性而提升作品的范圍。其間,我們不得不生活在我們已有的和能夠生產的文學中。我說生活依賴文學,是因為文學是生活中較好的一部分,只要文學是基于生活本身。從這點看,詩歌的意義與我們緊密相連。但不能因此斷定,源于非理性的詩是不可傳達之詩。布雷蒙先生的純詩本質上是非理性的。然而,由于它能傳達得如此廣泛,以至于布雷蒙先生將其看得至高無上。由于我們絕大多數人不能體悟布雷蒙先生的此種經驗,所以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那么,當我們在詩中發現它在一個美好層面上提供給我們瞬時的存在,是否有必要再繼續追問該詩的意義?如果一首詩本身有意義而對它的解釋毀滅了對它的幻想,我們是應該獲取它還是丟棄它?舉蘭波《靈光集》中題名為《被擊打的車轍》的詩為例。我引用一下魯特姆小姐的翻譯:
右邊,夏日的黎明喚醒了樹葉、薄霧和公園角落里沉睡的聲音。左邊的陡坡上,穿過紫色的陰影里是無數車轍碾過潮濕的路面。這的確是仙境中的游行:大車滿載著金色叢林中的珍禽、插著旗桿、裝飾著五顏六色的花布,馬戲團里的二十匹斑馬飛奔出場,孩子和大人騎在這些驚恐的馬匹上;二十輛馬車套著韁繩,插滿彩旗、鮮花,就像古代的四輪馬車或是一篇篇童話,車上坐滿了奇裝異服的孩子,他們正要去鄉村演唱牧歌。就連棺材也在暮色籠罩與黑色羽翼下,隨著青色的母馬小跑起來。
我不知道這首詩創造了什么意象。德拉哈耶先生說,該詩緣起于到法國沙拉維爾演出的一個美國雜技團,蘭波小時候在那兒住過,大約是1868年或1869年。這種解釋的作用是什么?無須我回答。西特維爾小姐曾為魯特姆小姐翻譯的蘭波詩集寫過一個序言。序言中有一段話,演示了真實主題取代名義主題的方法,她說:
當蘭波還是一個生活在沙拉維爾的小男孩的時候,過得是一種多么艱難的生活(貧民窟),蝸居著,更甚的是一種永無止期的悶氣星期天,在這些日復一日穿著緊身衣和禱文的日子里,當蘭波太太帶著他和他的哥哥以及兩個姐妹,參加11點鐘的彌撒,走過陽光下灰塵彌散的道路,在樹下能看到閃閃放光的葉子和碩大粉紅的花朵,這些形象看起來很有可能被轉化為上流社會女子的形象,她們搖擺著大笑著出現在清醒的隊伍之中。
西特維爾小姐自己也說不清,11點鐘的彌撒是否暗指閃閃發光的鮮花,或者上流社會女子是否帶著大量的光彩閃耀的葉子進入了她的頭腦、并正好被碩大粉紅花朵圍住,或者她們來時是否帶著碩大的粉紅花朵。在西特維爾小姐的腦海中,只能如此推測——上流社會女子,一方面或許是光彩和閃耀,另一方面或許是巨大和粉紅。這里的“真實主題”指向的是一種印象的燦爛和色彩。
7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現在,時代的壓力已持續很久并達到極端,沒有人能離群索居生活于幸福的遺忘中。在戰爭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一切都再平常不過了。海上漂浮著的都是游艇,游艇里站著的都是百萬富翁。那是一個只有瘋子才有煩惱可說的時代。那個時期恰似一個舞臺布景,其背后是拆卸和卡車離去的聲響。隨著戰爭的結束它也被拆卸,盡管我們花費了十年時間才爭取到對和平之重要性的認可,才形成對該事實的認識。大家說如果戰爭繼續,文明將由此終結,就像他們現在說的那樣,另一場類似的戰爭將終結人類文明。不過,談論文明的終結是一回事兒,感到這終結不僅可能而且會發生則是另一回事兒。如果你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就不會有文明終結于俄羅斯之感嗎?如果你不是一個納粹,就不會有文明終結于德國之感嗎?我們剛一說這事兒永遠不會發生在我們這兒,我們就意識到了我們這樣說其實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我們被這類事件糾纏著,甚至在我們沒有仔細觀察它們的時候,也是如此。我們有一種滄桑突變之感。我們感受到了威脅。我們從不確定的當前眺望更不確定的未來。不管是在詩歌中還是在政治中,我們都感受到了抗拒這一切、保持自我的意愿。如果由于時代壓力,政治更接近于我們每一個人,那么詩歌也一樣,并且是出于同樣的原因。是否有人認為,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通過理性思考會在最后一輪的選舉中被感動?這種理由的可信度就像電臺的可信度,這里仍有人確信這種感動是有感情的,而如果是有感情的,那么這就是非理性的。問題在于,時代壓力越大,抵抗力就越大。抵抗是逃避的反面。一個詩人他希望能夠思索混亂中的善,就像一個神秘主義者希望在邪惡之中思索上帝,不能有逃避的念頭。無論是詩人還是神秘主義者,都可能是用鯡魚和蘋果來表現自己。畫家可以通過一把吉他、一本《費加羅》、一盤香瓜來表現自己。這些雖然都是非理性的瑣事,然而它們卻在堅定信心。對時代壓力的抵抗只有一種可能,大約就是用鯡魚和蘋果等物了,或者不那么確定地說,用時代自身來抵抗。在詩中,某種程度上,主題并非只是時代,因為那僅是一個名義上的主題,而是時代的詩性。對不祥的壓力與毀滅的環境的抵抗包含著其自身的轉化,并且盡可能地,轉化為一個不同的、一個可釋的、一個可檢的境遇。
8
查爾斯·莫隆先生說過,一個人的個性特征就是他所執迷的東西。我們執迷于非理性,是因為我們期望非理性將我們從理性中解放出來。有一篇評論畢加索的文章,標題很明了,叫《社會現實與宇宙幻象》,作者克里斯蒂安·澤沃斯說:
他的精神爆炸已摧毀了藝術……強加在想象上的障礙。詩迎面而來,帶著全部的敏銳、詭異、陌生感,它不僅在生活中看到了真實的形象,而且還將生活看作是一個無處不在縈繞著我們的謎。
以畢加索為例,這個現代人容易想到的畫家,可便于說,畢加索的精神就是渴望尋求自由的藝術家的精神。一個對此種精神高度癡迷的人就是對自由的癡迷。然而,這里不再有那么多針對精神爆炸的借口了,因為,就像繪畫中那樣,在詩歌中,你也能做你所樂意做的事情,你也可以按照你喜愛的任一方式去寫詩。如果你覺得用大寫字母寫首行像17世紀的習慣,那么你可以嘗試更簡單的靈活轉化,等等諸如此類。沒有人會在乎。這很重要。最微小的聲音之事,最短暫的韻律之事,都很重要。你能做你樂意做的任何事情。你是自由的,但你的自由必須與他者的自由一致。再強調一下聲音的重要性。我們已經不再喜歡坡的叮叮當當了。當然,你若喜歡,盡可自由地叮叮當當,不過別人同樣有權利捂起雙耳。生活也許并非就是無處不在地環繞著我們的宇宙之謎。無論如何你得知道這個聲音正是那個確切的聲音。事實上你是知道的,不知道所以然而已。你的知識是非理性的。在這種意義上說,生命是神秘的,只要它有些許的神秘,我認為就是一種宇宙性的神秘,我希望我們至少能同意它是神秘的。聲音之真是一切之真:比如,感覺詞語時,無須顧及聲音。簡言之,未寫下的文辭總是處于變化中,詩人必須不停地對之進行轉換。正是通過這本書,詩人明白了他對文學的欲望就是對生命的欲望。文學中或任何藝術中對自由的無盡欲望就是對生命中自由的欲望。欲望是非理性的。其結果是非理性地尋求非理性,顯然這是一種愉悅狀態,如果你有此傾向。
那些有此偏好的人毫無保留地說:在非理性追求中,任何一絲一毫的嚴格刻板都將被視為令人厭煩的東西。理性人是暴民。我們應當在眼中進行挖掘,而不是單純地去看;我們應將聲音與一種情緒的咔嗒咔嗒并置起來,而不是單純地去聽。
這似乎是為了自由而自由。如果當我們已經自由時仍說我們渴望自由,那么很顯然,我們心里所想的自由是以前沒有經驗過的。那么,這難道不是一種類似于詩人對現實之態度的生命態度嗎?盡管當我們聽到此類事情時會想起種種譏諷,但一種從未經驗過的自由、一種從未構想過的詩歌,可能會借助詩意變形中固有的突發性而出現。對詩人來說,可能性乃是終極的吸引。他們凈化自身于現實之前,同時,也意圖在虔誠實踐的事物中凈化自身。
你是否記得蘭波寫給德拉哈耶先生的信中,他曾如此說:
必須成為一個先知,把自己變成一個先知。詩人把自己變成先知,靠的是讓感官(意識)處于漫長的、巨大的、刻意的混亂之中……他以此獲得未知。
9
關于詩歌動力學中的非理性部分,我再說最后一點。非理性與理性之間的關系,和未知與已知的關系一樣。在這個理智得嚴峻的時代,任何關于未知的話語很快就會被駁回。我無意于賣弄神秘修辭片刻,因為就我而言,我對此類事物毫無耐心。未知作為知識的資源作為思想的客體,是已知的動力學的一部分,這一點不容否認。未知激發學者的激情,如果他們囿于已知,會因倦怠而逐漸枯萎。即便在我們疑心重重之時,我們依然會接受未知。除了那些最明澈的心靈,大家都厭惡對其進行的思考,而一旦思考,未知的誘惑力將遠比已知更為強烈也更為深刻。
即便如此,總有些人,由于并不確信理性能確使我們變得神圣,還是愿意相信非理性在此方面起的功效。理性心智在處理已知時,總想發現它正閃爍于熟悉的氛圍。但真正發現的是藏在已知背后的、離得很遠的未知,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可能顯現出一種明暗對比的表象。自然,非理性的騙子也是存在的。然而無論如何,都不需要我們用騙子去定義非理性。我也不想讓人誤解,認為我指的是那些超現實詩人。他們將他們所有的杰出技藝都集中于一種看似非常局限的技巧之上,但同時又展現了非理性的動力學影響。他們是不同尋常的活力,而且他們讓我們有機會讀到充蕩著歡樂與青春的詩歌——正當我們開始對歡樂和青春絕望時,這對善來說意義重大。因此,他們能否使其它的形式過時,是檢驗其動力品質及動力效果的一個標準。久而久之,他們,將被吸收,并由此產生技巧方面的那些嚴格汰選又無足輕重的條條框框,一種非常粗劣的東西;他們,也將會相互妥協并成為詩歌生長所構成的相互妥協的進程的一部分。
那些熱衷于在新鮮奇異之處尋求詩歌新鮮奇異的人,源于一種熱烈的需要。詩人對詩的需求是他寫詩的一種動力因。他借助于非理性在非理性中發現了樂趣。當我們談論趣味的波動時,事實上是在談論非理性運作的跡象。此類變化是非理性的。它們反映了的詩學能量的效果,因為假若沒有這種波動,也就沒有詩學能量了。顯然,我說“非理性”這個詞時有些隨意,沒有區分它的若干含義。將來有的是機會形成一個比較系統的用法——等有人專門著述“非理性”之時——不管最終由誰來完成這個至關重要的論題。我們必須憑借非理性并在非理性的領域內,期待未來有連續不斷的活動。因此,即將取得的進展會更偉大,只要詩人的個性特征不再是如此隨意為之如此反覆無常。詩人不能像牧師信奉未知那樣信奉非理性。詩人的作用更廣闊,因為他必須跟隨每一事物,癡迷于大地和人類最樸實的意義。對詩人來說,非理性是基本的,但無論詩歌或是生活通常并不處于其動力之頂峰。就像我們都知道的斯威尼那樣,大家喜歡的是他最本色的樣子,而非環繞著耀眼光輝,毫無疑問,始終如此。
? 本文是華萊士·史蒂文斯1936年在哈佛大學的講演稿The
Irrational
Element
in
Poetry
,選自Wallace
Stevens
:Collected
Poetry
and
Prose
, Edited by Frank Kermode & Joan Richardson, Reprint by Library of America,1997, P781-792。? 福塞利(Henry Fuseli),1741-1825,瑞士畫家,代表畫作《夢魘》。譯者注。
? 此處的“the true subject”與“the poetry of the subject”,我譯為“真實主題”與“主題的詩意”,由于文中詩人著重討論了這兩個關鍵詞,為了突出,譯文中特意加上了雙引號,原文并無。譯者注。
? 此處的“M. Brémond”,指的是寫作《純詩》的法國詩人Abbé Henri Brémond。譯者注。
? 本文中史蒂文斯引用的蘭波的詩,翻譯時參考了王以培先生的譯文,在此表示感謝。參看《蘭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譯,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譯者注。
? 斯威尼(Sweeney),在英語文化中是一個 具有原型性的人物:一是愛爾蘭傳說中的斯威尼國王,因精神分裂而拒絕人類文明,成為一個悲劇性的英雄;二是傳說中的18世紀的惡魔理發師斯威尼;三是艾略特塑造的力士斯威尼形象。三者都是英語文化中熟知的人物形象。譯者注。
編輯/張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