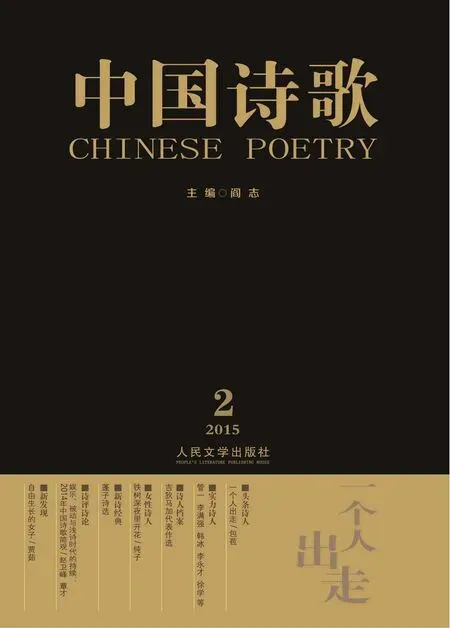管一 的詩
婚 姻
據說 死亡是一種快感
在接近的一剎那能看到天堂。
一個吸著煙的男人寧可忘記這種幻覺
他的理由是思考。
妻子的幸福感
是在噩夢的懸崖上被拽了回來
然后她憤然張開了剪刀。
日子里最閃亮的金屬是詛咒
能換回她年青的記憶
和歇斯底里的幻想。
婚姻向來有冷笑的成分
有時候漠視是一種合理的解釋
有時候
需要做的就是無動于衷。
離婚室
她的臉上有著南瓜的干澀 又有著
山芋干般的委屈 她滿懷著心事
卻又嘟囔著不愿開口。辦證員王小花
起身把她拉進了內室 緊接著
里面傳來隱隱的哭泣聲 王小花
出來的時候也變得滿臉憂傷
張了張嘴 連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了。
對于一個男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女人 對于一個
一年中只見到自己的男人一次的女人
對于一個幾乎忘記了自己
還是女人的女人 對于一個一年
才做了一次愛的女人 對于一個一年中
才做了一次愛就得了性病的女人
她除了委屈 還能說些什么
瓷 器
黑暗中不敢伸手的 必是一件瓷器
或者是像瓷器一樣的人
或者是小女兒 再或者是
命運中的一種隱疾。
思維的慣性具有強大的隱喻性
可是 絕不能理解為慫恿
因為常人無國可誤
誤的只能是招致心痛。
中年豈有心痛的理由 因此
將瓷器置于心中
用揣摩擦亮它。用目光
遠送它 用所謂的
卻是不得已的理性排斥它。
然后 由著它從生存的狀態
轉變為感性的生活。
而在生活面前 最好閉嘴
變化足以訓練一件瓷器
在黑暗中學會嘲笑。
過山車
那呼嘯而去的
終不再顯形。它讓人瞬間迷茫
攫拔與飛速降落 同樣讓人血脈賁張
所不理解的是 它得以存在的過程
其實暗合一個人的命運。
在高壓下的飯局 變味的鮮
莫明的怒火。這是一次事件中的檢索詞
一切發生即結束 發 展
即意味著向死而生。
卑鄙者的結束有其黏稠性
那嗜血的吸盤 像 章魚一樣充滿政治
充滿幫派的色彩。而登場者
警惕著 不 落入窠臼。
其實 事 已至此仍不知所云
就像抵達頂板者仍不知去向 或 者
任由事件相互間纏繞
像喇叭一樣無聊的聒噪
大 樹
大樹的方向就是沒有方向。
它在地下糾結 在地上沒有表情。
有時候它的表情就是輕易地
隨風而起。問候每一個
令它動搖的念頭 但不相信。
它不相信一位爬著爬著就睡過去的人。
它也不相信躲在背影處親吻的人。
它不輕易愛上風
但是它允許風從自己的身體內穿行
它不相信撕心裂肺
它只相信萬物對它的面無表情。
野山棗
好多年了 它們一直躲在山谷里
像那些我已失散多年的星星 像曾經被烏云
覆蓋了的月亮。已經沒有了一丁點的做作
它們滿臉的陽光 讓我羞愧。
要不是我沖動地爬上那片陡峭的斜坡
也許就會與它們失之交臂 這些年
我總是向往錯位的生活 或者那些
刻意的陡峭。我已厭煩自己這些年來
總是自以為是的習慣 更是深惡于
無所不在的提防 而不像它們
我的失散多年的兄弟 它們是黑暗中的星星
這些守山的精靈 它們可能已忘記
我的名字 而我們的猝然相逢
它們除了一臉的陽光外
還是一臉的陽光
秋 雨
有些人一遇到秋雨就皺起眉
仿佛秋雨是個不祥之物
比起思念 秋雨更能進入骨髓。
越是能引起共鳴的
越是要隱藏 就好像有些交往
不外乎是比賽著進入對方的睡眠。
行動慢騰騰的人 不一定
就不會愛 也不一定就不愛
他只是躲在秋雨中
休息一會兒 又沖進人群繼續泅渡。
他愛秋天所有的。
他交給秋天所有的。
那一刻 所述甚明
相反的倒無從解釋 一下子陷入寂靜
他的血流停止 表情是大青蟲
一點點爬出門外。
他想起寂靜是一個人的命運
比起那些茫茫然的幸福
他更容易接受寂靜。
跳舞者
肢體的扭動 變形 甚至
在毫無征兆下抽出花蕊。在促狹的
投影屏幕面前 歡樂的時光
像水一樣容易流逝。閃爍的
不僅是燈光 還有失控的思想
它們有狹路相逢的驚慌。
本不相識者 豈能有舞伴的默契
有的只是瞠目結舌般的懷疑。
擊打大理石臺面的震動 比起鼓掌
其實更是一種拒絕 因為
如此遙遠的美 近乎一種嘲笑
是比大理石還四平八穩的
被時光消磨掉銳氣的 滑稽者。
……這是一段古典的樂曲
那大開大合的 那影影綽綽的回眸
許多語言迅速被鐵銹腐蝕。
致GG
不是因為孤獨才寫到你
他的孤獨是一支筆的孤獨
在一張打開的白紙上 他莫名地
戰栗。
在那一刻他羞赧萬分 他自責
他幾乎放開心中的豹子
他讓下午的咖啡館暫時性休克。
可是 這與孤獨無關
就像一個跌倒的人與深淵無關一樣
他止步于內心的懸崖。
讓閃電撤回內心 讓薄冰
將深夜覆蓋。重新注目你的碎花裙
讓它在風中自由地飄
直至飄出視線之外。
相 識
在樓梯的臺階上 她雙手抱在胸前
笑臉相迎。
這小城瞬間被點亮 包括
油膩膩的松木扶手
也顯出喜悅的光芒。
我從黑暗中來 在生活的反面
看不清自己的面目
甚至沒有幻想的由頭。
很久不見了…… 或者
從沒有見過的
在一本舊書中相識的那一幕
在時空的盡頭
她莫名地熟悉了這里的一切。
那抄在菜單背面的一首詩
那瓶充滿氣體的黑葡萄汁
都變成這個夜晚的
不安的因素。
跟 蹤
吸引我的是一段窒息的白
在踝骨以上 小巷的第二個轉彎
她的眼神有著沒落的氣息
一只波斯貓攔住我
綠寶石樣的眼睛射出狐疑的
目光 這是污水橫流的居民區
洞開的大門前
夾著煙頭的老太太 一段
煙熏火燎的舊時光
一只烏鴉引領著我進入深夜
靠著星星的反光
我差一點迷失自己 或者
我就是那個巷口前貼在電線桿上的
早就走失的男人
梅 雨
儲衣柜上的霉斑 與衣服的鮮艷
無關 前者絲毫不妨礙后者
對于生活的慫恿。
對于她的抱怨 不要總是幻想著
予以澄清 欲言又止的情景
與昨夜的夢境驚人的一致。
烏鴉事先預置在對方的身體里
等待黑色的寓言
開出黑色的花。
梅雨季節來臨前的一張素描
從她肢體的輪廓上取景
只是幾根線條
便勾勒出她不太完美的一生。
她有頻繁更衣的嗜好
在不停的蛻皮中
她的厭世情結得到一次次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