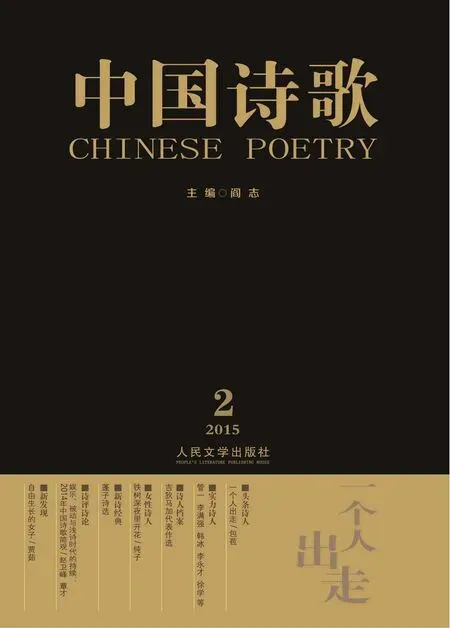詩學觀點
2015-11-14 23:26:16□薛曉/輯
中國詩歌 2015年2期
□薛 曉/輯
●蘆葦岸
指出,在娛樂塵囂過盛的時代,靈魂沉淪在文學中碎片化現象日趨嚴重,詩歌不可承擔人們詩意的棲居,甚至不能讓小眾化的詩人安心愉悅,靈魂的家園似乎成了最遙不可及的夢想。正因為如此,呼喚有靈魂的詩歌就成了“最高意義的歡樂”。詩歌于靈魂,猶如肉體之于生命,詩歌中的靈魂脈象有沒有,詩人文字里的精神品質好不好,直接決定一個詩人的“在場”與“遠涉”的能動性。維特根斯坦的靈魂煉金術是“自己之所是”,忠于自我,決心“不隱藏”的人生態度,在詩歌中幾乎是不二律宗。(《詩思并構的抒情范式與意境呈現
》,《芒種
》2014年10月上半月刊)●蔣登科
指出,個人體驗中融合屬于人類共同情感的元素:愛與美,使我們能夠通過這些舒緩、柔和的詩行中的體悟反觀我們自己。這樣的詩,超越現實,超越繁雜與浮躁,是內省的,貼心的。這樣的詩無論是表達方式還是情感狀態,都是慢節奏的。這樣的詩不是生長思想的詩,但它們是養心的詩。在多元發展的詩壇,人們的需要也是多元的,養心、養人、養情的詩都應該有其獨特價值,尤其在浮躁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慢的詩是可以養心的
》,《星星
》2014年第10期)●許文舟
認為,散文詩有詩的精髓,處處閃爍著詩性的靈光;散文詩有散文的特質,敘事因此有了足夠的空間和可能。散文詩不應簡單地對事情進行肢解,發現只是第一層面,剖析才能進行深度挖掘。散文詩并不貧瘠,與小說、散文一樣,只有找到自己的方式,才能掘出富礦,并通過思想的網篩,留下真正的金砂。確實有一種傾向,把散文詩內容無限擴大化,變成承載散文該負的責,表面是做大了,一旦將其濃縮,恐怕只有水分與殘質了。(《關于散文詩,只有敬重
》,《散文詩
》2014年10月上半月刊)●王迎高
指出,散文詩是一種比詩歌更自由的舞蹈,比散文更遼闊的飛翔。一個散文詩的寫作者,應該從傳統走向當代和未來,在歷史的綿延和文化的波瀾中回眸,強化生命意識,讓時間的陣痛與繁雜的現實情懷融入每一行文字,繁衍詩意,澆鑄精神,使散文詩作品有情,有感,有悟,有親切的畫面感與厚重的雕塑感。用靈魂發聲,用肺腑間滲出的韻律和色彩去表達、去呈現,這樣的散文詩才能使讀者聆聽到血液下面魚群溫暖的滑翔和大地之上萬物輪回的真實呼吸。(《散文詩的當代美
》,《散文詩
》2014年10月上半月刊)●王鑫
認為,詩是通過詩性的言說而最終通向思的。在西方,詩與思相通,詩是思的一種形式,詩通向哲學。詩性是彌漫在感性與理性之間的一部分,理性與感性可以在邏輯上截然分開,但是在事實上卻不可能,必定存在著某種過渡和涵容,而這一部分恰恰就是詩性。或者可以這樣說,詩性中包含著感性的認識和創造以及對這種感性認識和創造的形象化再現。借助于直感,詩性中包含著理性的思辨和洞見,詩是形象化具體化的思,故可以實現心靈與實在的通約。(《重建詩性
》,《芒種
》2014年10月上半月刊)●許德民
認為,漢字有一種特性和天賦,每一個字都有一種“象”,不僅是象形,而且是氣象和萬象,是生命的投射,是時間和空間的交融。有了語法和詞組后,文字成為關在籠子里被剪掉翅膀的鳥。抽象詩就好比將這只鳥重新放回天空,讓它自由而展翅。在抽象詩中,文字傳遞不同字組構成的文字自身的思想。抽象詩是從詩歌沉重的歷史感、宿命感、死亡意識中突圍出來的,快樂而非功利的詩歌形式。抽象詩追求詩歌張力、多重視覺與思維空間、似無還有的空靈感、與宇宙同道的頓悟與直覺。(《許德民訪談:自由而無用的靈魂
》,《詩歌月刊
》2014年10月號)●江飛
認為,詩從來都是自己言說自己,它是一種自為的語言,也是一種本能的、情感的、審美的方式,所有的詩歌,即使是最客觀的詩歌,都是關于人自身的詩歌,因為詩歌主要處理的不是思想和事件,而是人以何種方式與這些思想、事件達成一致和融洽。感性是詩歌的出發點和歸宿,對理性的有節制的疏離是使現代詩歌“切己”和“動人”的重要方式,它不是對思想的回避,而恰恰使思想和事件的深度意味自然而然地沁人心脾。(《一首好詩應如一個精美的“容器”
》,《詩潮
》2014年10月號)●倪志娟
指出,女詩人們的成就不應再被簡單籠統地納入“女性詩歌”概念中。詩歌創作不是一場足球賽,它是一個歷時性的過程,包含著代際的傳承、積淀和拓展。女性詩歌不僅為其龐大的讀者群帶來了無限慰藉,發揮了巨大的情感啟迪功能,而且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女性詩歌正在糾正我們的詩歌傳統中過于偏狹的男性經驗、男性審美趣味和男性言說方式。如果我們承認這個世界不應該只是由智力與男性荷爾蒙主宰,而應該包含著情感、寬容與慈悲,那么女性想象方式的不斷注入將糾正我們的心靈模式,使詩歌更為普遍。(《女性,如何創作詩歌而不只是女性詩歌
》,《詩潮
》2014年10月號)●張清華
認為,海子詩歌的某種“神圣”性質,以及海子在人們心中的崇高地位,使對他詩歌的解讀人性化了。這當然是必要的也是合適的。但需警惕的是,這種“神圣的人格化”也使人們對海子詩歌的理解被“壓扁”了,也就是說,他的豐富性被壓抑和刪減了,比如他那類具有情色意味的詩歌,也就變得無所依托。事實上海子不僅有相當曲折和豐富的戀愛經驗,這些戀愛經歷還在他的詩歌寫作中留下美妙痕跡。如果不從文本出發,他的單面的悲劇形象覆蓋了我們的閱讀,海子就會有被單質化的危險。(《關于海子詩歌中肉體隱喻閱讀札記
》,《上海文學
》2014年第10期)●沈奇
指出,單從精神層面看來,新詩以“啟蒙”為己任,其整體視角長期以來,是以代言人之主體向外看的,可謂一個單向度的小傳統。其實人不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地緣,都存在不以外在為轉移的本苦本樂、本喜本憂、本空本惑,這是詩歌及一切藝術發生學之本根。反觀新世紀以來的當下中國大陸詩歌寫作,其主潮性流向的關鍵問題,正是在于與現實生活的關系實在是過于緊密了,是以“鬧”,是以“泛”,是以“輕”,乃至成為本該跳脫而生的現實語境的一部分,所謂“枉道而從勢”(孟子語)。(《“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上海文學
》2014年第10期)●劉波
認為,真正的詩歌批評,最終還是與批評家的探索視野和思考深度有關,這一切都離不開“入心”,而現在不入心的批評實在是太多了。冷漠的肢解分析,晦澀的概念演繹,龐大空洞的總結,這樣的文字可能是“學術”,但惟獨見不到批評者的情感投入和靈魂落腳處,這樣的批評更談不上是一種文學創造。和好詩在民間一樣,真正的詩歌批評在民間。民間意味著要與主流話語權力保持距離,這樣或許更有利于看清處于臨界點上的詩歌和詩壇。(《何為入心的詩歌批評
》,《南方文壇
》2014年第5期)●高博涵
認為,卞之琳童年的安適條件,以外在影響形式培養了詩人相對富足的心態,個人經歷的相對順暢,結合詩人個人氣質,最終形成了他較為平和、沉靜、處事不驚的性格。這樣的性格在面對世界時,自然擁有更為客觀、直面的姿態,也更能呈現出現實世界的復雜色調,當這些姿態與體驗融入詩人創作中,作品就很能帶有相對沉穩、真實并多元的詩歌主體與基調。(《論卞之琳1930—1934年間的創作心態及其詩歌
》,《文藝爭鳴
》2014年10月號)●姜濤
指出,所謂“大詩學”,應該超越現有的學科限制,以詩歌討論為進路,與世界、與人之存在的根本問題發生聯系,進而朝向一種更廣泛的“思”。打破有形的現代學術體制,這是“大詩學”之為大的一個方面,而跳出現代性“裝置”來思考“現代”,能保持對無形的思想機制的警惕和反省。希望能在大與小、內與外、“詩”與“思”、“史”之間形成一種開闊而又內在的動態分析視野,不斷將外部問題轉化為詩的內部問題,也不斷從詩的內部、從特殊的歷史與美學狀況中提出重大的思想課題。(《“大詩學”與現代性困境中的穆旦問題
》,《文藝爭鳴
》2014年10月號)●奚密
指出,總的來說,朦朧詩在集體話語中肯定個人的尊嚴,在黑暗時代里思考生命意義。準確地說,大部分的朦朧詩都可視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現的“傷痕文學”的一支。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在于對“文革”的批判和對歷史的反思;它們采取的語調或哀悼,或譴責,或悲痛。這種廣義的傷痕文學更多地建立在集體式的宣泄而非個人理念的基礎上。(《“狂風狂暴靈魂的獨白”:多多早期的詩與詩學
》,《文藝爭鳴
》2014年10月號)●傅天琳
認為,詩的準則是遵循和維護自然的天然狀態。就是說在物與物、人與人、人與事的種種關系中,最詩意的就是一種渾然天成的自然狀態,也就是原生態。異化了就不是詩,人為地去破壞這種自然狀態就是詩歌的敵人。達到了這自然法則,詩歌就有了童話般的貞潔和美,沒達到或者弄彎了,詩歌就充滿了憂悒和苦澀。
(《露珠和雷霆:詩歌在對望和呼應
》,《海燕
》2014年10月號)●彭逸林
指出,詩歌也許什么用處也沒有,但它吐露了人性的常識。這種常識是那些把自己的人格從現實中分離出來的歌者從幻象的畫外吹送而來的,世俗的紛擾把它們掩埋了。我們需要詩歌,一是因為我們需要它來表達常識價值,它本身就是我們創造的行為現象,我們在其中展示內心的糾葛;一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結構中安排了一種召喚,那是人性的召喚,我們必得在幻想中提煉人性。沒有這兩點,詩歌就會滑稽失態、含血噴天、焦灼而亡。(《在詩歌的幻想里提煉人性的常識
》,《紅巖
》2014年第5期)●劉毅清
指出,中國詩歌從來無需與哲學一爭高下,無需為自身證明。這首先就在于中國詩歌具有的世間性特質,即中國詩歌建立在對生活現象本身的真實的肯定之上,以對日常生活的真實現象的直觀呈現作為最高的審美標準。中國詩歌里的人與天地一樣共存于自然宇宙中的一極,天地人被認為是平等的。中國詩歌最高境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默契交流,人與自然之間是興來如答,情往似贈的關系。中國詩歌里的人從來不是遺世獨立的,而是處在無限延伸的人生關系當中。(《“為詩辯護”:宇文所安漢學的詩學建構
》,《文學評論
》2014年第5期)●阿芒
的詩歌觀是,詩歌是荒野,大于人的荒野,無止無盡,人可以進入其中玩耍、探索、冒險,幸運時能解決生命的困惑、不舒服,更幸運時能有私人的新發現。當從這種“荒野體驗”回來時,會帶回新的比例尺,重新校準人生的比例、生命的節奏。(《阿芒的詩
》,《星星
》2014年第10期)●陳超
指出,詩應該是為詩而存在。它不但應有能力回避仿哲學的“深度”,也要有勇氣藐視寫“日常生活”這個新的權勢話語。它是、也應是語詞的探詢、歡愉和傷感并不借重藝術之外的力量,發現那些只能經由詩歌藝術發現的東西,而不是其他。詩應該準確地用詞,最好同時注意到該詞的詞典意義和你個人“語義偏移”的雙重準確性。如果無力兼顧,首先應考慮詞典意義。(《新詩話:龍蟲并射
》,《鐘山
》2014年第5期)●殷卓瑄
認為,雍容平和的社會對唐詩形成了質的規定:高遠樸實,自然干凈。傷感詩哀而不怨,絕不悲悲戚戚、呼天搶地;揭露詩含威不露,絕不義憤填膺、尖酸刻薄。文如其人,詩為心聲。唐詩是表達,是敞開,是唐代社會的真實反映,是唐人精神風貌的生動描繪。唐詩是不可以仿造的,是不可復制的。詩人或許就是這樣的混合體——在童真與深刻中游走,惟一不變的是一顆干凈敏感瘋狂的心。在如今這個紛繁多元的時代,許多瘋狂的行為都被視為正常,偏偏一個瘋狂的詩人卻難有立錐之地。在物質主義的溫床上,詩人無所適從;在消費的狂舞下,詩人落落寡合,痛苦而孤獨。(《詩歌的盛唐哪去了
》,《文藝報
》2014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