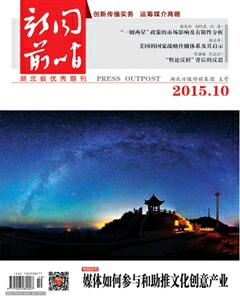從突發事件看謠言傳播及控制
◎陳淦璋 甘勇
從突發事件看謠言傳播及控制
◎陳淦璋 甘勇
謠言傳播古已有之。本文主要論述了新媒體環境下,在遭遇突發事件時,謠言形成的源頭、機理以及加速傳播的趨勢,研判了控制及治理謠言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并提出應該采取積極搶占輿論主陣地、繼續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強網絡法制建設和網民自治等舉措。
突發事件謠言傳播控制
引言
每當突發事件發生,謠言就會成為輿論傳播的一個突出現象。此次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發生后,冒出一些質疑和不滿的聲音,以及各種各樣的說法。有細心人對互聯網上出現的十大謠言進行了盤點,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還嚴肅查處了360多個傳播謠言信息的微博微信賬號。
正如美國學者卡斯·R·桑斯坦教授在《謠言》一書中所言:“互聯網時代,每個人都有可能是謠言的制造者、傳播者,但都會是受害者”。在筆者看來,新媒體環境下的謠言傳播,已經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一些特征,要控制并治理謠言,惟有認清本質,方能對癥下藥。
一、謠言形成的源頭和機理
1.個人認知的有限性。
每到突發事件發生,總會冒出一些“或許這意味著”、“這背后隱藏著秘密”的聲音,看似公正,實則揣測成分多。此次天津港爆炸事故中,“CNN(即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在華報道遭官方掐斷并組織毆打”的文章或視頻在微信群里傳播甚廣,最初在真相不明的情況下,一度被視為中國缺乏信息公開的“鐵證”。
然而,隨后CNN在其官方社交媒體賬號上發表聲明,稱直播是受到“在爆炸中傷亡人員家屬和朋友的干擾,而非天津官方”。也有事發現場的網友直言,CNN記者拿起一個手機就開始自拍報道,顯然惹怒了周圍仍沉浸在悲痛中的群眾,“誤認為”這個老外是在自拍作秀,也就有了后來的干擾拍攝。

隨著越來越多信息的披露,這一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筆者認為,突發事件發生時,處于第一現場的民眾,必然是能夠先于媒體發布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的。他們的聲音,也會通過社交平臺廣泛擴散。然而,因為個人認知的有限和未知世界的無限,或是個人被負面情緒或其他情緒籠罩,難免失之于偏頗。而圍觀的網民,未到現場,又普遍是依靠主觀經驗來判斷是非,有的在傳播過程中還出現了理解偏差或是添油加醋。當這些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信息,在新媒體環境下廣泛擴散時,有的甚至出現了與事件全局、發展邏輯相背離的情況。而這,也就是謠言產生和傳播的溫床。
2.對“控制感”的本能需求。
人的安全需求的三個層次,是確定感、安全感和控制感。在危急時刻,尋求控制感是一種較為常見的心態。人們都希望能夠更好地掌控周圍環境,而大前提,是能夠搜集到足夠的信息進行梳理分析。然而,危機時刻的消息傳播零散、模糊,人們面對著不確定,面對著無法理解的狀況,可能就跟抓落水稻草一樣,相信并傳播未經證實的信息,并獲得了一種控制和掌控局面的幻覺。
例如,此次天津港爆炸事件后,“污染物借風已擴散到北京,呼吁大家購買防毒面罩”的謠言開始傳播。從地理上出發,根據天津和北京的方位、風向,短時期內是不可能“順風”吹到北京的。然而,這樣的傳言不顧最基本的地理常識,越說越“真”,傳播量越來越大。這可以看出,人們對于控制感的需求如此之強,對于這個“可以確定”的負面結果,相信至少可以用購買防毒面罩的方法來控制、防范,而不是其他更可怕的不確定性。
從這個角度出發,意味著謠言是有“市場需求”的,也是一定會冒出頭的。而災難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會放大謠言背后的心理需求,讓人們更加關注個人安危,發自內心地感到焦慮。同時,根據恐懼管理方面的研究,死亡焦慮還會讓人們更加固執,可能更加膚淺地依賴主觀經驗來判斷信息真偽。結果就是,當災難發生時,這些機制一同發揮作用,人們在謠言面前格外缺乏抵抗力。
3.傳受主體的交織變換。
結合上述分析,張冠李戴、判斷失準導致了一些謠言的發生。例如,天津爆炸事件剛發生沒多久,“送血車輛已經從天津南站出發前往醫院,呼吁沿線車輛讓路”的消息獲得廣泛轉發,消息落款還是天津交警這樣的權威部門。盡管這是好心傳播正能量,但后來經過辟謠,這其實是天津交警在8月5日發布的一則公告,當時是為了救助罕見血型的小女孩。
好心辦壞事之外,還有一些謠言,可能出自惡作劇心態,就是希望吸引眼球,例如有湖南待業青年閑著沒事,謊稱是自己制造了天津爆炸,引發網友廣泛跟帖,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更有甚者,謠言可能來自于“別有用心”地炮制,“有所傾向性”地引導。
不管謠言的起點如何,人們能切身感受到的是,新媒體環境下,無論是“現場見證者”,還是“從朋友的朋友處聽說”;無論是通過微信、微博等移動端,還是在貼吧、博客等電腦端,一有重大事件發生,越來越多的網友在第一時間提供了信息,并加入個人情緒和看法。隨著關注度提高,這進一步吸引更多的網友加入討論,以致越傳越真乃至“三人成虎”。
應該說,新媒體環境下“人人都有麥克風”,這也就相應地就出現了“人人都是接收器”現象。當傳受主體產生了交織變換的連鎖反應,也就持續助推謠言的傳播。再加上自媒體高速發展,媒體門檻大幅降低,傳統媒體時代的“把關人”防控體系被消解,消息無論真偽都在恣意傳播,網絡上自然充滿了大量未經證實的消息。
二、謠言加速傳播的新態勢
1.傳播的低成本和求證的高成本。
新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的成本相比過去大為減低。正如前文所說的,智能手機能上網能拍照,微博、微信又掌握在網民(即“自媒體”)手中,其在傳播速度上的優勢巨大。
在天津港爆炸事故發生后的幾個小時內,隨著大量未經證實的消息出現,有一些被“大V”演繹成段子甚至謠言廣泛擴散。有細心人梳理了其中的十大謠言,分別有“天津人事變動”、“天津市區空氣污染”、“有害氣體擴散”、“CNN記者在華報道被官方人員阻止并毆打”、“8歲男孩需要RH陰性A型血”、“微博尋人”、“呼吁為血車讓路”、“呼吁周邊人群趕緊去醫院檢查身體”、“乙醚罐爆炸”、“一小區全滅”。
還有鄭州晚報微信公眾賬號,身為傳統媒體客戶端,其新聞編輯在未向權威部門求證的情況下,就將微信朋友圈中所謂的“天津市主要領導調整”不實消息編發成微信預覽,并發布至其新媒體微信工作群和其他新媒體平臺,帶來了進一步的強擴散,產生了相當惡劣的社會影響。
作為“意見領袖”的“大V”,普遍是明星、學者或社會精英,粉絲動輒上萬,他們傳播的消息無論真假,都容易被接受。而“大V”術業有專攻,并非全知全能,要是隨手轉發一條消息,顯然比認真花時間求證消息來源、作者背景、事件起因更便捷。
傳播一條謠言實乃“舉手之勞”,求證、辟謠的成本卻成倍增加。這顯然會導致兩種可能,其一,“大V”們要是代表了正確的輿論方向,會引發認同和點贊,可以比較合理地引導輿論。相反,“大V”們隨意轉發一條謠言,相當于是一個議題設置,則會對謠言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成為謠言傳播、擴散的重災區。
筆者還留意到,微博像“廣場”一般,不同的信息在此對沖,相互驗證,至少還有被網友列舉真相、進行自我辟謠自我凈化的可能。而微信朋友圈的封閉式傳播環境,且具有強關系型的傳播形態,自我糾錯能力弱,謠言發了也就發了,無人核實也就無人舉報,或者,一定要到有外力介入,才會刪除謠言,因為求證和辟謠的難度更大。
2.訴求的多樣化和影響的嚴重性。
先有立場,再有認同。作為人的情感,無論是喜悅還是恐懼,都會對認識事物產生作用。很典型的例子,是天津消防戰士的“我爸是你爸,記得給我媽上墳”微信截屏,獲得大量網友點贊并廣為擴散。而有消息稱,這位消防員已經安全返回,為這次全民感動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正能量”之外,需要正視的大背景是,當前我國正處于轉型期,拆遷、討薪等各種社會矛盾交織。一些民眾受到不公待遇,自然有著維護自身利益的訴求。而突發事件的網絡輿情治理愈發多元化,也是利益訴求多元化的體現。至于不滿、懷疑、無聊等各種情緒,更是增加了人們信謠與傳謠的概率。
更有一些“輿論搭車”現象,就是利益訴求人借助某一熱點事件,抱著“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思想進行發聲。有的時候,甚至不惜扭曲事實或者干脆制造謠言,而目的就是希望引起媒體和輿論的關注,能夠就此解決自身訴求。
此外,商業利益驅動,也成為滋生謠言的一大推手。如天津爆炸事件迅速成為網絡熱點,各類品牌蠢蠢欲動,有的給出了藥物使用和傷口清理方法,有的打出了“情懷牌”,還有的迅速抓住熱點宣傳企業形象。
應該說,網絡輿情失真問題,特別是網絡謠言問題,已經開始引發各界關注。《解放軍報》今年1月23日刊發題為“某些微信隱藏‘看不見的手’”的評論文章,指出某些微信公眾賬號是為了“從根本上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推動“政治轉基因”,對中華民族施行“拔根去魂術”。文章認為,依法關閉這些賬號,是維護國家和民族最大利益的必然選擇。
三、對謠言的控制及治理
當今互聯網影響巨大,網絡信息安全、網絡謠言治理、網絡輿論引導等問題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看來,這些問題不可輕視,因為不僅僅關乎到行業發展,而且影響到了國家安全。
1.積極搶占輿論主陣地。
過去,謠言通常以口頭形式在人群中傳播,偶爾也印在報紙或雜志上,或者傳播于電波中。但是,負責任的出版者和廣播電臺作為“把關人”,至少還控制著那些道聽途說的消息,盡量避免傳播謠言。
現在,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互聯網時代,這些道聽途說的消息會瞬間傳送至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用戶,會出現“蝴蝶扇動翅膀引發海嘯”的效應,進而形成了有影響的民間輿論。
當前更應該認識到的是,互聯網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過去互聯網在電腦端,打開電腦才能上網,主要覆蓋群體是思維活躍的中青年;現在互聯網正向移動端轉移,掏出智能手機,隨時隨地就能上網,連大叔大媽級別的老年群體都開通了微信,真正實現了“移動互聯”。其次,移動端讓碎片化的時間得到充分利用,等個電梯的功夫,就會刷個微信朋友圈。再次,蘋果iwatch、谷歌眼鏡等可穿戴設備已經面市,表面上它們只是電子設備,實質上它們通過數據交互,將來很有可能發展為人的器官延伸,再一次助推信息化。
在社會輿論日益復雜化、多變性的當下,一種較為權威的聲音發出,可以更好地促進社會共識的建立,減少不同利益主體間的情緒摩擦。搶占輿論主陣地,特別是更好地利用互聯網渠道,已經刻不容緩。
筆者以為,在互聯網時代,既要加快培育主流力量,擴大官方“大V”的輿論影響力,讓正面聲音不斷擴大,更要注重發揮傳統媒體的導向作用。新形勢下,傳統媒體或許面臨重大挑戰,但其多年的積淀,能考量每一條信息的準確性和真實性,并用專業視角深度挖掘,作出跟進性報道。向全社會傳遞條理清晰的資訊,發出客觀公正的評論,設置充滿正能量的議題,是傳統媒體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當然,對于傳統媒體自身來說,如何更好地順應大勢,積極運用新媒體技術,創新報道方式,回應社會需求,提供更接地氣的內容,在重大事件和熱點話題方面及時發聲,依然是重要課題。
2.繼續提高信息透明度。
信息的公開、透明與及時,是最好的“謠言粉碎機”。
在突發事件發生后,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召開新聞發布會,就掌握了議程設置的主動權。而向闡明政府對事件的態度和處置方法,傳遞的是正面信號——這是一個負責任、有能力、強大的政府,顯然有利于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動事件處置。
反觀此次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公眾的關切、質疑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官方發布的消息姍姍來遲,二是官方自身對情況掌握不全,“不清楚”、“不了解”成了發布會上的高頻詞。
有研究人士指出,當前政府信息公開存在“五多五少”現象:形式上公開多,實質上公開少;結果公開多,過程公開少;原則方面公開多,具體內容公開少;公眾被動接受的多,主動申請獲得的少;公開“正面”信息多,公開“負面”信息少,特別是政府工作失誤、不足乃至違法的信息少之又少。
而在突發事件出現時,屢屢有一些部門錯失權威信息披露的先機。其后果是,隨后即使公開再多千真萬確的信息,卻因明顯滯后,導致政府公信力大受損傷,深陷所謂“塔西佗陷阱”——哪怕說了真話,也難以取信于民。
按照《人民日報》的看法,按照“最壞的可能”來發布信息,反而為事件處置贏得了主動。新聞發布應該理解、尊重和順應公眾心理。不應糾結是否要把最壞的可能性告訴大家,就算公眾的承受能力有限,但有心理準備總比沒有好;即便證實事情沒那么嚴重,也不應擔心下不了臺。事情有好轉,大家總會愿意接受,情況由壞變好、損害由重變輕,其實跟公眾內心的期望是合拍的。
3.加強網絡法制建設和網民自治。
應該說,當前輿論場的新重心,已經轉向移動端,尤其是以微信、微博、(微)視頻、客戶端為代表的“三微一端”。
而按照美國《華爾街日報》今年7月報道的說法,中國社交媒體的謠言集中營,尤其集中在微信,在可信程度和轉載程度方面,都遠遠超過其他社交平臺。剖析其原因,不僅是微信活躍用戶基數大,已經突破了5億。而且,親朋好友通過微信發來信息,屬于強關系屬性,自然信任程度高。加上有些謠言乍一看很有道理,自然會給予主動轉載。
因此,要控制并治理謠言,加強網絡治理是重要手段,其根本又在于依法治理。關于互聯網的立法,美國就有130多部之多;而新加坡對在網上發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等言論的,都會依法入罪。而直到2014年10月,我國才出現了首例微信傳謠訴謠案。安利(中國)將一刊登2篇安利謠言文章的微信公眾賬號告上法庭,象征性索賠一元并要求其道歉,通過司法途徑反擊了針對企業的微信謠言。應該說,當前我國對于網絡謠言的立法和執法尚處于空白期,仍待進一步健全。網絡謠言不屬于言論自由范疇,可對網絡謠言如何司法認定,還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同時,有必要在執法程序、量刑原則與依據等方面,加強立法和相關法治建設。
同時,對于網民個體來說,應該樹立依法、科學、正確的網絡言論觀念,至少是看到疑似謠言做到不主動轉發、不主動傳播。對于一些社交媒體的認證用戶尤其是“大V”來說,更應該謹言慎行,為自己的言論負責。不僅如此,還應注重網民理性精神的培養,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崇尚真實,反對虛假造謠信息的社會風氣,從而從根本上降低網絡謠言的影響力。
(陳淦璋:湖南日報;甘勇:湖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