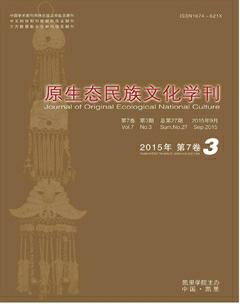從加池鄉規民約看清水江流域鄉村社會運行情況
簡麗
摘要:為深度了解清水汪流域社會運行機制,從加池鄉規民約對鄉村社會運行的規范和制約作用八手,主要考察了加池寨鄉規民約變化內容及其社會背景、鄉規民約中對事件處理等三個方面來解讀清水汪流域鄉村聚落的運行機制。
關鍵詞:清水江流域;鄉規民約;清水江文書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5)03-0065-08
加池寨位于黔東南的清水江流域,海拔600多米,行政上隸屬于貴州省錦屏縣河口鄉。寨子位于河口鄉的東北部(河口鄉鄉政府所在地為河口村),清水江的東南岸,西北邊與南路村隔江相望,北部則是與同處清水江南岸的文斗村相鄰,而西南部則是同錦來村相靠,東南部則與九佑村接壤。加池寨的祖祖輩輩都生活于此,據說加池寨的祖先是在宋朝時期從江西吉安府遷來此地。當時宋朝在吉安府地區實行大屠殺政策,祖先們為了逃命就來到此地,后來就在此安家落戶。當時搬來五兄弟,其中有兩兄弟在此居住下來,另外的三兄弟搬到其他地方,留下來的兩兄弟就發展成為9戶人家。至今這9戶人家已發展到186戶,968人。加池百姓從明清以來“靠山吃山”以經營林業為生,在林業經營過程中形成了以林業管理活動為重要內容的鄉規民約。本文是在2014年8月在清水江流域加池寨進行田野調查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初步研究。該研究主要涉及到鄉規民約中有關林業方面、社會治安管理方面變化以及當代鄉規民約在社會治安方面懲治等方面內容,探討了清水江流域社會生活中火災、偷盜、搶劫、賭博等事件處理,以此認識清水江流域鄉規民約對該地區鄉村社會制約和規范作用。
一、鄉規民約中有關林業管理方面的變化
在此次田野調查中,筆者分別收集到了1997年和2012年實行的鄉規民約,通過對比發現,這2個版本的鄉規民約前后發生較大變化。
2012年版本的鄉規民約與1997年版本的相比,刪減了很多規定和條例,尤其是在山場林木管理和社會治安管理方面。在山場林木管理方面,1997年的鄉規民約對山場界限、木材采伐管理和本村木材出售管理做了13條規定。在這13條例中明確的規定了山場糾紛處理、濫砍亂伐需罰款以及進行木材統一出售機制等。而2012年的鄉規民約則只簡單的規定“嚴禁無證砍伐山上樹木,違者自愿承擔違約金300-500元”。
2012年的鄉規民約中在山場這方面的規定已經從1997年的12條演變成現在的1條,先后出現如此大的變化,筆者認為這與該地區1999年林地保護政策以及林權改革有很大的關系。1999年國家在這一地區頒布實行“自然保護林”政策。國家將部分林地劃為自然保護林,村民無杈對劃分的林地進行砍伐和木材交易。2006年12月黔東南地區啟動錦屏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省級試點。在林權改革中,國家依據各戶人口,劃分山場面積。相對過去契約之下的山場管理,現在村民對自己山場林木的管理權限和范圍明顯變窄,自己經營管理的山場變少了,可以進行的樹木貿易也相繼減少。同時國家在林業管理這方面,直接以法律的形式對相關山場、林地進行規定、管理,鄉規民約再對山場進行規定也就沒有多大意義。因此,鄉規民約中也較少的涉及,只是簡單的說明了民事糾紛由誰解決及罰款等問題。
二、鄉規民約中關于社會治安管理懲治方面的變化
在社會治安管理方面:1997年的鄉規民約在偷盜行為、破壞行為、賭博行為、打架斗毆行為、罰款兌現以及本(外)村人在外(本)村違法的處理進行規定。然而2012年的鄉規民約中明顯的減少。例如,在偷盜行為中,1997年的對劫倉劫物、偷盜牲畜等有7條的規定而2012年的中卻沒有規定。不僅是在偷盜行為這方面,在賭博行為和打架斗毆、罰款以及本村人在外村違法和外村人在本村違法的處理等規定相繼刪去。2012年版本的鄉規民約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方面都屬于國家法律的管轄范圍,超出鄉規民約約束管轄的范圍;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國家法律法制的不斷健全以及法律宣傳工作的深入開展,這使得人們對法律有一定的認識與理解。如果有違法亂紀的事情發生,都需按照國家法律條文來進行處理。因此鄉規民約對這方面的規定也就相對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的鄉規民約更多的涉及民事糾紛的解決處理機制和火災懲處。這一方面說明寨中民事糾紛、火災等較頻繁,同時也說明鄉規民約在這方面有很大的約束力。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國家法律的普遍性。雖然國家出臺了諸多的法律條文,但是國家是站在國家的高度來制定法律,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然而村落由于具有其特殊性,有很多事情都超出法律條文之外,因此在某些事情上根本沒有相關的法律條文來進行解決。所以很多事情需要由村寨的習慣法和鄉規民約進行解決,因此在某些方面,鄉規民約的規定對國家法律進行補充,發揮了國家法律無可替代的作用。
2012年的鄉規民約繼承了先前鄉規民約的部分規定。例如在破壞行為方面,1997年鄉規民約在破壞他人山場、牲畜財產以及公共設施等方面有相應的規定。2012年的鄉規民約也對防止破壞他人物品及公共設施做了詳實的規定。例如第11條:“保護消防基礎設施,不準擠占、圈占、蓋壓、遮掩消防設備,不準隨意借拿消防器材影響村寨人飲水消防用水安全的行為;不準年輕力壯人員發生火情火警后不參加撲滅,只顧搬東西的行為,違者除恢復原狀,批評教育外,還應上交違約金100-200元。”又例如第15條“加強對村寨古物的保護,凡損壞古井、古樹、古碑、寨門、亭閣等公共財產,除承擔修復費用外,承違約金100-300元。”禁止村民破壞古井、古樹、古碑、寨門、亭閣等公共財產說明了村民對自身周圍環境的愛護,這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鄉規民約的作用。
同時2012年的鄉規民約還增添了很多時代性規定,例如第4條:“提倡從簡節約,反對浪費,提倡厚養薄葬;樹立尊敬長者,孝順老人之風。有不贍養老人、虐待老人者公開批評,責令改正。”又例如第7條:“提倡文明進步,反對迷信,不準裝神弄鬼,信邪八邪。”以及第13條:“提高水陸交通安全意識,不駕駛也不乘坐‘三無船舶、‘三無車輛,不在夜間,雨凍等惡劣天氣強行出車出船,違者承擔違約金30元。”2012鄉規民約對出現的新形勢和新事物以及過去習慣法無法涉及的內容都進行補充,這目口適應新的形勢,也豐富和補充了習慣法的基本內容,使得習慣法能與國家法律對接,很好的治理地方社會。
三、當代鄉規民約中社會治安管理的懲治
(一)關于火災的懲治處理
明清時期,加池寨木材貿易興盛,如今的加池子孫仍然保留著祖輩留下的山場。豐富的木材也就成為其建筑材料,這也造就加池寨獨具特色的干欄式建筑。木質房屋美中不足的在于其易引發火災,加池寨的祖先們早已注意到此問題,在鄉規民約的制定中散了詳細的規定。
通過采訪了解到,加池寨發生過3次較大的火災,分別是民國35年(1946年)(另一說法為民國36年)、1962年和1978年。民國35年(1946年)的那次火災燒的面積最廣。當時是學校旁邊的一所房子起火,木房的主人外出干活,家中只有其4個兒子和2個女兒,孩子們在做飯時不慎引起火災,導致全寨都燒光了。據說無人員傷亡,但整個寨子都將近燒光,除了四合院。至于四合院為何沒有被燒,姜齊有老人告訴我們說,眾人討論、分析四合院幸免的原因,一方面因為四合院離火源地較遠,不易受到影響,而且四臺院旁邊有一口古并,縱使不幸殃及,救火也較為及時、容易;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四合院屋頂蓋的是瓦片,縱使火苗落到瓦片上,也不易引起火災。據說民國時期四臺院較為富有,屋頂蓋的是瓦片,而普通的房子都是用的杉木皮。第二次較大的火災發生于1962年,由于私人做飯不慎引發火災,村寨公路左邊都燒盡。第三次就是1978年的那次火災,燒毀了幾十戶人家。
木質結構的房屋極易引發火災,這種現實狀況引起村民對此高度重視,因此在鄉規民約中有明確的規定和體現。鄉規民約中對火秧頭有明確懲罰規定。1997年的鄉規民約就規定:村內火警,每發生一次火警,驚動鄰居而未造成火災的,不管老幼罰款50元以上,重犯加倍罰款,并且還要喊寨兩個月。這也就是說,引發火災要進行罰款。如果是燒到自家,沒有波及他家,就只罰100-200元,燒到其他家的就700 -1000元。如果沒有錢,則拿自家木材,自留地等來抵擋。家境貧窮的罰輕點,罰款則上交村委,用來買消防用品,例如滅火器等。另外鄉規民約還規定:燒至10戶以上的之災的火秧頭,本村人員有權將其驅逐出原地基,并責令其遠離村寨居住或交給上級有關部門罰辦。將火秧頭驅逐出地基的這種嚴格懲罰,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得寨中的火災沒有頻繁的發生。雖然鄉規民約中規定本村人員有權特燒至10戶以上的火秧頭驅逐出原地基,但據了解,加池寨卻有將一引發火災的婦女趕出寨子,而鄉規民約的規定是將火秧頭驅逐出原地基,那為何婦女是被趕出寨子呢?村委為何沒有按照鄉規民約的文本來處理這個問題,代之以更加嚴重的懲罰?這是否意味著村民間存在無形的其他鄉規與民約。婦女受到如此重大的懲罰,毫無疑問,這一次的火災受災面積較大,可能在另一方面,村委有“殺一儆百”之意。但是反過來想,一位婦女被趕出寨子,如果是一位剛嫁到加池寨的婦女,究竟是將其一個人趕走還是將其同愛人一起趕走?如果是將其一個人趕走,這是否意味著拆散其因緣,那家族祈求添丁、延續香火的愿望該如何實現?若是將這對新婚夫婦趕走,其公公婆婆誰來贍養,香火又如何延續?若是一位已經生兒育女的婦女昵!將其趕走,其孩子該怎么處理!所以將婦女趕出寨子的懲罰是否過于嚴苛,并且處理方式不合乎文本鄉規民約、是否臺理都值得更深入地探究。但不得不承認,其嚴苛的懲罰制度使得村民事事小心留意,不釀成火災,不給個人、全寨帶來損失。
鄉規民約中不僅建立了房屋火災的懲處機制,對于山場火災也進行了規定。對于山場的火災事故,1997年鄉的規民約規定:如有意放火燒山的,除用其肇事者自留山之木抵足被毀之木外,還要責令其在被燒所有面積更新造林每畝罰款5元,所造林的標準按上級營林公司的規格標準(及成活率達95%以上)并管理直至撫育成林,方可交給原山主管理,不慎失火者,同上得罰。關于山場火災事故,寨中幾乎沒有發生過。這說明山場火災的規定對村民有約束作用。有這樣好的山場經營管理環境,一方面是由于嚴格的懲罰制度給村民的威懾力,文本中明確規定損壞他人的山場,用肇事者的山場木材或者自留地來進行賠償。另一方面,當地人經濟收八主要來源于山場,因此對山場資源十分看重,一旦山場失火,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可估量,因此村民也積極防治山場事故的發生。
遭遇火災后,寨中還有相關扶持政策。遭受火災后,一方面,國家民政會對受災地區進行補貼。村委將災情上報,國家下發賑災物資,例如糧食、衣服、被子等。國家賑災救濟在很大程度上幫助災民度過困難,但村寨自行扶持更重要。若受災嚴重,村委則會發起募捐活動。村委會負責書寫募捐倡議書,并張貼到各村,以此來進行募捐,在本村也會有募捐。募捐物資統一上交村委,村委再按照受災戶的戶口數進行分配。村民間另外一種扶持就是送物品以及勞動力的支持。災后的重建工作有極大的困難。一方面是房屋及物品的損失,在重建中,最重要的是材料及勞動力的需求。我們訪談了解到,如果某家受災后,在修建房屋的過程中需要某些特殊尺寸的木頭,鄉里鄉親一定會贈送,有時還會幫其做部分的重建工作,并且有些村民捐贈物資是直接給受災戶的。因此在鄉村這個家族社會、熟人社會,受災后的相互援助十分必要的。
為加強寨中防火防盜工作,寨中實行了相關制度。加池寨先后組織了民兵隊、治安隊及聯防聯保組。民兵隊是最早的社會治安組織,主要負責消防、偷盜、亂砍濫伐等工作。民兵隊設有隊長,成員則要求是從18周歲至45周歲的男子中挑選組成。一個民兵隊10人左右。后來民兵隊改名為治安隊。治安隊的性質則和民兵隊相差無幾。現在寨中則實行聯防聯保制度。聯防聯保制度實行于2000年,由寨中各個區域的人組成聯防聯保組。聯防聯保組每組由10個人組成,主要負責其附近區域的火災、偷盜搶劫事件的緊急處理。聯防聯保組既有男性也有女性,雖然在某些突發性事件上女性不能給予較多的幫助,但該組中有女性則表明聯防聯保制度的合理性和人性化。
“打更”制度是一種提醒村民注意用火的火災預防制度性措施,雖然加池寨的村規民約中并沒有將其做為一種制度寫八文本,但在鄉村中有實行。寨中若有20多天沒有下雨,就有人去“打更”。加池寨的這種打更不同于一般的夜晚打更,“打更”的時間一般在清晨或者晚上五六點鐘,在整個村子喊叫,叫村民注意防火。“打更”的人會手拿大鑼,敲一下喊七八聲。“打更”的人是由村里安排,一般會固定為某一個人,如果安排的人不愿意,就會去換人。打更也不是完全的義務勞動,政府會給予“打更”的人定的補貼,例如現金和糧食。
另外,“打更”還作為一種懲治措施,即使“喊寨”。“喊寨”作為一種懲罰主要是針對引發火災的火秧頭。如果受災戶達到10戶以上不僅要交罰金、還要喊寨2個月。這一方面是對火秧頭的懲罰;另外一方面也是對其他村民的一種提醒,一是要注意防火;二是增加成為火秧頭要其喊寨,承擔相應的懲罰。
(二)關于偷盜、搶劫等事件懲治及處理
社會秩序的好壞直接關系著該地的生產生活能否正常的進行,為此,在社會秩序方面,加池寨鄉規民約中對此的規定規范了社會秩序。
通過查閱鄉規民約,發現其中對偷盜的規定較多,并且對于偷盜的懲罰一般都為加倍賠償。據調查了解寨中發生的偷盜事件幾乎沒有發生。這也就說明嚴厲的懲治規定在褰中起到了作用。例如,在偷盜牲畜方面規定:偷盜耕牛,生豬者,除追退失主生豬耕牛外,每頭每次罰款500元,如果盜的豬、牛已售出和不能再繼續喂養的,可按當時市場價格估價,加倍賠償失主,并要補償失主的一切誤工費,還要交與公安機關。例如:盜偷田培養的魚,按失主說損失的數額加倍賠償外,每人每次罰款100元,重犯和加倍罰款。再如:偷盜別人的稻草,每一籠罰款2元。偷盜他家財產不僅要物歸原主,還要加倍賠償損失及其誤工費。就以偷盜牲畜為例,偷盜的每一頭豬罰500元,若變賣了不僅要按市場價進行賠償,而且還要補償失主的誤工費。偷盜田里的魚,不僅要按失主所說的損失加倍賠償,還要每人次罰100元。在1997年,進行偷盜后被抓,每頭牲畜賠償這么多,這將是一筆不小的賠償數目。也正是這極其嚴重的懲罰,使諸多有偷盜念頭的人止步,使得寨中的盜賊較少,寨子多了幾分寧靜與安心。
在有些時候,偷盜事件發生后,沒有運用鄉規民約來進行解決處理,但在另外的意義上卻也是鄉規民約。若是一個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人進行偷盜,被抓后,無錢賠償,這時該小偷賠償物主的資金是否按照鄉規民約進行,該如何賠償等問題交由該小偷的家族出面進行解決。面對這種情況,則就沒有完全按照鄉規民約來進行處理,因為鄉規民約中也沒有對此種情況進行規定。但這種方式是鄉規民約規范中的特例,所以特殊情況特殊解決,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鄉規民約的體現。
在有些偷盜情況下,是運用某些極端的方式進行解決。調查了解到,在解放前就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當時是國民黨變野年,人們生活較為艱苦。本寨有一家人3口,在另外一個人家做月工。當時月工會發一定的工錢以及一些米。有一天,他倆父子在那家干活,母親去替雇主春米打對。由于生活艱苦,她母親在那家偷了幾碗米,后來拿回家。兩父子當時在火邊吃飯,母親在敲門,兒子開門看到母親拿米回來,就知道母親的米是從那家偷過來的。兒子和父親都認為母親這種行為影響聲譽,如果將其交給地方按照鄉規民約來處理,一方面沒有面子,自家竟然出了小偷。另外一方面,家里沒有山場來抵押作為賠償。鑒于這樣,于是父子和謀,將母親捆綁,仍到河里溺死。偷米的事情就以這位母親的死而結束。這倆父子沒有按照鄉規民約來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鑒于聲譽,另一方面是更直接的沒有物質來進行賠償。也正說明了鄉規民約的懲治力度大,這家沒有能力來按照鄉規民約的規定來進行賠償。雖然這個案例雖然不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不是按照鄉規民約來解決的,但說明了鄉規民約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以及其懲治的嚴重性。
在鄉規民約的規范下,偷盜事件減少。同樣在鄉規民約中對搶劫也進行了規定,然而搶劫的情況卻不一樣。面對規定,為何還是有人以身試法呢?1997年的鄉規民約中規定:劫倉劫屋的,除退回其所盜的全部臟物外,并按被盜價值加倍賠償失主,每人每次罰款300元,無款兌現以家產作抵,并押送公安機關視情節處理。從這條規定可以看出,搶劫和偷盜懲治相差不多,歸還所盜竊贓物,并且加倍賠償及罰款,只是較偷盜牲畜的罰款來講罰款的金額少一點,可還是有一起又一起的搶劫事件發生。
在調查中,我們了解到在1995年發生了一起搶劫事件。加池寨有一個收購頭發、牲畜的商人被搶,搶劫的人原以為他很有錢,但其實沒有,最后搶劫犯被抓后,退了臟物,還簽定了協議。搶劫者被抓之后,如果能歸還贓物,商議賠償金額,就能達成和解。達成和解后雙方簽訂協議,此后雙方就當此事沒有發生。但有時候和解后并不意味著這事情就結束了,有些人會不滿意村委的處理,會去對處理該事件的人進行報復。但這樣的事情會很少,村委會的人很注意事情的解決方法,其次是這樣的事情發生后,解決起來也就比較棘手麻煩。
在寨中有些搶劫犯罪案件有可能不會發生,但是由于家人的縱容使得搶劫事件發生。姜齊有老人告訴我們加池寨有幾戶的家長極其不負責,縱容其孩子去搶劫。曾經有一戶人家,孩子的父親已經去世,母親一個人帶孩子。她兒子萌發了搶劫的念頭,于是去河邊挖了沙子,準備晚上搶劫時用。若搶劫時被老板發現,就將沙子扔到其眼睛中,他還想在沙子中摻辣椒末,以致無法辨認出兇手是誰。于是他回來就問他母親:“媽,有辣椒末沒?”他母親說沒有,她又問她兒子要辣椒末干什么,兒子回答說“我要”。他母親說你要我就春一把給你,也沒有問他兒子究竟要辣椒末要干什么。于是他母親就燒火爐,用炕來烘干辣椒,春好給了他兒子。拿到辣椒末后,她兒子就將辣椒與沙子拌著,晚上就去搶劫,并且還將物主打傷。在這個搶劫事件中,其母親未對其子要辣椒末干什么進行追問,一般來說辣椒末是用來做萊,可是其兒子不做菜,那他用來干什么很值得懷疑,可是其母沒有,反而臨時舂辣椒末給他。可以說她縱容了犯罪行為。最后他被抓到,受到了相應的懲罰。這個事件的發生,可以看到這母子有明知故犯的嫌疑,因為在鄉規民約中對搶劫事件的懲罰規定也較為稀少。可能更多的是那種僥幸心理,以為不會被抓被查。搶劫這種事件不能存僥幸心理,既然損害了村民的利益,罪犯一定會被抓到,運用鄉規民約和法律對其進行制裁。
家人縱容犯罪的還有一起事件,該事件發生于2007年,搶劫的是一伙青年。搶劫犯采用的手段就是用墨將自己涂黑,以致無法辨認。墨水搶劫的人是4-5個未上學的學生。為了弄到墨水,一個孩子就回家問其爺爺有無墨水。他爺爺也未問明其要墨水干什么,就告訴他書房有墨水,于是他就拿著墨水去作案了。很明顯,墨水是用來書寫的,除此之外也無其他常用的用途,這位爺爺就這樣的縱容其犯罪是很不負責的表現,并且最后承擔了惡果。這次墨水搶劫的金額是2000多元。事情敗露之后被抓,每人罰款2萬元,并且搶劫頭目判刑13年零6個月,現在仍未釋放。毫無疑問,罰款及八獄的處罰無疑是很重,但令人不解的是村規民約中并沒有如此重的懲罰規定,并且這個數目的贓物金額,法律的判決為何有13年零6個月這么長。由此可見,鄉規民約僅是對寨中與村民相關的較小的事情進行制約與管理,而情節嚴重,觸犯法律的則運用法律來進行處理。所以對于一個微型社區,鄉規民約的規定是具有極大的效力,也正是這種效力將社區正常運行。
在解放前,如果村里有搶劫殺人事件,要解決此事,首先找村里保長。在保長的處理下,若能找到殺人兇手,按照條例該殺就殺,該槍斃就槍斃。然而在國民黨時期,如果找不到兇手,則會讓村里的人湊錢,埋葬死者。如果是搶劫案件,僅僅幾十塊錢,由家族內部自己協調解決。如果是搶劫等大事件,則由司法解決。由此看出在解放前、民國時期對偷盜搶劫事件處理與現相差無幾,這一方面表明鄉規民約的繼承與發展。另一方面也就說明鄉規民約是實現村寨管理和良性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寨不僅有單槍匹馬,4-5個人組成團伙去搶劫,甚至還有過土匪寓。四合院的姜紹烈老人告訴我們,在解放初期,加池寨的河坡角苗坡灘有一個土匪窩經常搶劫河中過往的船只。當時,鄰村南加定貨的船時常往來于清水江中,這窩土匪就搶劫了貨船,并且還打死了幾個人。當時有6艘運貨船經過加池,貨船上裝的是銀子、布匹、針線等物品。當時貨船上還請了保鏢。但這窩土匪還是搶劫了貨船,并且還打死了一個船家胡老剛和瑤光的李宏毅。對于這個事件是如何處理,姜老沒有講清楚道明白。但我們可以看到,鄉規民約在搶劫案件的規定上較為薄弱,如果搶劫的懲治有像偷盜那樣的嚴,那怎么會有土匪團伙的出現,這也就說明了某些人對鄉規民約蔑視。南加的貨船上請了保鏢,這也就說明搶劫事件發生的較多,既然連鄰村的人都知道防搶劫,那加池寨的鄉規民約中為何沒有嚴令村民遵規守紀或者實行更為嚴重的懲治制度?
鄉規民約中對偷盜搶劫事件的懲處規定,一方面以其嚴格的懲治制度確保村落社會秩序的穩定,另一方面,鄉規民約在搶劫事件的規范上還存在不足,這也是寨中搶劫事件頻頻發生的原因之一。
(三)關于賭博問題的懲治處理
加池寨也有聚眾賭博的活動,關于賭博,鄉規民約對其也做了規定。賭博活動在明清時期就有,此后民國、解放后一直都有存在。姜以鋒就告訴我們:他的一位太太(不是妻子)熱愛賭博,曾將一個觀音形輸給人家。還有一個本寨的人,曾經很有錢,后進行賭博將其一雙金筷子都輸給別人,最后落的傾家蕩產。鄉規民約中規定:發現有聚眾賭博的當場抓獲的除沒收其賭博工具和在場人員的全部贓物外,每人每次罰款50元,如有抗拒而又行兇的交公安機關處理。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加池寨的賭博活動較為頻繁,但沒有禁止的舉措。由現在的社會治安來看,加池寨的賭博活動的規模較小,如果規模大,必然有大型賭場,并且有一批一夜暴富或者一夜傾家蕩產的人出現,這樣村寨的偷盜搶劫事件就會頻繁發生。但是在小賭中也不慎輸光資金,那該如何處理?
為了獲得賭資,那些賭博的狂熱分子會不顧一切的去籌集資金去繼續賭或者還債。賭資、還債的來源方式有正規和不正之分。理性一點的就會松手,本本分分種田或者外出打工來進行還債。有些冥頑不靈的人就會去搶劫偷盜,尤其是偷盜牛馬。這也就與偷盜搶劫等扯上聯系。
調查了解到賭博活動最多的時候是在民國時期和解放后的90年代。在民國時期,寨子里的賭博活動盛大,很多人都輸得厲害,一旦輸光了錢財,常常會拿山場、田地去抵押。實在沒有錢后,就采取不正當的手段,去偷去搶,這也是國民黨時期,偷盜搶劫事件頻繁發生的原因之一。在那時,在平常趕場時,都經常有三五成群到人少的地方去搶劫,不反抗則就將其物品帶走,若是反抗就會將其殺害。
鄉規民約中未對賭博活動進行嚴格的懲治,雖未有大型的賭博活動,但因賭博而引發的社會秩序問題卻時常發生,由此可見,鄉規民約的制約不到位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治安問題。
四、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清水江流域鄉規民約對鄉村聚落的規范制約作用。清水江流域的村民“靠山吃山”并且歷代以經營林業為生,因此鄉規民約中的規定對林業管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國家法律法治的不斷健全,在林業管理方面鄉規民約已經失去過去作為法律性條例的意義,因此鄉規民約中也減少了與林業相關的規定。也正是這樣使得鄉規民約更加注重社會治安管理,從而穗定鄉村聚落社會。在鄉規民約規范社會之下,鄉村聚落是否存在習慣法與國家法律的二元制對立?若有,鄉村聚落和政府是怎樣調和此矛盾,雙方又以怎樣的一種形式實現鄉村聚落習慣法與國家法律法規結合,以及為此采取哪些舉措等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