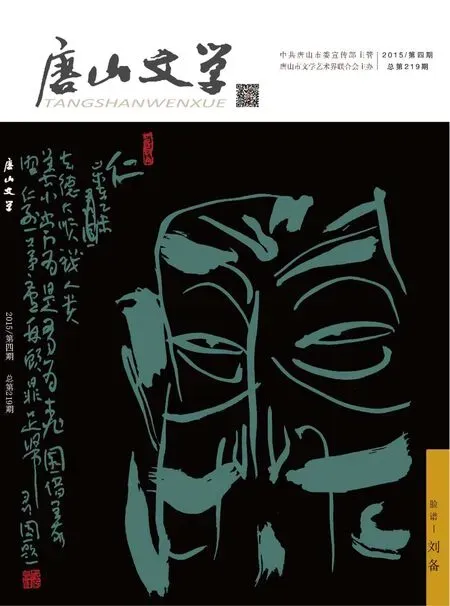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對伍爾芙小說《到燈塔去》中的隱喻所暗含的女權主義思想的分析
王恬
一、引言
弗吉尼亞伍爾芙(1882-1941)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意識流”小說家、評論家,是二十世紀倫敦著名的布魯姆斯伯里文人團體的靈魂人物。伍爾芙的小說以擅長于人物心理刻畫的“意識流”寫作為主,以細膩的筆觸捕捉人物內心的每時每刻的變化,具有極強的畫面感和理解力。而伍爾芙在小說中使用的大量的隱喻,在刻畫女性內心情感和活動上,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本文將從認知隱喻為出發點,分析在伍爾芙代表作《到燈塔去》中,作者使用的大量的隱喻,是如何在表達女權主義思想,表現女性內心方面起到關鍵性作用的。
對于《到燈塔去》這部小說,國內外學者對其進行了許多方面的研究。從其中所采用的“意識流”寫作手法到體現的女權主義思想,中外學者都有一些論著進行了分析和探索。在丹尼爾?蒙卡(Daniel Munca)在其文中對這一點作出了相當詳細的論述和分析。在許多學者看來,茱莉亞?史蒂芬與拉姆齊夫人有許多相似之處,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和妻子,她投身于慈善事業,并且掌管各種家庭事務,照顧每一個人,在與男性權威發生沖突的時候,選擇讓步和自我犧牲,甚至會主動維護男性的主導地位。而莉莉?布里斯科則代表著那些因為自我意識萌發,而強烈需要自我證明的新女性。
她們或許困惑、或許時而自我懷疑,但是她們已經摒棄了傳統的維多利亞式婦女的自我價值認定,即依附于男性的價值認定,或者這種舊式的價值體系在她們的世界里正在逐漸坍塌之中。伍爾芙以創作莉莉?布里斯科這樣一個角色,進行自我的女權主義思想的表達和訴說。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名女權主義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對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體(the Subject),是絕對(the absolute),而她則是他者(the other)。男性長期將女性邊緣化的社會結構,在此時遇到新的挑戰。 莉莉?布里斯科經歷的心理過程,反映出伍爾芙作為一個年輕女作家,要立足于男性長期占領的文學領域,必須克服所遭受的困難和質疑,最后自我戰勝的過程。《到燈塔去》是一部關于人生、女性和死亡的小說。其本身就是一個隱喻。在時間上的延續性和不同女性價值觀的承接,在時間和空間上,也形成了一個具有鮮明方向感的隱喻,在其中,新老的更替、周而復始的輪回、人們對自我的懷疑到摒棄,再到重塑和新生,都與小說“到燈塔去”這樣一個主題暗合。
作為認知科學的一個分支,認知語言學主要研究語言和認知途徑、認知方式之間的關系。在萊可夫和約翰遜合著的著名認知語言學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作者明確的指出,隱喻充斥在我們生活中無所不在。隱喻并非單純是一種語言的現象,其產生并不是在語言的產生之后,而是人類思維的產物。隱喻在人類思維形成之后,便存在了。通過將一個領域事物結構的相似性映射到另一領域中,從而人類可以理解到不同領域的事物。概念隱喻常常包含著一系列的常見的映射,從而將不同的領域事物聯系起來。它可以準確的表述出類似于經驗、感官知覺等更為復雜的人類思維的成果。因此,在《到燈塔去》中,許多晦澀而深奧的隱喻,如果用映射理論去分析,就會領會到伍爾芙獨特寫作手法所隱含的深意。
大多數學者對于《到燈塔去》這樣一部小說中的隱喻,作出了一些認知語言學的相關分析和研究。但是,目前對于這些隱喻在伍爾芙表達女權主義思想時,所起到的作用,以及隱喻本身所隱含的女權主義思想,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旨在結合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對《到燈塔去》中的隱喻,作女權主義層面的探索與研究。
二、《到燈塔去》中的隱喻與女權主義思想的表達
(一)“To the Lighthouse”
“To the Lighthouse”是統領整個小說主旨的隱喻。相對應的是LIFE IS A VOYAGE這樣一個隱喻。作者將此隱喻映射到女性人物的命運中。對女性而言,這個過程是一個飽含著時間性和宣言式的隱喻。從受到男性主導而并沒有自我存在感的舊式女性,以拉姆齊夫人為代表的以服從并維護男權為主的女性,向以莉莉?布里斯科為代表的具有自我意識、追求自我價值的新女性過渡的這樣一個過程。新的女性價值體系必然代替舊的價值體系,這就是女性群體最終會迎接的“光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性,而這種信念就像燈塔一樣具有方向的引領性。
這個過程的開始必然首先遭到男權主義代表人物拉姆齊先生的反對:
…‘But,’ said his father, stopping in front of the drawing-room window, ‘it won’t be fine.’ [1]3
拉姆齊先生的反對是不留一絲余地的,男權在維護其不容動搖的地位時,對女性的生存訴求采取的是殘酷的壓制和徹底的鏟除。拉姆齊先生對天氣狀況的粗暴而武斷的預言,暗含著對女性在尋找生存契機的壓制與否定,這種壓制與否定是對當時社會整體環境的一種男權至上主義不可動搖的自信,和對女性改變現狀能力的輕視和不屑。
(二)描寫拉姆齊先生的隱喻
伍爾芙在描寫男權至上主義的代表人物拉姆齊先生這一形象時,采用了許多生動而精確的隱喻:
…It was a splendid mind. For if thought is like the keyboard of a piano, divided into so many notes, or like the alphabet is ranged in twenty-six letters all in order…[1]24
在伍爾芙看來,一個以所謂的理性而充滿科學精神的男性的大腦,起結構就像“鋼琴鍵盤”或者“26個字母表”一樣排列有序。這種以女性思維和情感模式為出發點的對男性的觀察,體現出一個女性主義者對男性統治和駕馭世界的方式的不滿和無情的嘲諷。在伍爾芙看來,在男權統治下的社會,是違背人類情感自然法則,以及武斷呆板,單調乏味的社會,是冰冷的物質主義社會。
同樣,對于男權至上主義所鼓吹的成就,伍爾芙也運用隱喻進行一番生動的論證,揭示出其脆弱的一面:
…So she always saw, when she thought of Mr. Ramsay’s work, a scrubbed kitchen table…but upon a phantom kitchen table, one of those scrubbed board tables, grained and knotted,whose virtue seems to have been laid bare by years of muscular integrity, which stuck there, its four legs in air. [1]17
此處伍爾芙通過莉莉?布里斯科的心理活動將拉姆齊先生的成就形為一張實用的結實的木質餐桌。顯示出對于男權社會傾向于主張物質主義的諷刺和批判。“一張木質餐桌”這個隱喻,映射到現實中,批判了男性思維和行為模式中注重實效,認為多余的情感表達和心靈溝通都是無用的思想。這種批判的效果,因為隱喻的使用,遠比用文字直接表達更為深刻、生動和富于張力。
(三)描寫莉莉?布里斯科的隱喻
莉莉?布里斯科是伍爾芙在小說中自身的折射。因此,在描寫這樣一個新女性的奮斗過程中,伍爾芙在刻畫心理活動時,使用了大量隱喻。準確而細膩的表現了一個女藝術家為了實現自身價值過程中,內心活動的復雜性,以及沖突、矛盾的產生和化解。正因為有了隱喻的使用,使這種女性內心的迷茫感、困惑感和無助感表現得尤為真實可信。將女性內心細致敏感,脆弱而又堅韌的特點展現得比較豐滿立體。
…She saw the color burning on a framework of steel; the light of a butterfly’s wing lying upon the arches of a cathedral. [1]35
這一段描寫中,表達了強烈的女性主義思想。而這種表達是完全通過隱喻來實現的。作者通過莉莉看見“色彩在鋼鐵的框架中燃燒”、“蝴蝶翅膀的色澤停在教堂的圓拱上”。可以想象,“燃燒的色彩”映射的是年輕女性藝術家的才華,但是并不能自由的燃燒,只能是在男權至上的鐵的框架內燃燒;而“蝴蝶(映射到女性)翅膀的色澤”無法在天空翱翔,最終停靠在“教堂(映射到男性權威)的圓拱”上。這種深刻的無奈感和受壓迫感的描寫,是作者對男權社會壓迫女性的直接控訴和反抗。也直接體現出女性在撼動男性主宰的世界時,面臨的阻力和困難。
…Of all that only a few random marks scrawled upon the canvas remained. And it would never be seen; never be hung even, and there was Mr. Tansley whispering in her ear,‘woman can’t paint, woman can’t write…’[1]35
這一段落的描寫,有一個重要的隱喻,就是莉莉要完成的畫作。這一隱喻和“到燈塔去”這一主題,一直并列貫穿于小說的始終。畫作的內容并沒有特別的描寫,但是人物完成畫作的心理過程卻刻畫得非常細膩。完成畫作的過程映射到現實中,就是伍爾芙確立自己在文學領域地位的過程中,為了實現自身價值,所經歷的與男權主義的壓迫進行抗爭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尋找“燈塔”的過程。莉莉從不被承認的黑暗中,不斷被男權至上主義的擁護者坦斯利先生提醒“‘woman can’t paint,woman can’t write…’”,不得不到維多利亞式婦女的代表拉姆齊夫人那里尋求安慰,但是拉姆齊夫人為代表的傳統婦女在婚姻中尋求人生安慰、實現人生價值的道路,被莉莉否定。她的價值觀,并且由此價值觀所帶來的焦灼感,并不能由婚姻來實現和解決。最終,莉莉獲取了一種新的存在方式,也完成了畫作,實現了自己的追求。伍爾芙以畫作的完成這個隱喻,向世人宣告女性的一種新的生存狀態和價值觀。
小說中的具有女性主義思想的概念隱喻映射模式可以表達如下:
源域(source): 目標域(Target):
The lighthouse →The freedom of woman
The travelers →woman characters
Lily’s painting →achievements of woman
Burning color →the talents of woman
The butterfly’s wing →the talents of woman
The steel framework →rules set by the man
The arches of the cathedral →rules set by the man
Vision → the dreams of woman
三、結語
“意識流”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芙在寫作中,通過對隱喻這一寫作手法的嫻熟的運用,揭示出女性內心活動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展示了女性的生存狀態和訴求。對于女性該如何確立自身價值,如何堅持精神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作出了非常深刻的思考。這種思考完全區別于伍爾芙以前的女性文學作品,以獨立于男性給女性預設和規范之外的女性生存主張,重新定義了女性這一群體的價值和生存模式。同時也喚起了20世紀文學領域對于女性生存與發展的思考與關注,為新時代女性的生存價值探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 Woolf , Virginia. To the Lighthouse.[M]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4
[2] Lakoff, George and Johnsen Mark.Metaphors We Live by.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3] Munca, Daniel. “Virginia Woolf’s Answer to ‘Woamn can’t Paint, Woman can’t Write’in To the Lighthous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an’s Studies, 4 May (2009)
[4] 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ume 34,4 Nov
[5]波伏娃,西蒙娜·德,陶鐵柱譯,第二性[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2,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