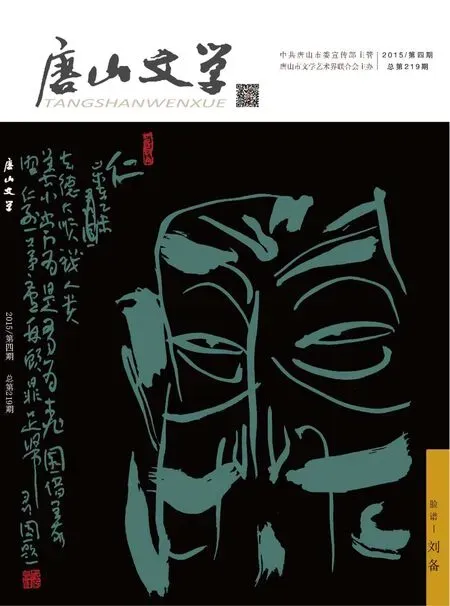精神還鄉——評遲子建新作《群山之巔》
劉皓
手頭是遲子建的新作——與《額爾古納河右岸》相隔十年問世的長篇小說《群山之巔》。小說很顯然是作家的一次精神返鄉之旅。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長篇小說領域進行多種藝術嘗試——內容上涉獵東北少數民族生活與東北城市生活、形式上每本長篇小說都變換敘事手段——之后,作家再次回到自己的藝術起點,即以一種詩性、曉暢的純粹的語言,和一種緊湊、精致的小說結構,講述一個情節不算難懂的東北故事,總體來說,作品的確呈現出幾乎是“百煉成鋼”般的美好的審美姿態。在這部新作中,作家摒棄了一切“花哨”的手段——第一人稱內聚焦敘述、日記體敘述、動物第一人稱敘述,等等,呈現給讀者的是第三人稱全知敘述之下的一個山區的故事。沒有濃墨重彩的形式的遮蓋,故事的本相便以洗盡鉛華的方式自動展開在讀者眼前。
一
小說主線極其簡單。松山腳下龍盞鎮屠戶辛七雜的養子辛欣來回家后不久,即用斬馬刀斬殺養母,后又偷光家用,并強奸了鎮上人視之為神仙的侏儒女安雪兒,藏入深山。安雪兒之父,當地法警安平對辛欣來展開追蹤,最終在松山深處將辛欣來歸案。
盡管不具備我們在自“現代派”以來常見的所謂“花哨”的小說形式,《群山之巔》卻并非在形式上毫無“機心”的作品。遲子建最初步入文壇時,正像當時大多數作家一樣,是以中短篇小說寫作而“出道”的。中短篇小說最講求結構上的精致,如何在講述一個故事時為讀者布下“陷阱”,設下“餌料”,都需要作家精心營造,好的中短篇小說如園林如樓閣,處處有景,處處“驚喜”。獲得過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的遲子建更是深諳此道。
小說并不是一開始就將血案展現在讀者眼前,而是以這樣的描述開頭:“龍盞鎮的牲畜見著屠夫辛七雜,知道那是它們的末日太陽,都怕,雖說他腰上別著的不是屠刀,而是心愛的煙斗。只要太陽好,無論冬夏,辛七雜抽煙斗是不用火柴的。他的兩個褲兜,分別裝著一面拳頭般大的凸透鏡,和一沓樺樹皮。抽煙斗時他先摸出凸透鏡,照向太陽,讓陽光趕集似的簌簌聚攏過來,形成燃點,之后摸出一條薄如紙片的樺樹皮,伸向凸透鏡,引燃它,再點燃煙斗。”在這第一個出場的人物身上,有一定閱讀史的讀者可以辨析出的人物特征是:閑散,適意,更主要的是,人物已經浸淫于生存環境中較長時間,與之水乳交融、相處融洽。
這樣的“淡化”的散文式寫法,不是作者為拖延敘述時間而采取的手段,而是一以貫之。小說中每一人物出場時,均采用這一寫法。先“點名道姓”,再指出其出身、職業、主要故事,不疾不徐,娓娓道來。如此寫法,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上世紀四十年代登上文壇、八十年代貢獻出一批優秀短篇佳作的小說家汪曾祺。《故里三陳》、《職業》、《異秉》等作品多以此方法引讀者“入彀”。早在2002年的訪談中,很少接受訪談的遲子建就曾暢敘自己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家的看法:“張愛玲的語言比較老舊,讀起來卻很有滋味;蕭紅語言俏皮幽默,少一些滄桑。當下很多小說的故事很好,但語言不好。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小說語言都比較不錯,有一種古典優雅的風格。他們之所以成為大家,是和這種精湛的語言密不可分的,說到底,文學畢竟是語言的藝術。……王安憶的語言魅力,耐琢磨。有些走紅的作家的文學語言比較差,那么即使他的故事再新穎,我也不承認他是一個成功的作家。” 不難看出,作家對汪曾祺的作品是懷有強烈好感的。而形式上的散文化,就是遲子建與汪曾祺在創作上不約而同的選擇 。散文化的寫作,是遲子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步入文壇開始即十分偏好的藝術手法。“從小說文體的特點看,它不可能和話劇一樣,人物一上場就是緊張連續的矛盾沖突,它可以更散淡、更隨意一些。小說中的風景描寫、心理描寫等等看似邊角廢料,卻在作品中起到很有成效的作用,能夠使作品有特別的意味。考察屠格涅夫、川端康成的小說,如果去掉了散文化的東西,故事本身就失去了耐人尋味的韻致。也許我是女性作家的緣故,我的小說敘事節奏比較舒緩,形成了散文化的傾向。”
這里要捎帶提及遲子建對汪曾祺式寫法的發揚。“散文化”、“慢”、“淡”、“抒情詩化”等等,是汪曾祺這位于1980年代以特殊風格重出文壇的短篇小說家的標簽。在這位小說家的筆下,蘇北水鄉風俗、人情以白描的方式躍然紙上,作家語言白而熟,不帶一絲火氣,人物也安于自己一番和諧融洽、頗有情趣的小日子,而這種創作特色,在今天這個語言傖俗化、網絡化甚至“火星”化的寫作時代至為難得。汪曾祺式的寫作在21世紀的學術界之所以依然時常被作為創作典范處理,也與這種“難得”的精神密不可分。遲子建在這部小說中“反其道而用之”,反將這種散文化的處理用作對東北松山根深蒂固的惡的揭示,其間也許滲透更多的是作家對人類的悲憫情懷。而正是這一點,讓我們看到了久已熟悉的遲子建。可以說,如果沒有形式上的散文化,小說中密布的惡所帶給讀者的沖擊未免尖銳,審美價值也就蕩然無存了。
二
小說如傘骨狀打開,龍盞鎮各具面貌的人物如線上珍珠紛至沓來,讓讀者見識到了他們的惡。這其中有制度的惡:陳金谷從作龍山林場場長開始即動用職權,給誘騙來的妹夫唐漢成許以職位,不僅如此,他的一家,原來是盤根錯節的地方一霸,其弟陳銀谷是青山縣副縣長,小舅子和小姨子一個是松山地區財政局副局長,一個是計生委主任,其一兒一女,一個是松山地區公安局副局長,一個在林市環保局工作。如此令人錯愕的裙帶關系式腐敗,恰恰見出遲子建的巴爾扎克式觀察力:在我國邊遠或落后地區,這種裙帶式腐敗積久不變,樹大根深,幾乎形成地方的“世襲制”管理。而且,越是邊遠,越是落后,這種狀況只怕越是嚴重。對“官員腐敗”的表現不止于此,遲子建接著在“格羅江英雄曲”里格外點出了龍山深處的罪惡權肉交易——女大學生唐眉與女護士林大花主動作駐軍部隊團長和營長的情婦一事,林大花在本章主人公安大營的注視下與營長過了一夜,第二天即獲得重金酬勞。
不僅有制度之惡,更有時代之惡。小說揭出一樁三十年前的罪惡,作為傘狀展開的故事的“傘柄”的關節部分。這便是七十年代知青返城時劉愛娣與陳金谷的一段情史留下的“孽債”——原來辛欣來是陳金谷的私生子。令人唏噓的是,這一往事的“挖掘”,起因竟是陳金谷雙腎衰竭時親子陳慶北不愿提供腎源——這又是個人之惡了。
小說中對個人之惡與群體之惡的表現,力度并不亞于對制度與時代之惡的表現。作家對人性的洞察力在這里作一總結。殺母、強奸、臨終理容師偷情而使殘疾丈夫在家中因煤氣中毒憋死,等等,隨著小說進程而一一聚散,難得的是遲子建并沒有止于對惡的淺層摹寫,而是將之變化為一個值得尋味的道德論題,如對“理容師偷情致殘疾丈夫死亡”一事,對殯儀館理容師李素貞內心的苦悶、對夫妻之情的極度渴望表現得一絲不茍,使得讀者不敢下奪命簽,不敢錯勘賢愚。同樣矛盾糾結的是小說中龍盞鎮鎮長唐漢成斗羊場上下黑手一事,唐漢成因保護山林自然資源考慮,不愿工程師開發本地的煤資源,于是對發現資源的單槍匹馬的工程師痛下黑手,買通斗羊師李來慶指引斗羊攻其不備。如此種種的惡,其中包含的況味,是不容細辨的:推算故事主體發生的時間,由“三十年前”的知青孽債一事可以得出應是新世紀初,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小說中表現的農民個體與群體形象還與魯迅、蹇先艾、王魯彥時代的鄉土小說中的農民形象極其相似。山之深、惡之深、惡之久,便更添觸目驚心。
“沖動的善良人”,是小說一個細心的設置。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鎮長唐漢成,小說中的法警安平,也是這樣的類型。在死刑改為注射行刑后,法警安平負責押送槍支上繳,途中飲酒后卻提槍奔下火車追兇,最后發現不是辛欣來,因失職而被病退。小說借由這類人物的設置,更將解決難題的希望徹底掐滅:原來浸淫在山區的非理性文化之中太久,所有人都抽身難退,沒人有能力實施自救。無論是被統一進倫理美的“人的價值”,還是在被統一進法制的公民的價值,悉數崩壞。換句話說,無論是作為康德所要求的道德律令的自律的道德,還是作為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公民道德,在這“也就七八十萬人口,卻有一個法國那么大的面積,境內群山環繞,無人區多,好隱蔽”的東北松山地區,都成為根本無力實現的對象。 積聚三十年,根深蒂固、不能撼動的惡,便進一步在這種反復書寫下呼之欲出。
三
也許是寫作《額爾古納河右岸》的“余震”效應,遲子建在這部新作《群山之巔》中依然采用了人類學的視野對筆下人物進行觀照。
為小說開頭的人物辛七雜,其驚人創舉就是絕育。絕育的原因是,他是日本人與逃兵的兒子。這一情節耐人尋味:辛七雜不久即接受抱養辛欣來,引發全篇的主線也隨之而來。“種”的問題于是進入到讀者視野。這種“一代不如一代”式的接力,不僅在漢人辛家是如此,在小說中唯一“善”的代表——鄂倫春族老英雄安玉順的安家也是如此:安家第三代就是智障的侏儒安雪兒。當我們對比松山一霸、盤根錯節的陳家時就不難發現,原來陳家代代健旺,陳慶北體檢年年合格。處心積慮經營龍山關系的陳家香火旺盛,不過是隨意落腳此處的辛家,和男隨女愿前來落戶的安家,卻遭受重創,致使我們聯想龍山為“可詛咒的群山”。同時,風葬習俗,繡娘最后的坐騎——白馬,安雪兒的替罪者身份,等等,也不難使我們聯想到《金枝》中一些饒有興味的段落 。
葉舒憲在《文學人類學教程》中“重建文學人類學的本土文學觀”部分中這樣寫道:“面對一個世紀以來西化的‘文學'和‘文學史'觀念的誤區,需要清理批判的三大癥結是:A.文本中心主義 B.大漢族主義 C.中原中心主義”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人類學之風吹過之后,人類學視野一直以零星的方式出現在作品中,而不再形成創作風潮。《群山之巔》中的人類學視野的出現,不足以構成對小說主題的沖淡,卻足夠形成一層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潛流,與小說敘事的“散文化”一起,沖刷著作品的河床,使之形成道德主題明晰、人文色彩濃郁、神秘氣息揮之不散的多重審美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