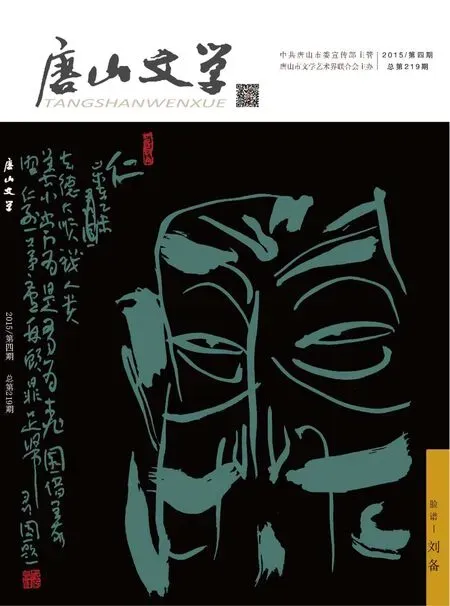玉蘭
劉曉靜
文學咖啡館
玉蘭
劉曉靜
曹妃甸工業區文學社社員作品選賞
她的故事就這樣走到了結局,以一種我似乎在心中鋪墊了很久但卻又很突然的方式。我記住了,她是一個女人,她的名字叫“玉蘭”。
與我們倆有關的第一場葬禮是在四十三年前。
那個晌午,天氣熱的連風都懶得在林子里逛蕩,只有知了還在傻不愣登的玩兒命號。不大的一張土炕上一頭躺著她因疾病死去的丈夫,另一頭躺著她襁褓中還在熟睡的小兒子。炕邊上其他幾個子女的哭喊聲輕易地就壓過了知了的聒噪,把玉蘭中年喪夫的噩耗傳遍了這個攏共就只有五戶人家的小山溝。
“他二嫂,二哥咋著也就是這病了,他成天疼的誒呀誒呀的誰聽了都揪心,去了,也就不遭罪了,你這么一大家子孩子呢,可得挺住啊!”村西頭的文三叔擔憂的看了看癱坐在炕上那個滿頭是汗的瘦小女人。“天兒熱,尸首放不住,這后事還得趕緊操辦,二嫂啊,叫人趕緊跑著去報喪吧,怕是明天來不及啊。”
“老大、老二已經去了。”玉蘭用幾近虛脫卻又清晰地聲音回答道。一下子進來許多人,讓原本低矮的兩間小屋里,顯得更加昏暗了。玉蘭沒有像孩子們那樣哭號,她腦子里清醒地知道發生了什么、該做些什么,只是心里卻憋悶得發慌,喘不過氣來,感覺就像把心放在空氣里腌著,一呼一吸都疼,但是卻嚎不出聲兒來,只有眼淚不住的沿著臉頰一路往脖頸子里流淌。“哦,那大家伙也別閑著了”,文三叔轉過身對著擠了一屋子的鄰里說:“都先緩緩,哭有的是功夫兒,二愣兒家的,你先幫著找找看看誰家還有白布,拆兌著縫點孝,先盡著二哥這五個孩子,三小子小也得戴,小坡你去后梁上通知小崗他爺爺,告訴他后天發送讓他帶著嗩吶過來……二嫂,二哥走之前壽材備好了么?”
“沒,”玉蘭哽咽著顫微微地扶著墻站起來,繞過丈夫,挪到了炕的另一頭:“他三叔,孩兒他爹走的突然,提前并沒有備下棺材,眼時俺也拿不出買棺材的錢,你看先用俺們結婚時打的這個板柜中不?”望著丈夫平躺在那里仿佛比平時還要頎長的身軀,再看看老板柜原就不大的體積,玉蘭的悲傷猛地敲碎了她用理智筑起來的隱忍長堤,她一下子跪坐在板柜旁,雙手死死扒住了那個老式楊木板柜的一角,只剩一層皮的手背上連血管都清晰可見的抖動著:“他爹啊,俺對不住你啊!你走了俺還得屈著你啊!俺沒法兒啊,俺以后一定不虧著你啊!他爹啊……”
村里的女人們趕緊圍坐到玉蘭身邊,文嬸用胳膊攙住了仰頭痛哭的玉蘭:“二嫂,你自個兒也得注意身體啊,你得顧著5個孩子,你可不能這么著啊,這里里外外的你還得操持著呢,聽話啊!”“是呀,二嬸子,你看你一哭,秀兒、小芬更不知道咋辦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勸慰著,玉蘭透過淚水看著在炕邊站著的兩個嚎啕大哭的女兒,母親的身份讓她拽回了一絲理智,她大喘了幾口氣抑制住了自己的哭號:“他三叔,就用這板柜吧,眼下俺這真沒有更好的法子了。”
“中啊二嫂,長嶺兒那邊這會兒沒了人也都是用板柜,就是這年景,你也別覺著太愧的慌,有板柜就不錯了!那就讓二愣兒他們幾個操辦著給二哥裝殮吧?”
“嗯,外頭的事兒就靠給他三叔了,別的都沒啥,二愣兒啊,你們先操辦著別的事兒,俺想給你二叔好賴換身衣裳,收拾收拾再讓他走。”玉蘭哽咽著撐起了身體,抬起了老板柜的蓋板,條理的把里面的物件拾掇了出來。
玉蘭丈夫的葬禮以村里固有的風俗被有條不紊的安排著。不一會兒人們開始到院子里分頭忙乎,屋子里一下子就沉寂了。玉蘭挨著炕沿兒緩了一下神兒,就下地去灶上點火,準備燒一鍋熱水。她呼呼地喘息著用力推拽著風箱,風箱也配合著賣力的發出呼呼地聲響,兩個女兒在一旁默默地往灶里添著柴火,娘仨蹲在灶臺邊上,聽著院子里嘈雜的聲響,誰也沒有出聲,屋子里一時間只聽到了風箱的響聲和灶里柴火燃燒時的嗶哩叭啦聲,只是玉蘭腳底下不時地騰起來的細微灰塵,讓人分不清楚滴到灶灰堆兒里的到底是汗珠兒還是淚珠兒……
水燒開了,玉蘭打了一盆水,仔仔細細的給丈夫擦了擦臉和手腳,為他換上了去年去北京看病時補好的齊整的衣服。都收拾好后,用剩下的熱水給女兒們煮了一鍋米湯。10歲的大女兒李芬熟練地抱起了餓醒了哭號的弟弟,一口一口的把碗里的米湯喂給了他。6歲的二女兒李秀抱著碗坐在門檐兒上吧嗒吧嗒的抹著眼淚。
過了晌午,風來了,知了反倒沒了興趣,看著風有一下沒一下的搖著院子里的杏兒樹,它也有一聲沒一聲的應敷著,好歹不是那么的悶熱了。全村都已經適應了玉蘭丈夫的死,各自忙乎了一陣子后,日子仿佛又如往常般平靜了。坐在門口楊樹蔭子底下縫孝的婦女們拉起了家常:“前兩天就看著李二叔臉色不大好,你說說,這人說走就走了,才四十多歲,怪可惜了的。”二愣家的一邊麻利的扯著孝布,一邊回頭向大門口張望了一下。“二嬸子這日子以后可難嘍,一大家子孩子,也沒個男人,也幸虧還有個老大,今年有19了吧?成個人了,多少還能支個事兒,幫襯一把。”
“幫襯啥呀,老大這年紀,二嫂還得想法子給他張羅婚事呢,你看著吧,又得是一攤子帳啊!”文嬸兒嘴里叼著幾綹麻條兒,雙手配合著使勁的把它們搓成了一股繩兒。“唉,到時候能幫就幫吧,他們家腦子活泛的老二,這下那學肯定也上不了了”。
“你別說人家李家這嫂子,瘦巴柴骨的,平日里看著話也不多,這一到事兒上還真鋼骨啊,你看人晌午那是一點也沒亂啊,這要放別的婦女身上,早沒了主意了。”小坡娘拉著手里的線,往四周掃了一眼,然后壓低聲音說:“這會兒誰在屋里跟著呢?你說也沒聽見二嫂啼哭馬虎的叨念啊!”
“你以為呢,李二嫂嫁過來之前,人家娘家原來就是地主,也是見過世面的,要不是因為成分不好,當年也不能嫁到這小山溝溝里啊。”
“怨不得呢,俺就說像咱們這種莊戶人家,死了一埋的事兒,哪有那么多講兒,你看他二嫂,又是給李二哥擦臉換衣裳的,到底還是不一樣啊。”
“有啥不一樣,都是女人,還是個命苦的女人,這年景,你看二嫂子瘦的,沒奶水,我看她家的三小子難養活啊……”
村里女眷們你一言我一語的閑聊著,隔著院墻,聽得到男人們在院子里張羅的吆喝聲。風吹過門前齊整整的白楊樹,忽扇的楊樹葉子刷拉拉的響,仿佛連它們也在為玉蘭的命運竊竊私語著,這一切的聲響混雜起來傳進了院子里老杏樹的耳朵里,樹上的青杏兒默默地又酸澀了幾分……
第二天夜里,玉蘭把三小子托給文嬸照看,她領著其他四個孩子跟著親戚鄰里們一起去后山的土地廟“抱廟”,按風俗迎回丈夫游蕩的魂魄。照理兒這一路上來回都不能出聲,只是在廟里貼冥紙的時候可以呼喚故去親人的名字,好讓他的游魂抱貼在紙錢上然后跟著家里人回家。到了土地廟,行過禮后,文三叔把冥紙發到大家伙兒手中,每人一張,因為每次只有一張紙錢會貼住,文三叔小心而又充滿敬畏的叮囑著:“都拿好了,一會兒別管誰的貼住了,其他人都得把紙錢交回來,在廟門前統一燒掉,記住了!”“放心吧三叔,都知道。”
所有人手里都拿著張紙錢,分散站在土地廟里里外外的墻面墻根處開始叨叨咕咕的叫起李二哥的名兒來。玉蘭定了定神兒,拉著小女兒秀兒邁進了土地廟的門口,在門右邊的墻角,玉蘭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著薄薄的紙錢,輕輕在距離墻壁一兩厘米的地方晃動著,嘴里小聲而又清楚地喚著:“孩兒他爹,回來吧,回家看看我們娘幾個,孩他爹,回來吧……”玉蘭還沒有喚出三聲,紙錢刷拉一下就貼在了墻上,玉蘭怔了一瞬,然后哇的哭了一聲:“秀兒,你看,你爹還是不放心咱們啊!”大家伙兒嚇了一跳,回過神兒后趕緊上前攔著“二嫂,這會兒不能哭啊!”“是啊二嬸子,貼住了是好事兒,得趕緊把二哥迎回去,要哭一會回家哭,在這可哭不得啊。”“老大老二趕緊扶住你娘!”“……”一時間勸的勸,扶的扶,玉蘭心中仿佛有滔天巨浪剛剛掘開一個口子,她多想不顧一切的放聲痛哭來宣泄自己胸中腌漬了許久的情緒,可是身旁的勸喝聲提醒她,現在她不能哭!她只能張大嘴大口大口的拼命啃咬著空氣,把胸肺間要涌出的聲音硬生生的噎憋了下去,那一年這個女人四十二歲……
與我們倆有關的第二場葬禮是在十二年前。
在間隔的這三十多年里,玉蘭從來沒有因為丈夫的離去而向周遭的人絮叨、抱怨命運的不公,也沒有因為生活的艱難而聽從娘家人的勸說往前再走一步。她一個人,默默地、堅定地守著馬犁溝里的石墻屋瓦、日升月落,守著五個不同年齡的孩子,傾盡一位母親的所有,把他們拉拔著全都長大成人,各自也都成了家、成了父母。我見到玉蘭時,她已經被歲月雕刻成一個標準的農村老太太了:背微微駝起,四肢干瘦,被陽光騰烤過的皮膚顯露出一種油醬色的光澤,上面爬滿了干癟的褶皺。她每每抱起我的時候,總是伴隨著明顯粗重的喘息聲,那是上一場葬禮后留下的哮喘毛病。這喘息聲伴著我走過了成長的歲月,我曾經幾乎認為玉蘭天生就是這么喘息的。她的子女們為了讓她行走方便,用紫荊疙瘩給她做了一把順手的拐杖,可是玉蘭卻從一直拒絕使用,她總說:“使不著啊,走個道兒能有多累?就是羅著個鍋子不方便唄,這點就喊累那還能干啥?我現在可靠不著它啊,留著吧,留著以后實在走不動了再使。”
十二年前的這場葬禮是在剛剛立秋的一個深夜。那一天的下午,玉蘭心里就沒來由的發慌,眼皮突突突的不住的跳。到了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出去給別人家落忙的大兒子并沒有像往常一樣按時回來。兒媳婦和兩個孫子陸續出了家門去尋。玉蘭知道出事了。當家里只剩下她自己的時候,她彎著腰,背著那個歲月在她身上壘起的記號,一步一挪的在院子里不住地轉悠,一會摸索摸索西墻邊新打的棒子,一會拾掇拾掇東墻根兒垛起來的柴火,累了,轉身就坐在場院的臺階上歇會兒:兩個胳膊拄在大腿上,眼睛不住地望向大門口的方向。院子里靜的瘆人,連平日里歡實的栓都栓不住的小黑狗都不叫了,老實的趴在窩邊兒打著蔫兒,空氣里只聽得到玉蘭費力的喘氣聲。
入夜,兒媳和孫子們由遠及近的哭嚎聲,讓守靠在大門口的玉蘭一下子蹲坐在地上,也把她老年喪子的不幸迅速擴散到了這個雖已經搬出山溝卻仍然依山而建的小山村里。鄰里鄉親們還是迅速的“聞聲而動”,陸續的涌進玉蘭家的院子,嘆息、哭泣、勸慰,接著就是照舊分工忙活。
如同上一場葬禮,玉蘭并沒有像其他女眷般從頭到尾聲嘶力竭的哭泣,在人們給大兒子穿裝裹衣裳的時候,她彎著腰佝僂著摸索到灶臺邊兒上,打了一盆熱水,用關節嚴重變形并且布滿粗繭的手沾著水,一下、一下的仔細給兒子擦了擦臉,捋了捋頭發……然后玉蘭就坐在炕沿上長時間的一言不發,直到后生們把大兒子抬進棺材的那一剎,玉蘭的淚珠兒毫不費力地的爬過了她臉上的溝溝壑壑,就像已經干涸了許久的河床上突然汩汩的冒出兩條細流,伴著玉蘭沉重粗濁的喘氣聲,平靜地洶涌著……
“二奶奶,我大伯是上好的地方享福去了,你可得往開了想啊”,“是啊二嬸兒,你可得挺住,不能讓大哥走的不安生啊”“……”玉蘭是馬犁溝村里在世的為數不多的老人,她平日里善良、堅強而又通情理的言行,讓她得到了全村人的尊敬。此時她的過分沉默到讓村里后輩們的心里都了沒底,專門叮囑了幾個婦女負責陪著她,也不讓她到大兒子的靈堂前去。對于大家善意的勸慰,玉蘭只是小聲的應付著:“嗯,嗯,想得開,我沒事兒”、“我可不哭他啊,這葬了良心的死小子……”“這一輩子啥沒經歷過呀,我沒事兒,別擔心,我挺得住……”玉蘭這樣說著,眼淚卻不像年輕時那般爭氣了,關也關不住的流著。
發喪的那天早起,秋老虎終于松了松口,肯讓人們順暢的喘口氣,涼風起了。我早早的到大伯的靈堂前點香,晨色朦朧中,我看到玉蘭一個人,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孤零零的坐在棺材旁邊的干草堆上,與其說坐,遠看倒更像是蜷縮著:她一只手肘支撐在膝蓋上,手掌托著額頭,另一只手掐摸著腳邊的干草桿兒,除了偶爾的幾聲鳥叫,四周一片靜寂。也許是怕讓其他人擔心,也許是怕讓別人發現后自己又不能和大兒子像這樣待在一起,玉蘭始終沒有出聲。她時而閉眼,時而盯著棺材前兒子的照片出神兒,面無表情的就那么長時間地、靜靜地蜷坐在那里,就像她一直咬著牙靜靜地接受著命運的打擊……我不忍心打擾一位母親與兒子最后的道別,安靜的退了出去。
天亮了,大伯的棺木在伯母和堂哥們呼天搶地的痛哭聲中被送往了墓地。玉蘭站靠在大門口,目送著大兒子遠去,一瞬間,她的背愈加的彎馱了。
這場葬禮之后,玉蘭仍然沒有抱怨過什么,也從不向村里人傾訴她心里喪子的傷痛,她反而總是要孩子們別擔心自己,生活被她掩飾的仿佛很快歸于了平靜,只是在她的手里,多了一把拐杖,一把閑置了多年的紫荊疙瘩拐杖。從那以后玉蘭走起路來便再也沒有離開過這把拐杖!那是一位母親,那是玉蘭,那一年她七十三歲。
與我們倆有關的最后一場葬禮,是在一個冰雪初融的春季,這一次,玉蘭安穩地躺在了那里,這一年她八十五歲。
玉蘭的葬禮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靈堂里并排的擺放著兩口新漆的棺材,一口是玉蘭自己的,一口是玉蘭生前為早已經離世的丈夫準備的。馬犁溝村因為地處太行山深處,所以土葬的習俗一直還在延續。照風俗,夫妻雙方不管誰先故去,只要另一方沒有改嫁或者另娶,將來百年后都要與先走的那一方“并骨”合葬。玉蘭在去世前一年就被查出患上了宮頸癌,醫生建議保守治療。子女們向玉蘭隱瞞了她的病情,但是玉蘭早就從孩子們比平日里更殷勤的問候里猜出了端倪,她也順應著一直裝作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她心里有一塊幾十年的心病,總也放不下。
頭一年入冬,玉蘭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積蓄,跟子女們囑托道:“等沒了我啊,我的棺板啊你們置辦,這點錢你們給你爹也置辦個大點的,好點的棺材,那個老板柜啊估摸著早就朽了,等著我跟你爹并骨的時候一開墳,你們就一并給葬了,這事兒一定得辦了啊,我虧著你爹幾十年了,這也是我最后的心愿了……”
“娘,你看你這是說啥呢,好么樣的,不愛聽你說這話!”小女兒秀兒眼窩子淺,每每聽到玉蘭提及身后事,眼睛里都忍不住水汽氤氳。
“是啊娘,再說爹的壽材我們買就好,應當應分的,你這是做啥呢?”三兒子雖是兄妹中最小的,卻也是最心疼玉蘭的。
“是啊,知道你們孝順,娘這一輩子啊,從來也不欠著別人啥,就是在你爹這一件事上,感覺欠著呢。你們也別擔心娘,娘沒事兒,到這會兒,走不走的這事兒娘看的開,這一輩子娘知足,沒啥抱怨的,娘不屈呀,就是你大哥和你爹命薄點……將來呀要是走,娘也想走的利索兒的,不能像小崗他奶奶似得躺的炕上累著人,都受罪啊……”
“娘!你看你還說起來沒完了,都沒有影兒的事兒!”
“是啊,是啊,不說了,不說也總有那么一天不是?”玉蘭笑著擺了擺手,結束了這個話題。
轉年春天,玉蘭因為長時間服用抗癌藥品,引起副作用突發腦溢血毫無預兆的走了。
村里人都止不住的感慨:“這下真是得了二嬸子的意了,一下子就過去了,也算是修下了,沒遭啥罪。”
“二嬸子這一輩子呦,明白了一輩子,鋼骨了一輩子!臨走也干巴利落的不給人找麻煩啊……”
玉蘭是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有一個詩意的名字。
(作者單位:曹妃甸工業區綜合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