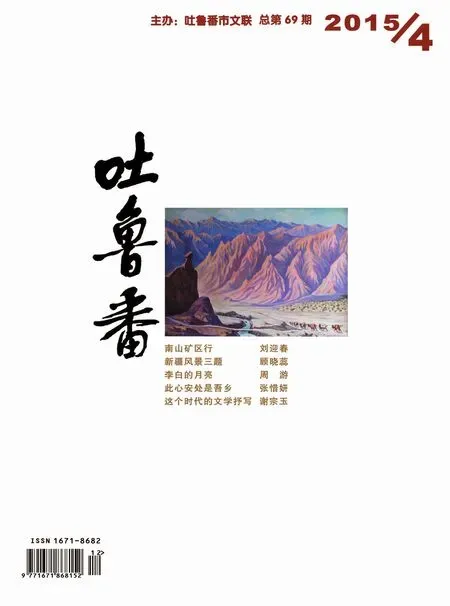在父親眼里我永遠是一個小孩子
曾利華
在父親眼里我永遠是一個小孩子
曾利華
冬天的清晨,如果條件允許,大多人會懶得早起。天氣愈冷,暖暖的被窩誘惑就更大,留戀床的人也就更多。
我原本就有早起的習(xí)慣,我的生物鐘十分準確,睜開眼睛時大抵都是在早晨7時左右,洗漱完畢再煮早餐吃或到外面吃早餐,然后上班,這已成定律。然而,這一次由于是周末,加之昨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一時,第二天早晨已近8時30分,我仍然酣睡未醒。
“砰砰砰,砰砰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誰把我的一簾幽夢敲走了?我十分不情愿地爬起床,對此時的造訪者充滿了敵意,心里滿是不快。
悻悻地打開門,卻看到了父親慈祥的面容。
父親手里提著一條鳙魚,滿上皺紋的臉上流淌的不知是汗水還是雨水,花白的頭發(fā)上沾滿了細細的水珠,白色的霧氣正從父親的頭發(fā)里往外升騰。
“這是從供大超市里排隊買回來的,便宜著呢!比市場價低了近1元1斤。”父親歡喜的情形和自豪的口氣,就像撿著了一個天大的便宜。
我透過樓梯間的窗戶向外望去,紛飛的寒雨、濃濃的白霧讓冬天的這個早晨醒得也很晚,看上去居然像是傍晚。
父親肯定一大早就起來了,因為父親的居所離供大超市有近2公里,況且為了節(jié)省一元錢,父親從不坐公交車去供大超市買東西。
從父親關(guān)切的眼神中,我突然發(fā)現(xiàn),雖然已成家立業(yè),但在父親眼里,我永遠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孩子,很多事情,他老人家仍然會不厭其煩地為我操勞。大到在城里買房,小到去市場上買菜,他都力求為我分憂。
想到這些,我鼻子一酸,眼眶里有東西充盈,我強忍著未讓那咸咸的東西溢出眼眶。
父親一直不肯和我住城里,盡管父親一再聲稱是不習(xí)慣,然而我深知,父親不肯在城里住的原因是城里開銷大,怕給我增加負擔(dān)。2005年,姐夫進城打工,為了幫姐夫照顧三個小孩,父親才同意搬到城里來。由于孩子們要上學(xué),父親每天都要很早就起來,幫孩子們弄早餐。當孩子們?nèi)ド蠈W(xué)的時候,父親就會獨自一個人前往超市里抑或街上逛逛,及時掌握關(guān)于柴、米、油、鹽、醬、醋、茶之類的供銷信息。有時為了從超市里買到一些便宜的限量蔬菜或食品,父親往往天沒有亮就起來,弄好早餐在火上溫著,然后就頂著凜冽的寒風(fēng)去超市購買東西。
父親今年76歲了,歲月的風(fēng)霜無情地壓彎了父親那曾經(jīng)挺拔的身軀。年少時,父親一直是一個學(xué)優(yōu)生,小學(xué)畢業(yè)時以優(yōu)異成績考取了當時的耒陽縣二中。初中畢業(yè)后,父親又入縣農(nóng)校學(xué)了一些農(nóng)技知識,之后便被分配到當時的耒陽縣石枧公社農(nóng)科站工作。
后來,公社農(nóng)科站也解散了,父親只好回到大隊的西嶺小學(xué),當起了民辦教師。
父親生性忠厚,不善言辭,更不會阿諛奉承任何權(quán)貴。正因為如此,在小學(xué)當民辦教師不到兩年,父親受到當時的大隊支書排擠,大隊支書老婆的一個親戚的親戚頂替了父親的崗位。父親“下崗”后,懷揣著農(nóng)校的結(jié)業(yè)證書,與幾個好友踏上了往西北方向的列車,在青海應(yīng)聘時,同去的4個人,只有父親一人被選中。為了和好友在一起工作,父親最終還是放棄了那份職業(yè)。當所帶的盤纏花得精光時,父親與好友只好回到故鄉(xiāng)操起了農(nóng)具,成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nóng)民。
但父親與其他農(nóng)民又有著小小的區(qū)別,這是因為父親學(xué)識比其他人要高。父親在農(nóng)校上學(xué)時,還學(xué)過一些畜牧方面的知識,因此,一些鄉(xiāng)親圈養(yǎng)的生豬患病時,就叫父親前往醫(yī)治。由于父親收費合理,加之醫(yī)技較高,經(jīng)他治療的生豬,基本是藥到病除,慢慢的,父親居然成了方圓十里有名的獸醫(yī),連鄰鄉(xiāng)的不少村民也不畏路途遙遠,步行10余里來我家請父親去幫忙。
我上小學(xué)后,經(jīng)常央求父親在農(nóng)閑時常給我講故事。父親讀了不少書,除了教我們《三字經(jīng)》外,也十分樂意給我講故事。記憶中最深刻的當是父親給我講的《十五貫》,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吃完晚餐后,父親坐在家門前的青石板上,而我則躺在農(nóng)村那種用竹篾編織的長椅上,父親拿著蒲扇,一邊給我扇風(fēng),一邊給我講《十五貫》。于是,我知道了故事中的婁阿鼠,知道了婁阿鼠為了十五貫錢而殺了屠戶尤葫蘆,知道了官居正四品的蘇州知府況鐘根據(jù)十五貫錢上染了豬油的特點,而找出了殺人真兇婁阿鼠。后來我讀中師時,課本中有了《十五貫》的文章,當我聽到老師講這篇課文時,再次憶起了那個炎熱的夏天晚上,我心里暖洋洋的,油然而生的是對父親思念和敬意。
也許父親深知多讀書的好處,所以盡管家里經(jīng)濟十分拮據(jù),父親卻從未有過讓我們兄弟姐妹輟學(xué)幫他干農(nóng)活的念頭。父親總是對我們說,只要你們讀,能考起,我就一定讓你們讀,哪怕是砸鍋賣鐵。1993年暑假我?guī)煼懂厴I(yè)后,分到了遠離故鄉(xiāng)的另一個鄉(xiāng)鎮(zhèn)任教小學(xué)。當時,北京師范大學(xué)在湖南三師辦了一個函授站,那年5月份我參加了成人高考,由于忙于實習(xí)沒有時間看書,我的考試成績并不理想。后來北師大降分錄取時,我還是幸運的達到了錄取線。但錄取通知書卻不是寄到我工作的學(xué)校,而是寄到了家里。生怕錯過錄取機會的父親明明知道下午沒有車去我工作的地方,然而,他卻不畏路途遙遠步行30多里坑坑洼洼的山路,一路顛簸,把信交到我手里。看到我并不很想去讀時,父親又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直到我同意去讀,父親才露出滿意的笑容。
如今,我已入不惑之年,父親仍常常把我當小孩子,經(jīng)常不厭其煩地在我面前嘮叨,諸如冬天要多加衣,在外要注意身體,應(yīng)酬不要多喝酒……聽多了,我時不時便會頂撞父親幾句:我不是小孩子,要你管這么多干嘛?每每我說這些時,我看到的總是父親那尷尬的表情。但是過不了多久,只要我和父親見面,父親又會嘮叨著這些。
我知道,在年邁的父親眼里,我依然還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