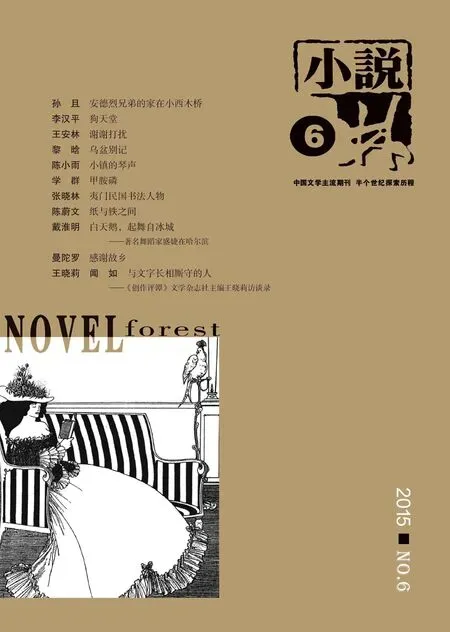夷門民國書法人物
◎張曉林
夷門民國書法人物
◎張曉林
陳雨門
陳雨門,1910-1995,原名陳禹門。民盟成員。
陳雨門出生在豫東睢縣一個沒落的書香世家。他自幼跟著祖父生活。他的祖父陳繼修是前清舉人,善書法,早年曾受清末探花馮文蔚親傳,書法自成一體。陳繼修對清廷忠心耿耿,盡管已經到了大清覆滅后的民國年間,他依然留著長及腰間的辮子招搖過市,常常引來一群頑皮的小兒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吶喊起哄。
陳繼修古板而嚴厲,為了背誦四書五經,陳雨門稚嫩的小手沒少挨祖父的板子,由此他的小手經常腫得像吹了氣的饅頭一樣。也正是因了這個緣故,他偷偷喜歡上了對門的栗寡婦。
只要是陳繼修出門的日子,陳雨門都會在栗寡婦的門前徘徊。一天,陳雨門剛剛站到栗寡婦的門前,“吱呀”,柴門開了,栗寡婦微笑著朝他招手。陳雨門無端地覺得那微笑很溫暖,他像著了迷似的,將食指含在嘴里,一步一挪地跟著栗寡婦進了院子。然后,進到了屋里。
栗寡婦拿出珍藏的帶玻璃紙的糖果讓陳雨門吃。第一次吃這種糖,那種徹骨的甜,若干若干年后,在開封城墻上的那間狹窄而昏暗的“無夢樓”里,陳雨門依然記憶猶新。
這一天,陳雨門打開了話匣子,他與栗寡婦無話不談。栗寡婦搖著紡花車,紡線槌眼看著一點一點大起來。她忽然說:“我給你出個謎,你猜猜看!”
陳雨門茫然地點點頭。
栗寡婦說:“一個小猴,關門露頭。”
陳雨門站在那兒,圓圓的小臉漲得通紅。他覺得好玩,但他猜不出來,四書五經里面沒有這么好玩的東西。
栗寡婦讓他站到紡花車旁,靠她近一點。陳雨門聞到了一縷暗香。栗寡婦解開了他小褂子上的一個扣兒,然后又重新給他扣上。陳雨門一下子全明白了。回家的時候,一路上,陳雨門把那粒扣子解開了又扣上,扣上了又解開,嘴里不停地念著:“一個小猴,關門露頭。”
1934年,陳雨門來到了開封。先是進河南美術專科學校讀書。讀書期間,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書店街的“大陸書店”,該店的店主是著名作家姚雪垠。兩年后,在姚雪垠的舉薦下,陳雨門進《河南民報》做了校對,繼而又做了副刊編輯。成年的陳雨門依然對謎語情有獨鐘,他在《河南民報》副刊開辟了“謎語”專欄。
也是在這個時候,陳雨門結識了開封詩人于賡虞。于賡虞不分季節地穿一件紫紅色的長衫,長發打著卷地披拂在肩頭。他的詩多把鬼魅、荒墳作為寫作對象,內容凄冷孤寒。陳雨門一下子癡迷上了這類詩歌,他拜在于賡虞的門下,開始了他的詩歌寫作。一個時期,陳雨門的詩作中無處不彌漫著于賡虞的氣息。他的《古城樓》里的詩句“晚鴉馱回野外荒墳上的敗絮,給頹靡的舊城樓貼花黃”。可視為這個時期的代表。
陳雨門發瘋般地寫詩,一天有時能寫十幾首。他用筆名“尚雨”在《丁香詩刊》發表了三首小詩,掙得三毛錢稿費。他用這平生的第一筆稿費買來八十個雞蛋,每天煎雞蛋果子吃,吃得他枯黃的臉上有了幾許的紅潤。
很快,陳雨門就摒棄了這種詩風的創作。他對詩歌有了自己的見解。在《中國新詩的前途》一文中,陳雨門闡述了自己的詩歌主張,并對于賡虞一類的詩歌進行了抨擊,認為那是“頹廢的,看不見人間的遼闊,一個人在走一條孤獨的路子”,是新詩發展的絕大障礙。他倡導寫詩要向白居易學習,婦孺都能讀得懂,要平民化,使詩歌創作走向民間,走入大眾生活。
在稍后與詩人武慕姚、李白鳳、郝世襄等人的雅聚唱和中,陳雨門也會偶來一拈紫羊毫。他的仕女畫,清新淡雅,頗有可觀處。書法走的是俊逸一路,無論篆隸或是行草,面目極具明清文人風韻。河南大學教授于安瀾寫詩贊譽道:“興來拈毫恣揮灑,情性到處不求工。云煙滿紙誰識得?文人氣息自盎然!”一時間,河南書法界把他和武慕姚、郝世襄、于安瀾并稱“河南四大文人書法家”。
對于書法,陳雨門從沒有拿出整塊時間去練習過,有時甚至好幾個月都不去摸毛筆。他認為,有時間了應該去多讀一些書,書法是什么?是治學之余事!他也從不因為練書法而去買宣紙,他練書法多在陳舊的報紙上練,或者廢棄的各類包裝紙,再不,友人來信的信封,這些,都是他練書法的較好選擇。
步入中年以后,陳雨門忽然對開封地區的民風民俗產生了濃厚興趣,創作了大量的民間傳奇和故事。他寫這些東西,不是為了發表,只是覺得好玩。他說:“開封是一座民間藝術的寶庫,世界各地的風俗,在開封都能找得到影子!”
陳雨門曾經寫過一篇關于開封斗雞的傳奇,名字叫《開封斗雞的兩大門派》,在這篇傳奇里,他把開封斗雞分為城東和城西兩大門派。文章寫好,他讀了兩遍,笑了兩遍,然后,順手丟在了書桌上。
開封有一個年輕作家,很有才華,他常來陳雨門的“無夢樓”,請教一些文學創作上的問題。或者,讓陳雨門給他開個書單,等回去后,照單去圖書館借來讀。
一個秋葉飄落的黃昏,年輕作家又到“無夢樓”來了。說了幾句閑話,他就看到了陳雨門剛寫的那篇傳奇。他拿在手里,讀了幾頁,就不舍得放下了。
他說:“讓我拿回家看吧。”
陳雨門看著他,微笑著點點頭,同意了。
年輕作家把稿子疊疊,裝進挎包,回家去了。一進家門,他就點上煤油燈,把稿子看了一遍,皺著眉頭沉思一會兒,又看了一遍。他找來紙和筆,連夜把這篇傳奇改寫成了一篇小說。改寫好,東方天際已經發白,成群的麻雀開始在院子的梧桐樹上“喳喳”鳴叫。
他把這篇叫《斗雞圖》的小說寄給了北京的《文學》雜志。三個月后,小說在頭題的位置發表了。年底,《斗雞圖》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年輕作家一舉成名。
同城的另一位馬姓作家,在年輕作家之前讀過《開封斗雞的兩大門派》,后來又讀《斗雞圖》,非常憤怒,認為是剽竊,他買一本發有《斗雞圖》的《文學》雜志,拿給陳雨門看。陳雨門看了雜志后,微笑不語。
年輕作家獲獎后,第二年春天,調到北京《文學》雜志當編輯去了。他再沒回來看過陳雨門,那篇《開封斗雞的兩大門派》手稿也無了蹤影。
每天的黃昏,吃過飯,陳雨門就走出“無夢樓”,走下城頭,站在城墻根下,用拐杖敲打城墻上的磚頭,一塊挨一塊地敲,篤篤篤,篤篤篤。
有個小女孩很奇怪,問:“老爺爺,你在敲啥呀?”
陳雨門微笑著答:“一塊磚就是一個謎,滿城墻的謎!”
許鈞
許鈞,1878-1959,字平石,號散一居士等。書法碑骨帖魂。
散一居士許鈞祖籍是祥符縣杏花營人,他們舉家遷居開封,是與清道光年間的那場大水有關。那年,黃河在杏花營張村決堤,滔天的濁浪瞬間吞噬了田野、村莊和樹木。平地變成了河流,石磙在激流中打著旋兒。許鈞的父親看著妻子業已凸起的肚子,套好平頭車子,說:“進城逃荒!”
1878年12月19日,許鈞在開封塘坊口街出生。他呱呱墜地的那天黃昏,許家院子的上空飛滿了灰色的鳥雀,接著,大雪漫天而下。開封有讓孩童抓周的習俗,抓周那天,許父把三樣東西擺在了許鈞面前,秤桿、木頭短槍和一支禿頭毛筆。許鈞在地上爬著,胖嘟嘟的小手毫不猶豫地抓起了那支禿頭毛筆,而且還狠狠地在棉花被上劃了一下。許父飽經風霜的臉上露出了微笑。十六歲的時候,許鈞投到河南名儒李星若門下修煉“四書五經”。1894年,李星若和好友王筱汀同赴汴梁試優貢,許鈞前往拜訪他們。談吐之間,李星若大為驚異,眼前這個清瘦的少年有著異于常人的稟賦。只是許鈞讀書太雜,他內心隱隱有一絲不安。在稍后的一次會晤中,李星若鄭重地告訴他:“你這個年齡,當讀圣賢之書,否則,易誤入歧途!”許鈞的臉紅了一紅,因為他正偷偷地讀一本春宮小說。
數年后,許鈞參加了清朝的最后一次科舉考試,考取鄉試開封府第一名,旋“納優貢生”。又三年,補廩生,到陳州府中學堂任國文教員。不久,重回開封,任河南師范學監。他正準備在教育上大展身手的時候,河南省臨時議會成立,議長楊勉齋欣賞他的才華,把他聘為貼身秘書。步入政界。
許鈞注定不是從政的那塊料,在秘書的位子上干了三四個月,他就滿腹的厭倦情緒,當河南省博物館四處物色書法部主任時,他軟磨硬泡說服了楊勉齋,毫不猶豫地去應聘了。書法部主任還肩負著培養書法人才的任務,這些年里,許鈞臨池是日課,他把自己學習書法摸索出來的經驗運用到教學當中,認為書法要以碑刻打基礎。他將學碑過程分成四步走,先學方筆造像,譬如《楊大眼》《孫秋生》《始平公》諸碑,強勁書法骨骼;次學圓筆,以鄭道昭的《鄭文公》和《云峰山刻石》為主,以豐潤肌膚增加神采;再學方圓并用之筆,如《張猛龍》《崔敬邕》等,來達到書法的形神相融;等完成以上三步,第四步就是學《爨寶子》《爨龍顏》二碑和《嵩高靈廟碑》,知巧而后守拙,回歸本真,回到嬰兒的狀態,與大自然對話。
1923年3月,康有為應河南督軍張福來、省長張鳴岐的“平原十日之約”來到開封。某日黃昏,作為河南金石修纂處主任的許鈞拜訪了他。交談不足四十分鐘的時間里,許鈞的書法理念發生了變化,正如康有為所說,書法得走碑帖融合的道路,許鈞認為,這無疑是學書法者的圭臬寶典。許鈞晚年創作的書法,以魏碑風骨寫米芾、王鐸神韻,一洗河南文人書風的酸腐和孱弱。
許鈞有七個兒子,除了最小的兒子外,其他幾個兒子在書法上都有著較深的造詣。1934年河南省舉辦第一屆書畫展覽,參展的九十名書畫家中,許鈞一家占了三個。長子許敬參入展書法兩件,五子許敬武入展四件。稍后,開封金石書畫研究社成立,同時舉辦了一次書畫展覽,許鈞、許敬參依然有書畫作品參展不提,許鈞的另外兩個兒子許公巖、許知非也有作品入展。一時間,許家“一門七書家”的佳話在夷門傳揚開去。
整個民國時期,在河南的書壇上,許鈞與靳志、關百益、張貞素有“四駕馬車”之稱。許鈞和關百益交往頻繁,二人曾同時供職于河南通志局。張鈁任河南建設廳長時,在吹臺立石碑兩通,一通名為《河南農林試驗總場紀略》,碑文書丹者是關百益;另一通名為《河南農林試驗總場紀念碑》,該碑的書丹者就是許鈞。這兩通碑嵌存于吹臺禹王殿西壁,雖經多年風雨侵蝕,字跡依然清晰可辨。
許鈞修撰《河南金石志》,查閱大量先賢金石文獻,對文獻中涉及的碑碣石刻,凡有疑惑的,碑刻和拓本即使在偏遠的山村,他都要跋山涉水跑過去進行核實,找鄉村知情人座談,直到無誤后才返回開封。許鈞為學嚴謹的名聲不脛而走,1936年6月,祥符縣成立修志館,縣長李雅仙高薪聘請許鈞出任修志館館長,重修《祥符縣志》。有整整兩年時間,許鈞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祥符縣志》的撰寫上,采訪資料、手稿、各類圖片等,裝滿了八大麻袋。1938年6月,開封淪陷在日寇的鐵騎之下,許鈞離開夷門避難,《祥符縣志》中途擱淺。
抗戰勝利前夕,許鈞遷居北京,住在史家胡同131號。許鈞晚年喜歡看一些雜書,有在書眉上隨意記些感悟之類的習慣。有一天,他躺在床上翻閱一本從開封帶來的舊書《黃山谷題跋集》,忽然有了感想,他用六兒子給他買的鋼筆把感想記在了書頁的空白處。當他寫完最后一個字,一個紙條從書里飄落下來,許鈞很奇怪,撿起來看看,紙條已經發黃,紙條是二十幾年前所寫,內容與今天所感所記竟然一字不差!
姜佛情
姜佛情,字無情。1896-2001。擅小楷。晚歲書法作品傳世不多。
第四巷是開封上等的窯子鋪。每到黃昏,滿巷子的窯子鋪門口都會掛盞粉紅色的燈籠。隨著夜色的濃重,時而有燈籠被摘下。這時,就有微風偷偷鉆進燈籠里去,蠟燭感到了羞愧和恥辱,有淚垂落。
下雨天氣,成群的烏鴉打第四巷的上空飛過。妓女們難得遇見這樣的日子,到中午的時候,她們才睡眼惺忪地從床上起來,坐在窗前梳妝,青絲如烏云般飛舞。脂粉摻雜肉欲的氣味飄滿了整個巷子,墻頭的一只黑貓顫抖著胡須打了兩個噴嚏,然后迅速地消失在爬墻虎后面。
與第四巷遙遙相望的會館胡同,雖說也是窯子鋪,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胡同里的空氣中散發著惡臭,低矮的房屋無論是頂檐或是墻壁,都長滿了霉菌一樣的苔蘚。如果是雨天,房前屋后,院子里,到處都是泥濘,豬屎、狗屎和溏雞屎攪在其中,有說不出的骯臟。間或有妓女打開柴門出來倒穢物,也都是黃黃的臉孔,頭發雞窩一般雜蕪。有的甚至上衣都不穿,乳房松垮地垂在胸前,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樣。
這是下等的窯子鋪。
第四巷的妓女們在揮霍凝脂般肉體的時候,會館胡同已開始向她們招手微笑;進了會館胡同,再過些年,汴梁門外衰草萋萋的荒野就是她們的歸宿了。
來這兩個地方的人很雜。去第四巷的,多是官吏、商賈、軍閥之流;而進會館胡同的,自是腳夫、挑擔貨郎和落荒的土匪之類。但對窯子鋪來說,只要腰間有銀子,來的都是客。來客揮灑銀兩,圖的是紅塵一笑。黑貓白貓,妓女們無權選擇,她們忍受卑鄙和腳趾間的污濁,靠銀子獲得心理上的平衡。這樣倒也算塵世間的一種規則。
然而,第四巷里不乏多情的窯姐,當春天萬物萌發的時候,她們開始拋出注定只會開謊花的繡球。這個繡球,燃燒著危險的火焰,一般都會拋向多才藝而又風流的公子哥。
第四巷的紅妓金縷,就把她的繡球拋給了夷門才子姜佛情。
姜佛情曾跟邵次公學習詩詞,頗得幾分次公的神韻。書法學鐘紹京的《靈飛經》,又參以鐘繇《宣示表》筆意,靈動而又厚重,在夷門書法圈被認為能將“二鐘”兩種迥異書風融會得了無痕跡的書壇怪才。在一次文人雅聚的時候,金縷對姜佛情一見鐘情。
二人很快陷入情網。芙蓉帳里,金縷梨花帶雨,顫抖若嬌羞的海棠。姜佛情豪氣勃發,拔下金縷鬢頭的銀釵,刺破中指,擠出一滴血在金縷的羅帕上,讓金縷收好。說:“我要贖你出去。娶你!”金縷杏子一般的眼里便蒙眬了一夢,夢是金黃色的,有銅銹一樣的花邊,且有潔白的鳥兒依偎在垂楊柳柔軟的枝頭。
以后的日子,金縷再不愿意接客。夜闌人靜之時,她燃上蠟燭,用清水一遍又一遍地擦拭自己的身體。擦拭過的身體在蠟燭的映照下,宛如陽春三月盛開的桃花。
老鴇開始惡毒地辱罵金縷。金縷用棉絮塞滿耳朵,罵聲變得渺茫,只看見老鴇的嘴在那兒滑稽地一張一合。金縷無邪地笑了,如玉般的小碎牙把老鴇暗綠色的長臉映襯得更加的丑陋。老鴇收了客人的錢,夜半讓客人硬闖進金縷的繡樓。金縷剛剛睡下,臨睡,她把盛滿洗澡水的木盆放在了繡樓的門口。客人撥開房門,一腳踏進去,踩翻了木盆,“撲通”,摔了一跤,后腦勺磕在門檻上,鉆心的疼。客人感到無趣,落荒而逃。
姜佛情贖金縷的念頭讓父母殘酷地捻滅了。他一急,就患上了一種古怪的病。睡到半夜,常常因喘不過氣而被憋醒。醒來之后渾身大汗淋漓,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懼,恐懼慢慢地侵占了金縷在他心目中的位置。請遍了開封所有的名醫,吃了無數劑藥,這種古怪的病絲毫不見起色。
家人請來了相國寺靜嚴禪師。號過脈后,靜嚴禪師說:“只有遁入空門,其他無路可走。”
肅殺的秋風吹落了枝頭最后一片樹葉,憔悴的金縷嘆了一口氣。老鴇把她的小包裹已經扔出了窗外,會館胡同的人在樓下等她多時了。金縷落下兩行眼淚。她從貼身的褻衣中取出那枚銀釵,用那枚銀釵刺破了自己的咽喉。
瞅著敗絮一般的尸體,老鴇伏身上去號啕大哭。然后站起來捏了一把鼻涕,讓人抬出西城門外,裹一頂葦席,埋在了亂草叢中。
河大詩人葉鼎洛,曾與姜佛情有過一段交往,在姜佛情的寓所見過金縷幾面,并暗戀上了金縷。聽說金縷葬身荒野,他灌進肚子半瓶汴州醉,扛起一把鐵锨,深夜獨自一人摸到金縷的葬所,將土掘開,用鐵锨砍下金縷的頭顱,攜到自己的住處,剔除腐肉,用清水洗滌干凈,再用紅漆漆了,日夜對著鮮紅的頭顱吟哦,得了佳句,就刻在頭顱上,刻滿再漆,漆好再刻,時而痛哭,時而大笑。
幾個月后,詩人葉鼎洛被學校趕出了校門。他的幾個校友把他捆綁起來,送進了瘋人院。
葉鼎洛被趕出校門的當天夜里,金縷的頭顱被兩三條野狗你爭我奪地叼去了。河大的老校工瘸腿老高以為那是個寶物,跟在野狗后面一顛一顛地攆有三里地遠。
姜佛情做了大相國寺的居士,他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焚香誦經,已修得滿面紅光。念經之余,每天習練書法,他又開始把明朝大才子文征明的小楷筆意融進他的書法中去。書法大進。
姜佛情活到九十六歲,忽然去世。去世之日,有一盞粉紅色的燈籠在空中閃現。
張曉林,《大觀》雜志社社長、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開封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先后在《莽原》《西部》《山東文學》《作品》《西湖》《廣州文藝》《小說林》等100余家刊物發表筆記體小說400余篇,300余篇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散文選刊》《作家文摘》《讀者》《長江文藝選刊》等選載。出版小說集《圉鎮筆記》《讒言》《宋朝故事》《書法菩提》《蝦湖之謎》等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