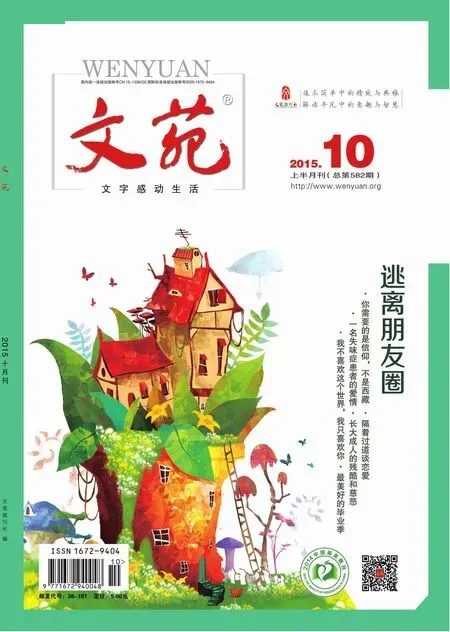自我的白鯨
[文/李歆]
其實我不知道該如何講述這個故事,甚至不知道這個故事該不該說。
女兒今年快4歲了,我們最經常去的地方,就是家旁邊的海洋公園。這里是上海的AAAA級景區,號稱總面積達1萬平方米,擁有上萬尾超過了300多種的水生生物。
無論是誰,從每周末停在海洋公園外的一輛輛旅游巴士,和排隊購票排成變壓器線圈一樣的家長和小孩都可以做出結論,這里值得一去。
的確,從一開始我就很喜歡這里,女兒也喜歡。
我們一起看大大小小的水母,一起坐透明的水晶船看池子里的鯊魚。我們看水獺自由地在陸地和水中穿梭玩耍,我們看企鵝純屬為了嬉戲追逐水里的魚。
如果故事一直是這樣甜美,我就沒有說下去的必要了。
我的困惑,發生在海洋公園另外一端。
除了魚,海洋公園還有一個白鯨表演館,但這里實際上不只有白鯨,還有海獅。表演上下午各一場,每次半個小時。
從入場開始,白鯨們就開始展現一種海洋霸主的優雅和從容。體形龐大的它們,不同于海獅的滑稽搞笑表演風格。雖然速度不快,但它們會擺動那大大的尾鰭激起美麗的浪花;它們潛入水底,再鉆出水面的時候,可以靈巧地高高托起馴獸師一起游泳。
此外,聰明的白鯨們還會為觀眾們獻上“歌聲”,它們的叫聲其實很像小孩,很有節奏,全場觀眾開始會很驚訝,繼而拍手大叫。
每次節目的最后,馴獸師和白鯨會圍成一個圈,在席琳·迪翁的《My Heart Will Go On》的歌聲中,向大家揮手致意,展現和諧,結束演出。
雖然我們經常來,但是每次出場的海獅和白鯨順序、數量都會有些變化,表演不全一樣。如果是新觀眾,是體會不到這些差別的,對年卡持有者我來說,經常去看,也不會覺得悶。
看表演的時候,我經常會見縫插針地跟女兒說教。比如當白鯨配合馴獸師刷牙的時候,我就會跟女兒說,你看,大白(我女兒也這么叫它們)也要刷牙的,你每天也要認真刷牙哦,女兒聽了就會點點頭。白鯨表演好了,馴獸師給它們魚翅,我也會跟女兒說,你看它們聽話,就有好吃的了。女兒就說,我也聽話,我也有好吃的。
問題出在一次,我帶女兒去看演出,白鯨沒有聽話。
通常,在表演節目中有這樣一個環節。為了讓觀眾了解白鯨捕魚的本事,馴獸師會拿出一個木頭做的魚,背對白鯨拋入水中。之后,白鯨會看也不看就直接奔向假魚,然后迅速張大嘴巴,把假魚叼在口中,游回馴獸師身邊換取真魚吃。
嬗變學習理論認為,成年人是通過一系列的學習、反思和實踐過程實現自身轉變的。這個轉變不是一般的知識積累和技能增加,而是一個學習思想意識、角色、氣質等多方面的顯著變化。[4]根據嬗變學習理論,培訓不僅要注重教師知識和技能的增加,而且要改變教師內在的思想意識。教師培訓需要考慮如何激發教師有意識地發掘自我概念,促進既有經驗與新理念、新知識、新技能的交互,發生認知的改變。
這天,跟往常一樣,三個馴獸師帶著白鯨三姐妹依次登場,前面的托舉、唱歌、刷牙都很正常,可是到了捕魚的環節,其中一頭白鯨,咬著木頭魚,不再肯交還給馴獸師。
這頭白鯨,是三姐妹中體形最大、年齡最長的一頭。最開始它不肯交還假魚,解說員還能控制場面,要求觀眾給予更多掌聲,讓表情略微有些遲疑的馴獸師再給白鯨一次同樣的指示,等白鯨把嘴巴里的木頭魚吐出來。
可是,馴獸師幾次嘗試都沒有成功,無論他怎么努力,做什么樣的動作,吹幾次哨子,或者拿出多少魚在白鯨面前誘惑,大白就是不聽話,雖然不知道原因,但誰都能看出它的故事。觀眾的期待就此落空,現場一片嘈雜,解說員也沒詞了,每個人都不知道下面要發生什么。
解說員此前一直說白鯨類似3歲兒童的智力,那天大白鯨的表現就能證明——它明白別人要它做什么,但是它不想做。它叼著木頭魚,高昂著頭,不時轉個圈,仿佛自娛自樂,就是對馴獸師的任何信號都視而不見。面對這些對它無計可施的人類,白鯨咧開的嘴里仿佛滿是嘲笑。同時,它還兼具領袖的氣質,另外兩頭白鯨,也意識到了發生了什么。雖然有另外兩個馴獸師積極安撫,給予食物,但是看得出它們的不知所措,甚至有小小的驚慌。
不久,馴獸師就決定帶兩頭聽話的白鯨先行離場,讓它們先回到連接著表演池的飼養籠。同時,解說員開始跟觀眾道歉,說最后一個節目的確有點遺憾,想必是白鯨身體不適,希望大家理解,現在演出結束,請依次散場。
在可以容納1500人的巨大環形劇場里,沒有了剛才的笑聲、歡呼聲,取而代之的滿是抱怨和無奈。大家在引導員的帶領下,緩慢地退場。還有很多觀眾,跟我一樣,想看看最后還會發生什么。
此刻的水池里,氣氛依然緊張。馴獸師跳入水中,試圖撫摸白鯨,穩定它的情緒,拿下木頭魚,可是白鯨死也不松口,甚至用力甩頭躲避水中的馴獸師。藍色的大水池里,蕩漾著徒勞的水花。此前,我聽到解說員說過無數次人和大自然中的生物如何和諧共處,現在,我只能看到自然生靈力量的強大和人類的束手無策。
這時,我一直沉默的女兒發話了:“爸爸,大白為什么不聽話?”我想了想,撒了個謊,說白鯨沒有不聽話,它在跟馴獸師玩。女兒看看我,仿佛知道我沒說實話。那天最后,我帶著女兒的疑問和不解,就那樣離開了,也不知道結局如何。
之后,我們雖然還去海洋公園,但是女兒已經不想再看白鯨表演,她只喜歡看看可愛的小海馬或者頑皮的熱帶魚。
如果你問我有沒有因為那天撒謊而內疚,我的確是有一點。可是從那天到現在我想得最多的,是大白,它為什么不聽人的話?或者,它到底應不應該聽人的話?
白鯨,本來就不屬于這個人造水池。大白的家,是海洋,它應該在那里繁衍、生息,想玩什么就跟同伴玩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許是我受了《海豚灣》的主人公瑞察·歐貝瑞的影響,我覺得白鯨不該為了一兩條冰鮮魚,在小小的水池中被人類指揮!
孩子也應該把時間花在游戲、花在探尋自己、花在大自然上,而不是為了成為一個乖寶寶、一個好學生、一個好員工從小被禁錮在各種牢籠里。如果在城市中,周末只有商場和游樂場給兒童玩耍,他們和那些被禁錮馴化的白鯨,有什么區別?
我的女兒快4歲了,除了一個音樂興趣班,讓她在里面蹦蹦跳跳,我沒有帶她去過任何早教學機構。只要有時間,我更多地陪她散步或者折紙或者講故事或者旅行,我甚至做飯的時候經常叫她過來看看食材本來的樣子,只要她覺得好玩。總之,我不想強加給她任何她決定抗拒的東西,或者讓她學習身邊每個差不多年齡的孩子都在學的東西,這是我的一種固執。
雖然我知道,我即使帶她跳離了強制教育的小水池,可能還是跳不出如今社會壓力這個大大的水池,但是我真的不想女兒有一天,成年后,覺得我剝奪了她的童年,拒絕再服從我,宛如那頭嘴里死死咬著木頭魚的大白,不想再聽從馴獸師。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 2015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