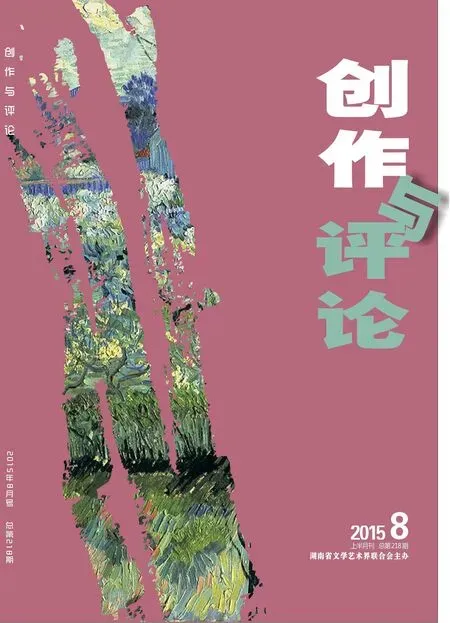活著的姿態(外一篇)
○ 姚岸頎
一年前,從昆明轉機至曼谷途中,我一直在看余華的《活著》,在休閑的旅途中,陪福貴度過了漫長的一生。可就在享受這沿途美景時,自己與書中人物的生活反差讓我倍感不適,就如同站在海邊聞見餐廳里飄來誘人的麥香,正要饕餮一餐時,導游報出了泰國貧困人口的數目。因有這樣的反差,我對福貴的命運一直在思索,福貴活著的姿態到底是什么。
年前市民政部門在體育館舉行了募捐活動,有100個貧困山區的小孩坐在體育館內,每個孩子的背后墻上都有他們的簡介。有人提議:先找到那個活得最悲慘的。于是我們幾個人將100份簡介逐個看了一遍,大家很難過,簡歷上的話直白不加任何修飾,有的是“父母雙亡,無家”,有的是“父死母貧,交通肇事者逃逸,賠償始終無法到位”,有的是“除她之外,全家死于突發泥石流”,這些的字眼讓人不忍卒看。要不是參加這個活動,還真不知道世界上竟有如此眾多的窮孩子活著。
劉哲霖默默走到換零處:“幫我把500元都換成5元的。”他一條龍地捐了過去,說了100句“要努力讀書。”我們都開始捐款,眼前的孩子在記者的導演下,大多在對著攝像機鏡頭笑著,但笑得勉強。那些簡歷里的生活才是他們的真實生活。
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從前不喜歡也不認可這句話,我認為幸福是相似的,不幸也是相似的。《肖申克的救贖》中有這么一段話:“人們要么忙著生,要么忙著死。”我認為幸福即生,不幸即死,無需多言。現在我覺得,即使生,都有不同,不幸就更是各有各的不幸。
那次捐贈,我雖然給幾個不幸的孩子帶來了臨時的小小幸運,但我無法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幸運。換句話說,臨時的小小饋贈,只是一次偶然。
稍后,我跟媽媽提議去幫助農村貧困小孩,媽媽答應了,還說服了幾位家境較好的同學的母親同往。開學的第二周愿望得以實現。我和同學張凌峰、羅沐下鄉了,張凌峰的媽媽彭教授開車,我媽媽跟班。車子行駛在崎嶇的鄉村小道上,GPS定位我們的奧迪轎車正在山村上空飛行。透過車窗,望見油菜花及遠處的山影,電影《后會無期》 中的一些場景若隱若現,窗外的自然都在提醒我:你連世界都沒有觀過,哪來的世界觀?
不知顛簸了多遠的距離,車子在一個凹凸不平的禾坪里停了下來。我們下了車,在鄉村小道上繞了一個大彎,走了一段下坡路后,來到一座房子前。房子是新蓋的,我很驚訝,這新蓋的房子里也有我們要幫助的人嗎?
前來迎接我們的長嶺小學的李校長說,我們將要援助的這個小孩叫馬學文,五年級在讀,他的母親于六年前因神經病去世,父親體弱多病,患有慢性腎炎,沒有勞動能力,也無錢進醫院透析,更別說換腎了。他們沒有戶口,馬學文這是寄住在姑媽家里。
進了房子的一樓,這才明白什么叫徒有其表,房子四壁是坑坑洼洼敷衍塞責的石灰砂漿墻面,有些地方還露出磚頭的痕跡,幾件家具老舊得寒磣,除了未曾油漆過的桌椅板凳,城里常見的平板電視、電腦、冰箱、真皮沙發之類的擺飾全都沒有。看來孩子的姑媽家也不寬裕。在渾濁的彌漫著雞糞味和霉味的空氣里,我們看見了小男孩馬學文。
在微弱的10W的電燈光下,他把頭埋在方桌上全神貫注寫作業,面對突然走進來的一群衣著光鮮的城里人,有點束手無措。他木訥地保持著握筆的姿態,面容菜黃,瘦削的臉龐上看不見紅暈,身上衣衫陳舊,兩只袖口還有顯眼的補丁,如果不是系著皺巴巴的紅領巾,根本想不到是個學生。
“這孩子真不懂事,”她的姑媽大聲說,“還不站起來迎客問好!”馬學文有點勉強地站起來,向我們一一點頭,但沒有直視我們的眼睛,因為周圍手機的閃光燈閃個不停,有一種不自然的感覺。iPhone6每閃光一次,他就拿起書本擋一下自己的眼睛。他似乎想不到這群城里人的突然光臨,與自己有何關系。
我有些反感,輕聲嘀咕:“干嘛這么頻繁地拍照呢?還沒進門就把自己當成天使啦!是來拯救一只病危的珍稀動物熊貓嗎?你們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偉大?”
隨來的王阿姨說:“照張相留作紀念有什么關系呢?我們今天來扶貧,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留下一點紀念,新聞網站和市里的報紙是要發表的呀……”
“掛網?炫耀?”
“這孩子!難道扶危濟困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光榮的事業?不然,特蕾莎修女何以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我走到馬學文身邊:“小弟弟,能看看你的書嗎?和你一樣,我也是個學生,只是年齡比你大一點。”
他將手里緊攥的書遞給我。打開,原來是小學六年級語文課本,每一篇正文的空隙,都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注釋,有些繁難的詞匯后面還標著拼音,寫得工工整整,一筆不茍。我稍加琢磨,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錯。我相信任何一個語文老師看了,都會覺得這幾乎是一個優秀高中生寫的課堂筆記。
阿姨們又開始了拍照,把那些工整娟秀的字跡拍成特寫,或者連馬學文的臉部一齊納入取景框。
馬學文的眉頭擰了攏來,厭惡情緒已經從他的面容中暴露無遺。但是,我無法阻止城里天使們的某些特殊嗜好——大概她們在想,我們是來無償捐助的,我們什么也不圖,就想紀錄下這次行程,用照片證實我們曾經向一個陌生的有出息的窮孩子獻出過愛心……
馬學文不說話,在一張紙片上寫下一句英語,亮在眾人面前:I don't like take photos(我不喜歡拍照)。
阿姨們笑起來,覺得這個孩子挺逗,居然用英語提出無聲的抗議了。一個鄉下小六生,怎么英語寫得這么準確?要不,就是個啞巴?
為了沖淡尷尬,我和凌峰、羅沐開始和馬學文交流學習情況。原來他的文化知識并不比我們幾個城里高一學生相差太遠。他的校長告訴我們:“這孩子是學校成績最拔尖的,英語已經能準確無誤地默完初三的單詞,并寫出簡單的家信,尤其數學,自學完了初三的課程。又特別愛學習。我們想鼓勵他跳級,小六畢業后直升高中。可是,我們又不免擔心,高中已經不屬于義務教育了,上學得交清學雜費的。倘若生在城里富裕人家,考個北大、清華他是完全不成問題的。可他家環境只是這樣,你們都看到了……”
馬學文的姑媽大概想最大限度調動城里天使的憐憫心,兀自將衣櫥中屬于馬學文的一只大抽屜打開,馬學文本能地擋住姑媽的手,他顯然不想將自己的隱私暴露于眾,但他姑媽還是用力拉開了抽屜:一團團亂七八糟的東西出現在眼前,揉得皺巴巴的四季衣服,破了洞的波鞋,疊滿補丁的書包,粘著膠布的塑料文具盒,疊得整整齊齊的日記本……
此時,手機的閃光燈變得尤為刺眼,鏡頭對準抽屜,“咔擦”“咔擦”的拍照聲響個不停。鄒教授把那疊日記本搬出來,攤開在方桌上,一邊翻看,一邊念念有聲……
馬學文的反感幾近憤怒,尤其翻看他的日記時,眼眶里明顯有淚水涌動,喉嚨口有強咽委屈的咕噥聲。她的姑媽似乎察覺到了這一點,帶點恨鐵不成鋼的口吻說:“城里阿姨是來幫助你的,看看日記有什么關系呢?又不是舉報信?這孩子,真傻。”轉而說:“看吧,你們只管看。沒關系的。沒關系的。學文只是有點害羞,怕見生人,你們看后給挑挑毛病啊……”
馬學文神情幾近麻木,眼神卻偽裝出一種無所謂。日記理應屬于他的隱私,一旦處在寄人籬下的環境,便喪失了自衛的權力。面對大人們的翻檢,他似乎不屑于生氣,或者說不敢生氣。這是隱忍。他知道他姑媽的苦心,這個同樣貧窮并主動擔負起撫養自己義務的姑媽,擔心人們會因為他的“不配合”而憤怒地取消某種憐憫……
當城里媽媽們經過一系列驗證,得出馬學文確實優秀,肯定不會辜負別人的資助的結論后,和校長咬了一陣耳朵,而后把資助的計劃悄悄轉告給馬學文的姑媽。
這位姑媽得悉幾位城里媽媽,會將馬學文從小六到高三的學費負擔到底,立刻翻箱倒柜想回贈每個人一點禮物,因為實在拿不出像樣的東西,命令馬學文:“快從地窖里搬五只南瓜來。快一點啊!”
馬學文意識到姑媽要做什么,執拗地站著沒有動,半晌,從牙縫里擠出一句話:“我不想……”
那位姑媽一時拗不過,搶步去了地窖,氣喘吁吁地搬來五只金黃色南瓜,強行塞進小車尾箱,并再三聲明,種植南瓜秧子時,沒在土里拌農藥,南瓜打苞后,沒有點激素,吃起來大可放心……
走的時候,我拍著馬學文的肩膀說:“加油,要考取一中啊!”本還想說“要更自信一點”——但我咽了回去——他應該早已擁有自信,不然,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怎能以一名小六生的名義,自學完初三的課程呢?他應當沒有自卑,沒有被貧困摧殘的氣餒,即便是在一大撥人強行參觀自己隱私時,仍然保持著不卑不亢的姿態。
他的內心是強大的。
回去的路上,我向媽媽們抗議,下次再來,不能隨意拍照了,更不能未經同意用閃光燈對準人家的眼睛。這一次,也不許把拍下的照片掛到網上,或者投給報紙。無論他將來是北大、清華的高材生,哈佛的博士,還是拾荒者乃至乞丐……
有人說:“掛網和投給報紙,是為了激起更多的同情,激發更多的義舉。”
我說:“同情心固然珍貴,但義舉是激發出來的嗎?如果同情等同于憐憫,捐助是為了張揚,這個同情就變質了;況且,依賴他人的捐助過日子,永遠不會強大……”
有人感嘆:“不可思議的90后、00后啊!真是飽人不識餓人饑。”
我反駁:“我活著與馬學文活著,有什么不同?難道我活著就叫幸福,他活著叫不幸這么簡單?‘每一朵花,只能開一次,只能享受一個季節的熱烈的或者溫柔的生命。我們又何嘗不一樣?我們只能來一次,只能有一個名字。而你要怎樣地過你這一生呢’。這是席慕容的原話。”
是的,下次援助時,不僅僅是看望,不僅僅是給他援助學費生活費這樣簡單,我要同他交流:用更頑強的姿態擁抱生活。
我再一次想到《活著》,作家余華之所以處心積慮塑造福貴這個文學形象,應當不單單是出于廉價的哀憐;也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阿Q的復制。
我想到福貴活著的姿態。
一葉一菩提
時尚作家韓梅梅一口氣出版了三本書,同名為《遇見一些人 流淚》,每一本都講述了二十個人的人生經歷及心路歷程,從清朝的倉央嘉措,到現代的張國榮,從長腿的赫本到長發的三毛。這六十人,都是逝去的名人,他們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都無比美好,他們的降臨是上蒼對我們的饋贈。
我翻開第二冊的一頁,看見慈和的李叔同老先生的面容,我以為隨后就是豐子愷先生了,但三本書翻完,也沒有看見他,我不禁替韓梅梅惋惜了,在這個豐麗的花園里怎么能錯過豐子愷先生呢?
我最早知道豐子愷,還在我不太識字時,那時我喜歡在母親的書架旁溜達,什么書都會去翻翻,但那些滿滿的文字書,我也就翻翻而已,翻完就把它們判了死刑,不再光顧。有兩本圖畫書入了我的法眼,它們是《三毛流浪記》 和豐子愷的畫冊《子愷畫集》,我不時地把它們拿出來溫習一遍。
豐子愷的畫簡單,易懂,如果說小時候看見的是它的有趣,那么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生活的獨特理解,他的質樸,他的人情味,他的教育觀,還有畫中的古樸的詩意都深深地打動了我。
在他的一幅題名為“除夕”的漫畫上,父親正把兒子舉過頭頂,旁邊題辭:今天一歲,明天兩歲。畫的線條筆墨簡單,就只一個大人,一個小孩,一個電燈泡,但從人物的動作和題辭可以看出濃濃的年味,可以看出父愛對兒子的喜愛與期待,可以看出小孩在父愛的沐浴下健康成長。就是這樣一幅畫可以讓讀者想到自己家濃濃的年味,想到父母對自己傾注的愛心與期待。
一幅題為“中秋之夜”的圖畫,夫妻兩人一手攙著婆婆,一手牽著小孩,畫面溫馨。“提攜”這幅畫,母親一手抱著小孩子,一手用繩子牽扯著大孩子,生動而有味,也可看出母親拉扯孩子的艱辛與不易,“提攜”雙關之意明顯,哪一個孩子不是母親雙手“提攜”長大,哪一個孩子不是母親傾注一生的心血“提攜”長大。這樣充滿人情味的畫作在他的作品里有很多,他為兩個女兒豐陳寶、豐一吟撰作的漫畫大多屬于這個題材,而且更多了一種諧趣。
豐子愷先生還有一部分詩意的畫作讓我尤為喜歡,其代表作是“紅了櫻桃,綠了芭蕉”。這幅畫的題目取自詞人蔣捷的《一剪梅·舟過吳江》: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在豐子愷的畫面,紅紅的櫻桃,嫩綠的芭蕉,一只飛旋的蜻蜓,畫面又簡約又飽滿,春夏之交的景色全然繪出。畫面還有一支點燃的香煙,裊裊燃起的煙,讓畫面充滿動感,意味雋永。據說豐子愷先生還真的在自家的庭院里種了櫻桃和芭蕉,這真是詩意地棲息啊。
這類作品很多,“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都有此等意蘊。
正如魯迅先生對陶淵明的評價一樣,陶有“悠然見南山”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式”的一面,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
評價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也應這樣全面地來看,如果,他的漫畫內容只有人情味的和詩意的漫畫,那還遠遠不是豐子愷的漫畫,我們涉獵更多他的畫集,包括他因與弘一大師相約而畫出的《護生畫集》,就會知道他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我欣賞他的漫畫“一肩擔盡古今愁”,畫中,一位弓背老者肩負沉甸甸的行囊,躬著腰前行,遠處半輪下沉的夕陽,倚在山樹之間。一肩擔盡古今愁!是何等的氣概!又是何等的悲壯!敢于承擔的精神正是人類前進的原動力。老者的背影仍時常在我的腦中浮現,這個負重的步伐也激勵我思考自己的人生。
對戰爭的譴責,對不平現實的控訴,對眾生的悲憫,這也是豐子愷的畫作里表現出來的思想與情感。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豐子愷就是這樣,他的世界有恨有愛,有憎惡同情。有金剛怒目,才有菩薩低眉。
我想對韓梅梅說,遇見豐子愷,會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