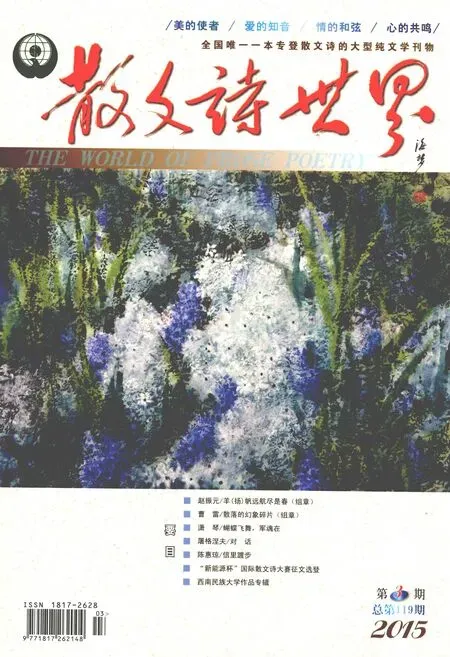在青藏腹地(五章)
甘肅 牧 風 [藏族]
在青藏腹地(五章)
甘肅 牧 風 [藏族]
甘南獻詞
這是千年的馬幫馱來的風景。
在青藏腹地,我常常聆聽到鷹族和羚群把黃河首曲的神韻踩動。可愛的甘南,在草原深處,雪域的鐘聲和陽光下的經幡把生命的琴弦撥響。
一個游牧的民族,偎依著篝火把根系在逐水草而居的地方。牧歌隨颶風拔地而起,牦牛的骨魂敲響前行的號角。我萬年敬仰的神駿,在這綠色的生命壘成的精神高地,箭鏃一樣射向遠方。
草原永遠是游子的故鄉。
坐落在阿尼瑪卿的骨穴里,獨自傾聽鷹鷲的喧嘯和格桑爆綻的妙音。湖泊上的蝴蝶獨獨飄來,恰似傾訴草原的空曠和蒼茫。
今夜雪封古道,我留戀的草原依水而寒。龍頭琴狂放的流水之音,彌漫著雪域的古樸和滄桑。班瑪的歌聲是我精神的月光,秀美的帳篷和迎風玉立的馬幫,在我流淚的模糊里迢迢遠去了。
鹽巴和酥油換來的是甘南草原的春天。面對晨光里青銅般滾動的黃河,以及遠處神山上古寺的祈禱聲,我打馬馳過望眼欲穿的故鄉……
牛頭城懷古
俯身望去,大野里一片肅殺。
蕭瑟的風時時襲來,一切生命的跡象都被迷茫的白霧覆蓋,讓我無法辨清牛頭城的原貌。那片廢墟在狂雪飛舞中越發顯得沉寂而蒼茫,甚至有點奇寒。吐谷渾壘土為城,飲血踏歌,身居高地,屯兵大野。每當夢里浮現牛頭城凝重的身影,與城密不可分的故事便潮水般蕩漾開來。
吐谷渾意外地從北方腹地撞入洮州大地,這些匆匆的身影在廣袤的洮州艱難地扎根。我想那些暗魂可能還廝守著這片故土吧,不然,為何山坡上那毛桃樹還迎雪挺立,依然保留著一種倔強的姿態。吐谷渾深埋內里的精神滲透在每個遺留的殘垣斷壁中,浸潤在每片破瓦和殘磚中。細細地咀嚼一番牛頭城優美的傳說,聞一聞古城廢墟上彌漫著歷史氣息的煙云,也是一種愜意的尋蹤。
雖然,時光已倏忽飛逝千年,與牛頭城的對話卻打破了時間隧道的束縛,短暫攀談,僅僅是瞬間的交流,翻撿那些歷史的殘章斷句,我感受到了這個謎一樣的城帶來的神秘啟示。
當我在迷惘中遠離故鄉,雪已在黃昏里暗淡下來,留在牛頭城遺址上的只有我深淺不一的腳印和被寒風吹皺的裸露背影,耳畔又傳來我詠嘆牛頭城的詩句“蒼涼之歌,嘹亮歷史的記憶之門。誰是立定城堞的將士和馬群,敗北的軍隊,帶傷的馬匹,消失的箭鏃,以及沉落的榮光?”其實牛頭城已失去西晉吐谷渾雄居時的神采,遺留下來的也只是片片廢墟和廢墟上隨意散落的瓦礫,以及破敗城垣上時暗時明的洞眼,還有那一幕幕與城有關的古老傳說。
遠望洮州衛城
透過暮色,透過黃昏中飛動的狂雪,洮州衛城赫然裸露出古老的容顏。
明代洪武時期的烽煙,從沐英揮動的手指間暫次滑落,唯有江浙一帶的古老裙裾和靈動的軟語,如潺潺流水浸潤了洮州這片神奇的高原和農牧融合的古道。
時光雖已老去,而記憶顯得更加清晰,古樸而憨厚的洮農依舊在春風里笑談祖先在滄桑中西遷的一片歷史。
六百多年倏忽間就從歷史的冊頁中輕輕地翻過,渾然一座古城還依稀留下當年明將征戰的氣勢,古老的戰事似一頁頁醒目的篇章,在后人的腦海里來回閃現,城垣上裸露的洞眼,似一雙雙將士深沉的眸光,緩慢地透過時光的遂道閃爍著。
在旺藏寺駐足
一扇虛掩的空門囚禁住一地春欲。
那清凈之域鐘鼓齊鳴,有天籟之音洞穿魂魄,營造著慈悲的境界。
一雙雙虔誠的腳步被渡入佛界,深入大悲咒悠揚而沉鳴的韻律中。我在塵世的聲音越飄越遠,一直蔓延到旺藏寺的周身。
忽有祈愿之聲落入耳鼓,動人心魄,由遠及近抵達眾生。
數百年幽靜的聲音,透過時光之壁傳遞佛陀賜予的福祉。
白龍江深處的旺藏寺,在云朵里孕育著吉祥。
遙看寺院旁邊的茨日那村,紅色的記憶再次打開,一九三五年九月,迭部旺藏的民眾在晨曦中送走毛潤之厚重的背影。
孤寂的勞作
勞作,使我成為一汪苦水,在陽光的呵護下透出淡淡的清香。
勞作,用生命的全部,用心靈的撞擊,以及火花的雙足。
當一切病人膏盲的嘈雜之聲停息,純樸的民歌便亮起喉嚨。
一種樸素的聲音,民眾為擺脫貧困的呼吸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浸入我的腦海,透過水墨未干的紙面。
一個勞作的群體,一個為生活而不斷謳歌的群體,一雙雙期盼的目光等待福祉的雨露。一抔黃土、一滴汗水、一聲吆喝,傾注了勞作的人們太多的夢想和勞動給予的幸福。
一種勞作,忘記了得失和名利。
一種勞作,忘記了喧鬧和聒噪。
一種勞作,忘記了孤獨和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