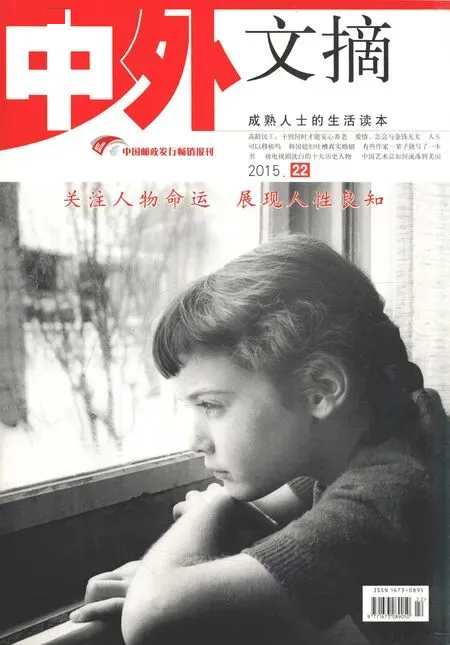精致的世界精致的人
精致的世界精致的人
人的活法越來越精彩,人的死法越來越謹慎。二戰中美軍三個月攻占沖繩島,墓地留下了一萬三千十字架。如今美國兵“拯救”世界,大多靠“精確打擊”了,人躲得遠遠的。美國人擅以精確取勝。當年攻打西西里島時設計了“肉餡計劃”,偽造的一個登陸艇專家馬丁少校的尸體被德國人打撈上來,上了美國人的當。重點是偽造得太精致。不說別的,連少校收到的情書都反復折疊又打開,好像他看了多少次。仿造文物的人都知道,器物易仿包漿難成,時間打磨過的東西,你不停地摩挲幾個月都不像。
工匠之精不足奇,如今做人之精正當道。學者錢理群曾說過一段話:我們的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寥寥數語,震聾發聵,甚于那泛泛的“錢氏之問”了。日前有媒體對此話置疑,這原本很正常;但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背書,則大可不必了。“精致”無可非議,“利己”也是一種個體選擇,二者一結合卻有了中國特色,它早已走出校門,大搖大擺地走向社會。
官員們變精致了,他們越來越善于圍著“利己”打轉轉。天津港危險品倉庫爆炸,不消說威力有多大,8個活生生的人無影無蹤了。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問民用樓該與倉庫距多遠,眾官員沉默了10秒沒搭腔,電視直播無奈地切回了演播室。我猜這些官員不會都不知曉吧,但形勢嚴峻,誰愿意跳出來引火燒身?閉嘴是上策。也許我高估了他們的智商,假如當真集體“無知”,那反倒讓人踏實。太原要提拔一名市委常委,官員們一改昔日“躍躍欲試”的姿態,紛紛避開了。樣板在前:一位待提的副市長公示后被舉報超生,連原來的烏紗也丟了。不會低調的人休要談做官。
學者們變精致了。自然科學絞盡腦汁上項目、搞經費,“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成了公開的秘密;國際著名刊物撤下四十幾篇造假論文,全是中國的。一些社科學者更是“善于表演、懂得配合”,靠討巧逢迎名聲大噪。瞄一眼他們的論文,我們個個都博士了。
媒體變精致了。打開版面,深度報道和精辟言論難得一見,目不暇接的是領導人在某處“露過幾次面”、講話中某個詞“出現了多少回”……一時吃不準的,標題一律加問號。什么“政治家辦報”,干脆統計學家拿個計算器辦報算了。領導一視察就“有何深意?”一張口就“釋放了什么信號?”靠猜度和揣摩過日子。拜托了老總,能不能抽時間說兩句自己的話?體會、理解民間聲音與中央精神,做一個肯負責有擔當的媒體,還是離這種“精致”遠一點好。
1947年6月,國共在東北四平進行了一場慘烈的廝殺。激戰18晝夜,林彪部民主聯軍被迫撤退,陳明仁部國軍堅守成功。役后,國民黨組織中外記者去采訪,《大公報》張高峰隨行,連發數電細數城內慘象,為飽受戰火的百姓“痛哭”。他寫的《哭四平》在《大公報》刊出,文末憤然疾呼:“人民沒有了活路,到處一片廢墟。國家的希望在哪里?早點停演這時代的悲劇,悲劇讓別人去演吧!”杜聿明讀后說:“這哪里是慶祝大捷,簡直像共產黨的記者!”媒體人你當知,《哭四平》載入了報業史,而杜將軍后來去哪兒了?
開封一位老人摔倒在馬路的水洼里。三個年輕人見狀奔過去,遲疑片刻又退回來。兩分鐘后老人再次被拉起時已溺亡。別去怪這些年輕人,救助的本能他們不缺,只是社會的大環境令他們有了片刻的算計與權衡,終致退卻了。我不禁想:我們何時能拋開那些精致的腦筋彎彎繞,沖動一點莽撞一點,路見不平一聲吼,一個個競相跳出來?
也許這想法已不見容于當下社會了。
社會是誰?還不就是咱們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