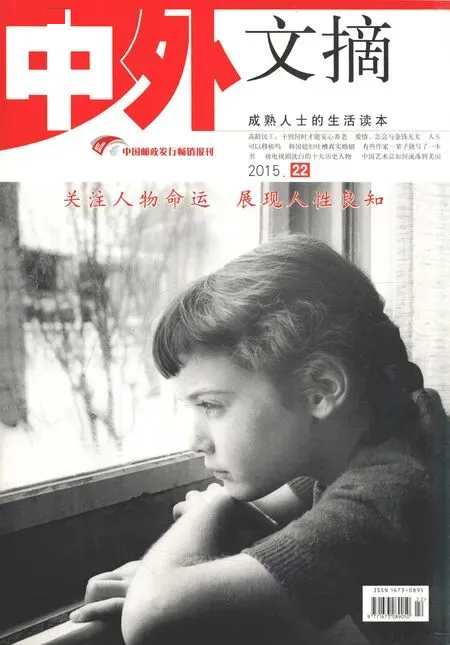美國:有錢人才讀得起文科
□ 畏 德
美國:有錢人才讀得起文科
□畏德
在已經打響的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戰中,各路候選人之間的多樣性成為一大焦點。從政治主張到選民基礎,從競選策略到公關技巧,不同候選人之間可謂各方面都是“火星撞地球”。
但有意思的是,他們大多都是“百無一用”的文科生:希拉里·克林頓、馬克·盧比奧和克里斯·克里斯蒂還好,學的是法律;杰布·布什學的是拉丁語;卡莉·菲奧莉娜學的是中世紀文學;邁克·哈克比學的居然是神學……
《大西洋月刊》刊文稱,這些掌握了美國政治最高話語權的寡頭的大學經歷或許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當今美國高等教育的現狀——文科成為富人家孩子的專利,理科受到窮人家孩子的青睞。
1780年,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約翰·亞當斯在寫給其妻子的一封信中談到了有關后輩教育的問題。他表示,鑒于自己花費了畢生的精力在謀求國家獨立上,他希望他的子輩都能學習一些用于建設國家的實際學問,比如數學、航海和商業等。這樣,到了他的孫輩一代,“我們的孩子就有了學習美術、陶藝、音樂和文學的物質基礎。”
200多年之后,美國的現實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疾馳而去。正如美國國家人文主義研究中心杰弗里·哈芬所說的那樣,“從決戰疆場到閑情逸致”。
目前的美國大學里,那些由父母出錢交學費的孩子往往更傾向于選擇“花俏”和不怎么實用的專業;而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則更愿意選擇“有用”的專業,比如計算機科學、數學和物理等。高收入家庭的學生與之相反,更多選擇諸如歷史、文學以及表演藝術等學科。
“家庭收入對學生的主修選擇的確有很大影響。”康奈爾大學的社會學學者金·威登在查閱了美國國家教育數據中心的統計資料后表示。
威登表示,要解釋這個現象其實很容易。“有錢人家的孩子選擇對就業不太利好的文科專業是因為他們的家境允許承擔潛在的失業風險。”她說,不同專業之間以長期計的收入差距最大可以達到300萬美元,“因此窮人家的學生押寶在理工科上是有道理可言的,相對有錢人家的孩子就不用考慮那么多了。”
“還有一個可能是,中上層階級家庭的孩子從小就相對更多地接受到文藝和文學熏陶,這讓他們產生對這些人文學科的認可,并且也影響著大學專業的最終選擇。”威登說。
來自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格雷戈·克拉克的研究從一個方面分析了“文科成為貴族學科”的現象。克拉克從過去15年劍橋大學的學生以及他們的主修專業的數據庫中發現,稀有甚至古怪姓氏(在英國這意味著高社會地位)的學生比起一般姓氏的學生更有可能主修文學、歷史,而不是計算機科學和經濟學。
喬治敦大學教育勞工中心的數據就顯示,人文學科年收入中位線大約5萬美元,而計算機科學則是7.5萬美元。
反過來講,學生的專業選擇甚至還可能影響到家長的財政狀況。不僅低收入家庭更容易培養出醫生,當了醫生的畢業生也能夠反過來提高父母的收入,這個比例按照美國勞工局的數據是40%;而藝術家,則會反向拖累父母的收入,比例是35%。
紐約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道爾頓·康尼則表示,父母的收入不是影響孩子大學專業選擇的唯一因素,其他的變量,比如父母的社會地位和教育程度也占有很大的權重。“我個人認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響更大。”
收入和社會地位可能會隨著代際變化而變化,但一個家族的整體階級位置和受教育程度卻相對穩定。
“有些人可能認為有錢人家的孩子選擇窮的文科專業、沒錢人家的孩子選擇富的理科專業是一種維持階層流動性的好辦法,”康尼說,“但實際上對被迫選擇理科的窮人孩子而言,他們失去了選擇職業的自由;對選擇了文科的富人孩子而言,他們卻仍然保有名校學歷和家庭財富。”
從這個角度來講,影響一個人大學專業和職業走向的因素越來越變得簡單粗暴,那就是,“你媽你爸錢多嗎?你媽你爸上過大學嗎?”實際上,正如我們在聚會上初次見到陌生人時最愛問的那個有關職業的問題那樣,“這不僅僅有助于回避直接詢問收入時的粗魯和尷尬,更有助于了解對方的深層次信息。”
“你好我是一名醫生”背后的潛臺詞多半是“我的父母是農民”。
(摘自《看世界》2015年8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