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地帶站崗:詩人哨兵
山旋旋
夾縫地帶站崗:詩人哨兵
山旋旋

山旋旋,24歲,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愛旅行,愛徒步,以夢為馬,珍惜每一處路過的風景,敬畏每一個偶遇的生靈。愛閱讀,愛寫作,用手中的筆記錄身邊的點點滴滴。永懷一顆溫柔的心,用文學的態度對待世界。
哨兵,1970年11月出生于長江中下游的一個小城——洪湖,曾獲《人民文學》新浪潮詩歌獎、第二屆《芳草》文學雜志漢語雙年十佳獎,出版詩集有《江湖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清水堡》(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
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詩人相較于稍早一些的“第三代詩人”,面臨著更加尷尬的局面。在他們剛剛開始從事創作的時候,商品經濟的浪潮已經開始席卷神州各地,文學不再是人們所關注的焦點,詩歌也不再擁有掀起社會激情的魅力。程光煒甚至發出“八十年代已結束”的感慨:“原來的知識、真理、經驗,不再成為一種規定、指導,統馭是人寫作的‘型構’,起碼不再是一個準則。”1。而洪湖,最被人熟知的莫過于《洪湖赤衛隊》里所描述的有著“浪打浪”風光的魚米之鄉。但很少有人知道,洪湖作為湖北省的一個縣級市,歷來被當做武漢市的分洪區。洪湖這一方圓413平方公里的淡水湖,一直被作為長江的泄湖而存在。就像哨兵在他的詩中所說的那樣:“未曾出世/我們已分擔了世界的不幸。”2(《分洪區》)這種雙重的夾縫境地,造就了哨兵這樣執著地書寫故地,書寫內心孤獨的詩人。
一、地方志書寫——水鄉風情
哨兵幾乎所有的詩都氤氳著水汽,都與他的故鄉洪湖有關。不論是《江湖志》,還是近期的《清水堡》,詩集中描寫最多的就是水鄉的水、動植物和人。“哨兵大多數的湖泊詩歌不是沉迷于用詩意的語言表達湖泊的植物和動物世界,而是潛心挖掘和精心感受湖泊與人的精神世界的交往。”3他是一個有著強烈地方性意識的詩人。對于這片湖北省最大的淡水湖,哨兵從來不吝惜贊美之詞:“多少年了。我一直頭枕水鳥叫喚入眠或者/醒來。那耳邊藕絲般顫晃的聲音,是好姐姐/均勻的呼吸。”(《頭枕水鳥叫喚入眠或者醒來》)“朝露是我的嘴唇/我用一百只魚鷹的叫喚洗臉,荊棘/做木梳,云朵和帆影 /是印在小腹的胎記。當黑夜/再次降臨,野藕就是我的糧倉。而漁火/正圍著星光憂傷,像上蒼遺留在/大水里的文字。”(《湖神》)“我愛的湖洪湖。請讓我借用/你方圓三百里的水面做我的胃我要消化/愛情憂傷惆悵和淚水一一吐出/荷花鳥鳴稻谷和四季。”(《頌詞》)對于故鄉的富饒的物產,哨兵像一名態度嚴謹的湖泊生態記錄員,將“一百八十七種禽類的飛翔”一一記錄在案。他更像一名經驗豐富的老漁民,知道“驚蟄過后,三成的螃蟹會死于脫殼。”(《洪湖螃蟹的生活史》)他把菱角比作巫師,蠱惑著十歲的他下水摸索。也因菱角兩頭長有尖角,他也把它們比作勇士,“摘一顆,只當砍頭,卻命索不絕。”(《菱角》)
“洪湖”作為一個地名,實則有兩方面的含義。即湖水的自然風光以及其內的動植物,和作為縣級市的洪湖,這里居住著詩人的親人、朋友。例如每年夏天送詩人出湖的舒水發,他每次的繞道可能只是想逗弄一下挖藕的女人,懷念一下被“拐”到廣東的自家女人。還有詩中身份不明的“小趙”,終生是操著一口膠東話的洪湖人。赤壁的姑媽王永喜,被丈夫與兒子拋棄后 “像農貿市場一根貧賤的芹菜”。(《赤壁姑媽》)哨兵在追溯祖父祖母的詩中,也交代了他們因躲避戰亂亡命洪湖,表明了自己“異鄉人”的身份。還有懂三種方言和普通話的杭州籍老漁民李少雷,在湖中耗掉了大半生,死后甚至愧于重返大海。無論是在湖邊怡然自得的船夫,還是身份尷尬的漁民,他們都在洪湖這一夾縫地帶頑強地生活著。哨兵筆下的洪湖,無論是景還是人,都散發著找不到歸宿的孤獨感。他并不僅僅滿足于描摹洪湖醉人的自然風光,他還用一種現代性的目光審視著這片生于斯,長于斯的湖泊。他不僅僅看到了水鄉旖旎的景色,更用親身的經驗和細致入微的觀察給讀者重塑出一個具體又抽象,且時刻充滿著矛盾的洪湖。他的詩,與其說記錄洪湖的歷史,不如說是記錄個人的成長史、戀愛史與心靈史。
二、背叛——對故鄉的質疑
像福克納一樣,哨兵將洪湖當做“約克納帕塔卡”,灌注了他全部的精力與熱愛。然而,洪湖并不是一處虛構的天堂,她時刻在隨著時代前進的步伐而快速發展。哨兵的詩不僅僅滿足于描寫湖泊的美,小縣城在城市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他也從不回避。“他的寫作的獨特性在于:超越了贊美家鄉贊美地方文化的一般模式,用以洪湖為敘述主體的地方志寫作來展開他對個體生命和破碎生活的思考,既懷疑又審問,且將地方審美和人類審美貫連,從而成為一個現代派詩人而非單純體制批判的現實主義鄉土詩人和單純贊美的浪漫主義鄉土詩人。”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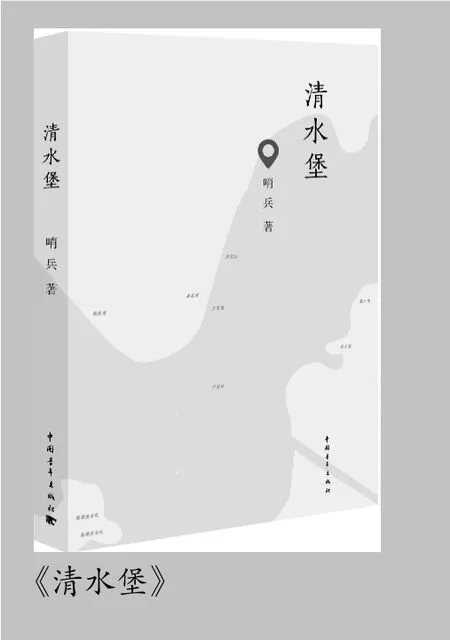
《清水堡》
首先,是環境的惡化。在他的博客里,有一首詩叫做《霾:PM2.5之歌》:“而霾/又落在洪湖,就算我坐在岸邊/像個少年,想把愛過的山水/再愛一次,但我已看不見我愛的世界/在哪里。”最近幾年來,藍天白云已經成為城市的奢侈品。如果某一天抬頭發現天空居然是藍色的,在驚訝之余一定會倍加珍惜這一日的光陰。詩人哨兵敏銳地發現這一變化,在霾已經侵蝕掉越來越多的大城市之后,PM2.5也開始“替換”洪湖這座小城的空氣。又如《偷獵》中,哨兵發出了響亮的質問:“問題是,我們偷獵到了野鴨/——誰在偷獵我們?”洪湖因其生態多樣性而得名,而現在越來越多的偷獵者已經在偷偷改變洪湖的生態系統,使野生動物的數量急劇減少。同時,不僅僅是生態的惡化,“我們”作為偷獵者本身在面對死亡時內心也逐漸在麻木,“我們目睹死亡,卻心懷竊喜。”
其次,洪湖作為一個小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商品化進程中。以往曾被詩人獨自擁有的水產與風光開始被外界所共享,或者說開始被外界入侵。哨兵的《在子貝淵》寫道:“拖著野鴨、桂花魚、螃蟹、烏龜/和小禽獸,猶如拖著/我們的影子,東去武漢/或南下廣州,再空運/至日本、南韓及世界各地/只扔下/魚棚 /和我們 /困在荒野/仿佛世界的垃圾”。現代性的商品交易雖然給洪湖帶來了經濟效益,但是給詩人留下的卻是“苦楚”。就像自己珍藏多年的寶藏突然被他人知曉,被他人獲得,這一枚“綠膽”在詩人心目中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同時,湖邊曾經怡然自得的人們的身份也開始慢慢轉變,暗娼、下崗工人、乞丐、瘋子等成為詩歌中的角色之一。“這個下崗多年的女工,比我們懂得更多。比如,她懂生活/是一直未曾命名的禽鳥,得自己/給自己打鳴。再比如,她懂/愛不是高尚和忠貞,而是/墮落和沉淪;她年過四十,羅圈腿,慣穿羽扇廠的工作服/顯得與長江中游的夜晚格格不入。”(《秋日札記·2》)生活的艱辛迫使下崗女工不得不另尋他法,在幸運的人眼中看起來是“墮落與沉淪”的行為對于她是維持生存的途徑。哨兵并沒有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來批判或者是為其惋惜,而是用一種理解的口吻,認為生活本該如此。人們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外來異鄉人的戶籍感到尷尬,以往身份的夾縫似乎早就被淡忘了。每一個人變得更關心“活下去”,而不是“怎么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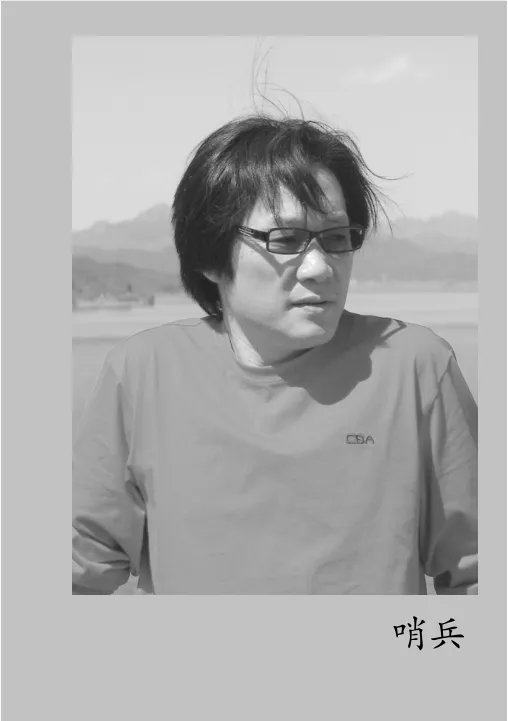
哨兵
哨兵筆下的洪湖其實一直是精神意義上的湖泊,我們作為讀者所讀到的也是他構想中的第七大淡水湖。在詩集中他營造了一座詩歌的烏托邦,但是他自己無法回避地生活在現實中的洪湖。《靜脈》這首詩用階梯型的排列方式,從首句的16個字逐漸減少到末句的兩個字,描寫洪湖作為一個縣級市,與京珠高速的拐點和省轄市都相距甚遠的尷尬境地。她就像被遺忘了一樣,只有在夏季水位高漲,被用作長江的泄湖時才被世人提及。“洪湖是一個盛裝水災的土沙壺 /值得大地私藏嗎?”(《對洪湖的十二種疑問》)每天面對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以及不再單純的小城,詩人自己心目中的詩歌湖泊也像如今的洪湖水域一樣,面臨著不斷縮小的困境。這使得本來就處于夾縫地帶的洪湖更顯得逼仄,也更加引起了詩人的焦慮感與孤獨感。
三、逃離——異鄉人的旁觀
哨兵在《異鄉人》中寫道的:“這些年我總覺得人是天外來客/不然,父母姊妹為什么像旅鳥群/全部遷離了洪湖?而在這水邊的出生地,我只能認鳥/作親。如白鶴于冬春間往返/錯把故土當成了異鄉。”然而,他自己也離開了故土,來到“異鄉”——武漢。
“眾多‘本土’的詩人不斷離開鄉土到異鄉生存,而這些身處異鄉甚或‘外省’的詩人更是日益顯豁地呈現出對地理詩學和出生地的‘精神故鄉’的眷顧以及遠離‘本土’的尷尬困境”。5一方面,在武漢創作的《武漢辭》6組詩中,我們仍舊可以看到詩人對故土割舍不掉的眷戀:“在別人的/故鄉,我只可能干自己的事/譬如把東湖開發為洪湖,把大學城/建成小集鎮。”面對武漢的大江大湖,哨兵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家鄉的水,“在武昌和漢口見掘楚河,貫穿東湖與/沙湖,似乎在另建一個洪湖”。另一方面,哨兵時刻在用來自洪湖的眼光審視著這座陌生的大城市,感受著她的繁華和壓力:“每到萬科銀座和新長江地產/交相燃起的那幾排廣告燈箱/我都會懇求那些霓虹/交換得慢一點/慢過我的心跳/呼吸,別驚擾我去數星。”在來到武漢之前,哨兵的內心矛盾可以說是理想的洪湖與現實中洪湖的分裂而產生的夾縫。來到武漢之后,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地理上的故鄉都被推到遠景,城鄉的沖突變得更為激烈。這不僅僅表現在城市高昂的房價和永遠處于癱瘓狀態下的交通,更表現在詩人內心對所在城市的一種“不認同”。他像 “房地產商面對武漢/僅作旁觀者。我亦為過客/不可能有愛恨。”這種“不認同”源于對“城市化”、“商品化”本能的抗拒。哨兵在武漢遙望洪湖時,自然而然地隱去了水鄉的不足與缺陷,主觀上美化了他的“精神故鄉”。與擁擠的大城市相比,洪湖起碼還留有的一小塊水土,用來安放在急躁的時代也不得不急躁的心靈。《武漢辭》的題記寫道:“近段雷雨頻暴,總聽見天上有人在喊我回去。”身體暫且回不去了,靈魂希望可以回到那個新堤小縣的夾街頭。
時光倒回到十年前的2005年,哨兵作為“平行”詩人群的代表人物活躍在平行詩歌論壇上。正如張執浩在其主編的《平行》中所言:“那些試圖用寫作取代生活的人不是平行者,同樣,那些認為生活大于寫作的人也不是平行者。所謂平行,首先是與生活保持一種恰如其分的對等關系,既是毅然反抗,又是倘然承擔;既從容,又緊張,既明知無望,又矢志前行。”7哨兵正是如此。他既沒有對現實生活妥協,也沒有全然逃避。面對日益喧囂的世界,保持一顆沉靜的心并不容易,“以詩/混世界,特別是混武漢/這座渾水碼頭,都挺難的”。(《武漢辭》)在走過世紀之交那場“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立場”的大討論之后,詩歌越來越成為一小眾人的自娛。曾經繁盛一時的“平行詩歌論壇”如今也成為一個無法顯示的頁面。哨兵的詩中,除了泄湖與長江的夾縫,夢中的洪湖與環境惡化的洪湖的夾縫,小縣城與大城市的夾縫之外,還有一條詩歌理想與現實生活的夾縫。然而無論是詩歌還是故鄉,哨兵一直在夾縫地帶頑強地站崗,小心翼翼地守衛著自己的每一首詩,每一寸心靈的自留地。
注釋:
1程光煒:《歲月的遺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1998年。
2哨兵:《江湖志》,長江文藝出版社,武漢,2009年。本文所引哨兵詩作,凡未說明出處的,皆引自該詩集。
3李魯平:《一個人的洪湖——哨兵的湖泊詩歌創作》,《湖北日報》,2013年7月7日
4劉川鄂:《哨兵的地方志書寫及在當下詩壇的意義》,《南方文壇》2012年第2期,第126-130頁。
5霍俊明:《從“江湖志”到“清水堡”——哨兵的“洪湖”和“地方志意識”》,《文藝報》2014年5月9日。
6哨兵:《武漢辭》,《中國詩歌》2013年02期,19—24頁。
7張執浩主編:《平行》第一卷,武漢,2005年,第29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