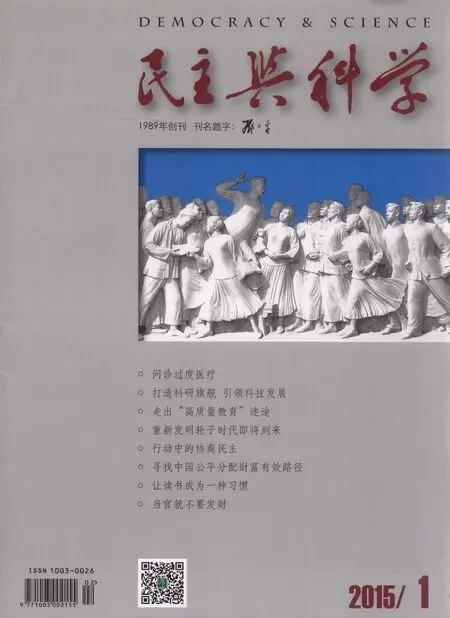林可勝:偉大愛國者和杰出科學家
■金 濤
林可勝:偉大愛國者和杰出科學家
■金濤
上世紀90年代,一次在與著名科學家嚴濟慈老先生談話時,嚴老跟我提起一個人。嚴老說:“當時國民政府給我和林可勝大夫頒發景星勛章,沒有舉行什么儀式,只是報上發了消息。”他接著又補充道:“林可勝大夫是協和醫學院的。他通過美國醫學界同行和美軍的醫生,為解決抗戰急需的藥品做了很大貢獻……”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林可勝的名字和極其簡短的介紹。
不知道當年獲此殊榮的是否還有其他的科學家,但90高齡的嚴濟慈對林可勝在抗戰期間的功績十分敬佩,留下很深印象。這固然也是惺惺相惜的緣故,因為他們都在同一時期,離開實驗室,把全部智慧和力量投入全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神圣事業。是戰爭召喚他們,給了他們施展才華的另一個人生舞臺。
嚴濟慈多年后仍然記得林可勝的名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嚴老知道林可勝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還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他們雖然屬于不同專業,嚴濟慈是物理學家,林可勝是生理學家,1948年,嚴濟慈和林可勝同時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首批中研院院士共81人,經民主推選產生,其中數理組院士28人,生物組院士25人,人文組院士28人。嚴濟慈為數理組,林可勝歸生物組。有人評論說,在首批中研院院士81人中,隨便哪一個名字,都是當時中國學術界最出色的人才。這是恰如其分的。
林可勝是怎樣的人,他的輝煌一生詳情如何?我深感興趣。
關于林可勝,海峽兩岸知道的人大概很少。長期以來,他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在一些與他生平有關的紀念活動中,由于這樣那樣的忌憚,他的名字被有意或無意抹掉了,似乎歷史是可以任人拆掉又可以重新編織的一件過時的毛衣。
然而時間是最公正的,隨著偏見的霧霾逐漸消散,許多歷史人物的真實面目終于浮現出來,獲得公正的符合實際的評價。同樣,林可勝這個被遺忘的名字,將會在中國現代科學史上重新閃耀。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人民
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全民抗戰中,林可勝的功績永垂青史。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炮聲震撼北平,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神圣戰爭爆發了。此時,林可勝正在歐洲,立即日夜兼程返回祖國。到北平后,他把協和生理系的事務作了妥善安排。
他和許多人一樣感受到戰爭的召喚,思考下一步該怎么辦?對于戰爭的慘烈和殘酷,林可勝一點兒也不陌生,那不是從電影或書本中間接獲知的皮毛印象。他曾經和戰爭打過很長的交道,在血雨腥風中,在和受傷士兵的親密接觸中,感受了戰爭的氛圍。
林可勝,祖籍福建省海澄縣。1897年10月生于新加坡。他出生于崇尚科學的華僑之家,其父林文慶,畢業于英國愛丁堡大學,曾創辦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學校——中華女校,1921年出任廈門大學首任校長。其母黃瑞瓊是著名老同盟會員黃乃裳之女,最早留學美國的中國女學生之一,任教于新加坡中華女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林可勝的姨父伍連德醫師是我國現代醫學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國現代檢疫與防疫事業的先驅,“中華醫學會”創始人。在1910年至1911年之間,他臨危受命,負責組織撲滅在東北暴發的肺鼠疫大流行。1911年4月,由伍連德主持的“萬國鼠疫研究會”國際醫學學術會議在沈陽召開。他因此在1935年成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的候選人。
林可勝8歲時被送往英國,讀完中學后即考進父親的母校愛丁堡大學。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他有英國國籍須服兵役,被分配在英國南部普茨茅斯附近的印軍醫院當外科助理醫生(另有一說法,他奉派法國南部,任英印軍準尉,從事新兵戰地救護訓練)。戰后仍回愛丁堡大學。1917~1918年擔任生理學大師謝弗的助教,并連續在學刊上發表論文,深得謝弗賞識。1919年以優異成績連續獲得醫學內科學士和外科學士學位,并被破格聘為生理學講師,擔任組織學教程,繼續隨謝弗從事生理學研究。1920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被聘為高級講師。1923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為了回國創業,并希望廣開視野,增進學識,1922年林可勝致函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駐華醫社(CMB)盼能獲得資助。他前往美國與歐洲大陸游學,得到駐華醫社批準,并希望他前往該社設立在北京的協和醫學院任職一年,以代理該院生理系主任克魯克山克的職務,后者需休假一年。正是這個機遇,改變了林可勝一生,也對中國生理學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1924年,27歲的林可勝回到祖國,應聘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學教授兼系主任,成為協和第一個華人教授。原先駐華醫社只是希望林可勝在協和代職一年,然而由于他的出色業績,自1924年至1937年,他任職協和生理系整整12年。這個時期,他的成就主要是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團隊,在生理學領域取得一流研究成果,為中國生理學奠定了基礎。
然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林可勝義無反顧告別
鐘愛的學術研究生涯,投身抗戰。根據一次大戰近4年的從軍經歷,他深知自已的崗位該在什么地方。他必須動員更多同行和他的學生們參與進來;還要充分利用自己在學術界的影響和社交網絡,甚至他的華僑身份,爭取海外僑胞和西方社會各界為中國抗戰出錢出力。
想到這里,林可勝充滿信心。
他是個說干就干的人,安排好協和的事務,躲過日軍監視,逃出北平,把子女護送到新加坡。之后立即經香港赴南京參加抗戰,應國民政府衛生部長之邀,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干事。隨后只身回到武漢,組織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由他擔任總隊長。在他的感召下,立即響應者有700多人,協和南下醫護人員幾乎全部參加。經過一番組建,救護總隊共有9個大隊,84個小隊(后擴充為123小隊),每小隊15至20人,分為救護隊、醫療隊、X光隊、防疫隊和環境衛生隊等,擔負起輔助軍醫和戰區防疫的任務,成為抗戰一支重要力量。
鑒于戰爭的持久性和醫護人員的緊缺,林可勝先后在長沙和貴陽圖云關創設救護總站,舉辦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和訓練示范病房,以培養戰地醫護人員,還附設藥品及醫療器械制造廠。當時的衛生人員訓練所,實際上集中了醫學包括基礎醫學在內各方面專門人才,規模之大,人才之眾,遠遠超過國內任何一所醫學院,前后訓練近兩萬人。救護總站先后派遣100多個救護隊分赴各戰區,并在5個戰區設立分站,有力支持了抗日戰爭。
抗戰初期,前線由于缺醫少藥,傷兵得不到及時醫護,往往輕傷轉重,重傷致死,嚴重影響士氣和戰斗力。自救護總站在前線設立戰地醫院后,情況大有改進。傷兵運到后,及時加以醫治,輕傷者痊愈后即重返戰場,重傷員則經過緊急處置后,轉移到后方醫院。
由于林可勝的國際聲望,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成立伊始,得到國際進步團體、個人以及愛國華僑的廣泛支持,獲得大批捐款、捐贈的藥品和醫療器械。林可勝每年1 至2次親赴美國募捐,在他執掌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6年間,據統計共募得6500萬美元捐款,平均每年1000萬美元,以當時匯率計,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數字(1937年中國政府的美國桐油借款為2500萬美元)。
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在1940年率領南洋華僑慰勞團回國慰問,親眼目睹林可勝的敬業精神和非凡業績,深受感動,極表贊許,當即主動應承逐月由南僑總會捐助1萬元給救護總站。
救護總站始終得到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的大力支援和幫助。當年,有一位德國人王安娜,她是中共地下黨員王炳南的妻子,是奉宋慶齡之命,與救護總站聯系的特殊人物。王安娜經常對紅十字會的工作和傷病員及難民情況作出書面報告,及時對外報道宣傳,擴大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總隊的影響,并協助將募得的大量捐款、醫藥物品和物資轉交。王安娜在她的回憶錄《嫁給革命的中國》中,詳細回顧了對林可勝的印象,以及中
國紅十字總會的工作:
……到達長沙,我們訪問紅十字會辦事處,受到林可勝博士的熱烈歡迎。林博士是位年輕的看來精力充沛的醫生。他是新加坡出生的華僑,著名的科學家。他在英國的愛丁堡留學,取得好幾個學位后回國,戰爭開始時他是北京大學(誤,應為協和醫學院)的教授。戰爭爆發后,他立刻拋棄優越的職位和科學家的生活,向政府要求參加抗戰服務工作。
……到了1938年夏天,中國全軍仍只有275所野戰醫院,共計22.3萬張病床。而且,這些野戰醫院——我親自看過的——大多數只不過是骯臟的洞穴;衣衫襤褸的傷病員,大都只能睡在木板上或泥地上,連瘧疾蔓延地區不可缺少的蚊帳也沒有。為了補醫生和護士的不足,林博士在長沙辦起紅十字學校,培養了幾百名青年男女,分成小組把他們分配到前線去。“這個學校最初培養的幾批醫療小組”,林博士自豪地說,“在前線都表現得很出色。令人遺憾的是,他們有的已經犧牲,有的負了傷,損失不小啊”!
1938年夏天,已有58個紅十字隊活躍在各個戰區。后來,我常常與這些紅十字隊見面。在許多地方,他們的工作,他們那種獻身精神,在各種困難面前都不屈服的樂觀主義精神,使我驚嘆不已。
許多跟隨林可勝多年的戰時醫務人員,都不會忘記林可勝身先士卒、嚴格自律的作風。
1940年盛夏,林可勝親自率領七八個醫師深入湘北戰區考察。當時許多地區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烈日下,他時常光著上身,頭包白布,赤腳草鞋,走在隊伍前頭。每天午飯后,他就在村子里找個長凳躺著歇息。他訓練自己該睡就睡,要醒即醒,始終保持旺盛精力。每到宿營地,他總是自已動手鋪床,掛蚊帳,反對帶勤務員。他們步行70天,回到貴陽后,根據沿途所見所聞,針對中國農村臟亂差的環境狀況,擬定一個“水與污物管制計劃”,推廣到各戰區,要求各戰區從管好環境衛生、水源清潔、污物處理入手,切實減少軍隊傳染病。這一計劃的實施,對改善廣大官兵健康狀況,增強戰斗力,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改變中國鄉村環境衛生提供了科學范本。
林可勝對受傷官兵懷有深厚感情,在他身上,時刻體現出救死扶傷的責任感。許多醫護人員還記得一件感人至深的故事:有一年圣誕節傍晚,從前線轉來一大批傷兵,救護總站的工作人員因時間已晚,推說病房已滿,不予收容。傷兵們只好瑟縮地躺在訓練醫院門口。時近半夜,林可勝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下山視察,當場大發脾氣,命令立即停止歡慶圣誕的晚會,全體醫護及事務人員緊急集合,打開訓練示范病房,安置好全部傷兵,并煮粥給他們吃,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
然而正當林可勝聲望如日中天時,他卻遭到解職處分。有一種說法是:“原因約略有二:其一,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及訓練所潛藏大批共黨分子;其二,紅十字會的龐大資源為小人覬覦。”(見《中國生理學之父——林可勝》,張之
杰著)不過主要原因,是林可勝認為對國共兩黨所轄的戰區應該一視同仁,紅十字會的物資不僅應該發給國民黨軍隊,也應該發給共產黨軍隊,在他眼中,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王安娜的回憶錄中也曾提到她前往山西五臺山地區,訪問白求恩大夫領導的國際和平醫院,白求恩和她談起缺少藥品和醫療器械的情形。林可勝拋開黨派之見,公正的辦事作風,不可避免地招來國民黨頑固派的非難,并對他的政治背景產生懷疑。
1942年夏天,林可勝卸去中國紅十字會總干事和救護總隊總隊長之職。一直到1944年,林可勝奉命隨中國遠征軍前往緬甸,出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醫藥總監。這期間,由于戰況緊張,他不辭勞苦,經常每日工作16個小時,因此多次得到中國政府的嘉獎,以及英、美政府的授勛。
抗日戰爭勝利后,林可勝還做了一些很重要的工作,把各軍醫學校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為國防醫學院。他出任院長,創立軍醫中心教育制度,培訓中國自己的軍醫。同時還負責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1948年,林可勝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蔣介石擬委任他為國民政府衛生部部長,他堅辭不就。
經歷8年抗戰的磨難,本該大展宏圖之際,面臨的卻是全面內戰的爆發和復雜的人事糾紛,而后者恰是他最不擅長的。于是在歷史轉折關頭,林可勝既沒有隨蔣介石去臺,也沒有留在大陸,1949年5月去了美國。他的心情是復雜而苦澀的。
林可勝后半生又繼續回到課堂和實驗室,先后任伊利諾大學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克雷頓大學醫學院生理學與藥理學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后又受聘于印第安納州邁爾斯實驗所,負責生理學藥理研究工作及醫學科學研究指導,直到1967年退休。1952年至1967年在邁爾斯實驗所,對于疼痛及止痛機制作了比較深入研究,發表十多篇論文,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1942年,林可勝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1955年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世界各地不少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聘請他為成員,1961年香港大學授予他科學博士名譽學位。
1969年7月8日,林可勝因患食道癌在牙買加的京士敦逝世,終年72歲。
林可勝的一生,可圈可點之處很多,無論是對科學的貢獻,還是抗戰期間的業績,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境界,這篇短文所能表達的肯定掛一漏萬,我誠摯希望能看到更加翔實的傳記。在本文即將結束后,再補充一個不得不說的小事:
在紅十字會工作期間,對物資的發放上,對捐款與贈品,林可勝要求有關部門和財會人員,必須嚴格管理,廉潔奉公,一筆筆列有清單,以備查看,一絲不茍。與此同時,林可勝本人更是以身作則,潔身自愛,一塵不染。這位曾經經手幾千萬美元的紅十字會會長,兩袖清風,離開祖國赴美時卻因為沒有路費,只好變賣全部家當,最后就連朋友送的幾雙新襪子也賣掉了。
(作者為科學普及出版社原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