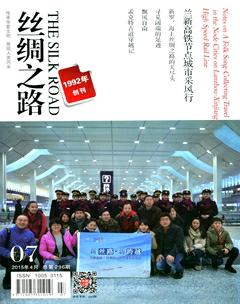尋覓闊端的足跡
文/劉炘
尋覓闊端的足跡
文/劉炘
一夜的小雨,路面還未干透。當太陽掙扎著顯露云層的時候,我激情滿懷地與朋友徑直向武威城西北的永昌鎮趕去。元朝一名叫闊端的皇子曾在這里為中國歷史濃重地書寫了一筆。曾經“市塵人語殊方雜,道路車聲百貨稠”,“號令鐵甲五千人”,“拱衛神京半屬秦”的城郭,如今在城市化的浪潮中無情地向四周田園擠壓。
宋代時,這里為西夏統治。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鐵騎攻破今天額濟納旗的黑水城,接著攻下沙州(今敦煌)、肅州(今酒泉)、甘州(今張掖),當元軍黑云壓城般地來到涼州(今武威)城下時,守衛涼州的西夏將領干扎簀由于力量不支,遂打開城門投降。至此,西夏王朝經營了190年的西涼府改朝換代。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227年,元朝分封窩闊臺的二皇子闊端為“永昌王”,即取“永遠昌盛”之意,駐守涼州。也有一種說法,說元朝分封的永昌王是闊端的兒子只必帖木兒。永昌王闊端看到戰火浩劫后的涼州城破敗不堪,于是便在現在武威城西北15公里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新王府。元世祖知道后,便把它命名為“永昌府”。
我們驅車前往的涼州區永昌鎮,正是永昌府舊址。公元1273年,元朝實行了路、州的行政建制,《元史·地理志》記載:“以永昌王宮殿所在地設永昌路,降西涼府為州。”這樣,永昌王王府的所在地、現在的永昌鎮就設立了永昌路,隸屬甘肅行中書省,升格為涼州地區的政治中心,涼州卻下降為永昌路領導下的一個縣級州。史學界對元代的永昌路究竟建在今天的武威還是今天的永昌縣,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至元十二年(1275),為蒙古族立下大功的回鶻高昌王亦都護奉旨到河西涼州,永昌王讓出永昌府,率部西進,在今永昌縣城建立永昌路,永昌府成了高昌王的王宮。由于“永昌”兩字的雷同,一些學者把元代設在涼州西北郊的永昌府(今武威永昌鎮)和明代設置在今永昌縣的永昌衛、清代設置在今永昌縣的永昌縣常混為一談。
說話間,我們到了永昌鎮政府。旁邊是石碑溝,因發現西寧王碑而聞名。不僅村名叫石碑村,就連小學、飯館都以“石碑”冠名。永昌王的足跡在哪里?永昌王府的遺址又在何方?僅僅近800年的歲月,如今竟成為一個難解之謎。武威電視臺的記者報道:“當地的農民說,在西寧王碑北側150米左右的農田地里,每逢澆水的時候,都會出現較大的滲漏現象。專家們考慮,這里是不是就有西寧王或哪個王子的墓地?”這是一個北倚低洼湖泊的高臺,它的南面就是發現西寧王碑的地方。按照王子墓地走向推理,這一帶應該是埋葬他們的地方。鎮文化站站長特地帶領我們,經過一片玉米地來到糧管所的后墻處。原先的城墻已經毀塌,尚有一段殘墻,推斷是當年有7里周長城郭的西北角。站長指著最下面的墻基說:“據分析,這下面的一段墻基有可能真正是元代的。墻基上面的土墻其實都是后來加上去的。”“最近有沒有發現與王城和王府有關的痕跡?”“沒有。前一段倒是希望能找到永昌王的王陵,我們還請來地質隊在這一帶做過勘探,最后也沒有什么結果。”
我們來到一個院落里,建成時間不長的現代風格的亭子里,豎立著一塊巨大的珍貴石碑——《大元敕賜西寧王碑》。鎮上的領導說:“在永昌王時代,有兩個重要人物。一位是忻都,一位是高昌王,他們的后人都給他們立了碑。”石碑保存得很完整,有5.8米之高。正面為漢文,背面為回鶻文。閱讀碑文得知,忻都是回鶻族阿臺不花的兒子,他和父親阿臺不花曾經跟隨忽必烈的大臣火赤哈爾的斤保衛過火州(今吐魯番東南),父子倆對元朝建立過卓著功勛。忻都去世后被朝廷追封為西寧王。忻都的兒子翰欒也曾任元惠帝的宰相副職。石碑記述了阿臺不花家族為元朝建功立業的歷史,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已經成為研究回鶻歷史的重要資料,美國、日本的學者千里迢迢地趕到這里進行專題研究。
還有一通石碑,記載了紐林的斤的事跡,珍藏在武威市博物館。火赤哈爾的斤率兵攻打火州時戰死,他的兒子紐林的斤繼承父業,奉詔平息叛亂有功,被元仁宗封為高昌王,頒發亦都護之印。于是他便定居于永昌府。高昌王死后,元文宗為了表彰其家族效忠元朝的功勛,特地立了《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
我們趕到永昌縣,可惜縣城里已經沒有了元代的遺跡。他們推薦我到南面的皇城看看。那豐美的草原,曾經是永昌王闊端馳騁疆場的地方。已經下午3點半了,略微猶豫之后,我決心去永昌王的夏季寢宮看個究竟。
從永昌縣縣城出發,沿著永皇公路,與東大河的渠道一直向南并行。東大河,古代稱為轉澗口,它由冷龍嶺北麓20多條小河匯成,今天依然是澆灌永昌縣東部的主要河流。約20公里后,我們接近了祁連山的前沿山地,駛下一條低洼的河谷,東大河的河水基本干涸。一條名叫娘娘橋的很窄的橋架在東大河的老河床上。“一過這個娘娘橋,對面就是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地界了。這里是兩個縣的交界處。”“河里怎么沒有水呢?”“上面修了水庫,水都進了渠道。所以河都是干的。”幾十年來,由于人口的驟增和耕地的擴大,祁連山一帶的河口幾乎都建設了水庫,河流被攔截起來。“它就像一把雙刃劍。節約了水量,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但又切斷了地下水的自然流淌,改變了荒漠的生態,惡化了環境。”
我們踏入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東邊的一塊大“飛地”——皇城草原。一過河谷,有了明顯的高山草原的感覺。時而兩山夾峙,看見大片的羊群和金光燦燦的樹林;時而層巒疊嶂,雪峰閃爍著一片銀光。我不斷地停車,貪婪地拍照。
汽車一直沿著東大河的南岸行進。翻過一座小山后,出現了一個小鎮。“這是一個藏族鄉,叫泱翔鄉。里面有個寺院,很大,叫沙溝寺,藏語稱目泱翔貢吧。我們回來時一定要看一看。”老閆說。“沙溝寺原來由永昌縣管轄,后來劃歸天祝,現在歸肅南縣皇城區管轄。”
河谷里的灌木越來越多。冷霜浸過的河柳,全都變成了一片黃色。可惜天氣昏暗,云層很低,否則,我可能會在河谷里拍一個下午。緊接著,公路出現了坡度,在逐漸的上坡中兩山靠攏。
“這地方叫‘駱駝脖子’,說明它的位置很險要。”我們看到了一線湖水,皇城水庫到了。水庫于1995年完工,庫容8000多立方。上到大壩時,只見一汪潔凈的圣水被儲存在這里。深灰色的云層倒映得湖面一片灰暗,雖然沒有碧綠如染,但卻清凈澄澈。如果在夏季,這里絕對是一個蔥郁秀麗、雪影倒映、帳篷座座、歌聲陣陣的旅游休閑好去處。
“你看,雪山和水面之間的草原上那一線黑色的輪廓,就是皇城的遺址。”
這么遠的距離,城池的規模竟這么大。
據說,在明清以前,這里就叫皇城灘,古名稱苕蓼。苕蓼牧場靠近雪山,氣候適宜,雨量集中,氣溫涼爽,這里有大片富饒的草原牧場和數量眾多的牛羊牲畜,自古就是發展畜牧和避暑納涼的理想之地。俞浩在《西域考古錄》中說:
黃城兒。元永昌王闊端藩封地,蒙古謂斡耳朵城,宮殿塋基,迄今遺址猶存。在前代謂苕蓼焉,南北朝時名最著。
也許,闊端正是看中了這里南可以抵青海,北可以出蹇占山口(即頭壩河口一帶)到永昌,東北出西營河谷直通武威的重要戰略位置,才在這里建造夏宮,重兵把守。
過皇城水庫不過一兩公里的草場上,我們繞過幾處鐵絲網,進入一座當地人叫“斡耳朵”的王城遺址。“斡耳朵”是突厥—蒙古語的譯音,意思是蒙古皇族成員的“宮室”,當時的皇子們都有自己的“斡耳朵”。這里存有大小城池各一處,相距約200米。之后對照資料得知,我們進入的城廓是南面的城廓。第一感覺就是城池占地很大。城墻雖然只剩下兩三米之高,但四周城池延續得很完整。城墻外面是茂密的黃色馬蓮草。我登上城墻,沿著城墻走了很長一段。
“陴壁連云荒草木,旌旗蔽野驚雁雕。”當年不可一世的霸王之氣已經煙消云散,但東西長338米、南北寬306米的龐大城郭依然張揚著元朝皇子曾經的武功霸業。從輪廓看去,東面和南面的城墻上各開一個城門。四角有城墩,每邊的城墻上也有四個城墩,遠遠看去,似一個個土堆。據考古發掘判斷,我們進入的城池是王城宮殿,而北面的大城池則是永昌王的牧馬城。
深秋濃暗的云層,蕭瑟凝重的氣息,極易引發對這片草原爭戰、歷史更替的想象。佇立古城,眼前浮現出闊端運籌帷幄、力主統一、改寫中國歷史偉業的情景。自吐蕃王朝崩潰后,雪域高原一直處于分裂混亂之中。公元1239年,蒙古將領多達那進入西藏,結識了西藏佛教領袖薩班。事后,多達建議蒙古領袖窩闊臺迎請薩班到涼州,共商西藏大計。五年后,薩班派譴侄子八思巴到涼州見到闊端。兩年后,薩班不顧年事已高,千里跋涉來到涼州。公元1247年,歷史性的時刻終于到來,薩班作為西藏代表,與元朝代表闊端舉行了商談,并在百塔寺簽署了協議。此刻,西藏統一于元朝中央政權之下,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
荒荒斜日淡,黯黯暮云低。
紫塞何空廓,玄冬漫凄慘。
天色漸晚,回眸曠野,依稀彌漫著清人胡(金加弋)筆下的那種境地。800年前的王城廢墟,曾觥籌交錯,舞榭歌臺,最終都抵不過歲月的雨打風吹,不得不感嘆時光的飛逝和風云的更迭。
此刻,向南望去,黑壓壓的云層下布滿了霧狀的雨絲,慢慢地,那道海拔5254米的冷龍嶺群山披滿了白色的雪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