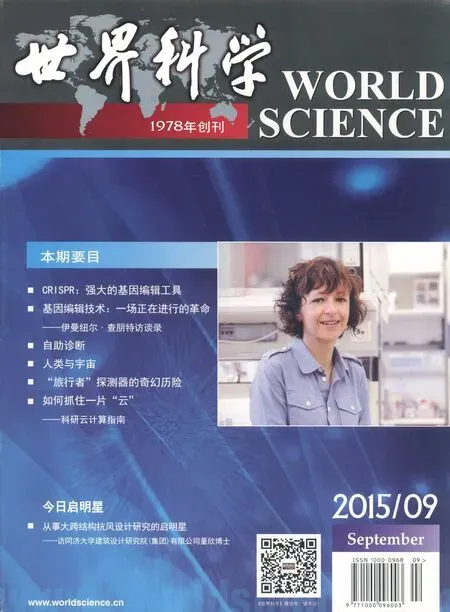歐文·A·羅斯(1926-2015)
呂吉爾/編譯
歐文·A·羅斯(1926-2015)
呂吉爾/編譯

歐文·A·羅斯(左)在2004年接受瑞典國王卡爾·古斯塔夫頒發的諾貝爾化學獎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生物化學家歐文·A·羅斯(Irwin A.Rose),于今年6月2日在馬薩諸塞州迪爾菲爾德的家中去世,享年88歲,其家人稱羅斯在睡夢中安詳離世。
羅斯博士因闡釋了活細胞如何再循環處理不再需要的分子——一個為醫學新療法另辟蹊徑的發現——而分享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在羅斯和兩位以色列科學家發現的細胞代謝過程中,一種叫做泛素的分子通過所謂的分子“死亡之吻”將自己附著于不再需要的分子上,從而將它們標記為有待銷毀的物質——如其名稱所示,“泛素”(Ubiquitin)與“廣泛存在的”(ubiquitous)一詞同根,說明它在細胞內廣泛存在。
1980年代早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福克斯·蔡斯癌癥研究中心,羅斯和兩位在那兒休假的以色列人阿龍·切哈諾沃(Aaron Ciechanover)和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就展開了對泛素作用的研究。
在《圣經》中,傳道書講到“物立自有時,物破亦有時”。在很大程度上,現代生物學已經成為DNA及其在構建生命所需之蛋白質的過程中所起作用的記事。羅斯及其同事將他們的重點集中在生命周期的其余部分:分子是如何被銷毀的。他們因此被認為是該學科領域中勇敢的逆行者。
一個“特別有洞察力的”選擇
然而,這項工作抓住了科學想象力,泛素介導蛋白銷毀過程的戲劇性本質可在諾貝爾委員會于2004年所發布新聞時的生動語言中體會到,即泛素對蛋白質的附著被描述為生物化學的“死亡之吻”。
一反科學界語言古板的常態,該新聞接著說,那些不再需要的蛋白質在被標記為銷毀對象之后就被送進細胞“垃圾處理器”中加以銷毀。這些結構包含在單個的細胞里面,被稱為蛋白酶體,不再需要的蛋白質分子將在蛋白酶體中被分成小塊。
由泛素介導的銷毀過程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分子從細胞中掃地出門,而是具有高度的針對性和選擇性。泛素在附著于注定要銷毀的特定蛋白質分子之后,兩者就一起來到蛋白酶體那兒。而形狀識別過程是引導蛋白酶體攝取不再需要的分子依據。根據科學家的理解,在此發生之前,泛素將自己松綁,離開即將就要被銷毀的蛋白質,重返自己的神圣使命。
事實上,僅僅闡明如此微妙和復雜的分子過程本身就堪稱科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在諾貝爾獎得主的同事看來,這不僅僅只是提供了理解生命基本過程——如DNA修復、細胞分裂、人體免疫系統的運行——的新方法那么簡單。
該領域的專家曾經指出,細胞若不能清除不再需要的蛋白質,那么就可能導致疾病,包括多種癌癥。而理解細胞銷毀蛋白質機制的過程有助于開發囊性纖維變性、各類癌癥及眾多其他疾病的治療方法。
在頒發諾貝爾獎時,哈佛大學的細胞生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戈德保(Alfred L.Goldberg)贊譽這是一個“特別有洞察力的”選擇。他寫道,羅斯博士和兩位以色列人是“開創性研究工作改變了現代生物學”的科學家。
自諾貝爾獎頒獎以來,美國人差不多贏得了其中的一半。但許多美國獲獎者是從其他國家移民來的,而羅斯的第一所學校是布魯克林的一所公立學校,他的全部及后繼研究工作都是在美國完成的。

生命科學領域中勇敢的逆行者——羅斯
“謙遜、不傲,潛心于研究”
歐文·A·羅斯(Irwin A.Rose)——有時也被稱做歐尼(Ernie)——于1926年7月16日出生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個世俗猶太人家庭。他的父母經營著一家地板商店,在羅斯13歲那年,母親把羅斯和他的弟弟帶到華盛頓州東部的斯波坎市的親戚家生活,他們認為,那兒的干燥氣候對患風濕熱的弟弟會有好處。而羅斯的父親則一直呆在紐約照料他的地板生意。
對此,這位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當時寫道,這是“我始終沒能理解且感到困惑的”安排。“父親很少看望我們,且相隔很長時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母親在斯波坎市的海軍補給站做文書工作。
羅斯曾在斯波坎市的醫院工作過一段時間,就此點燃了他對“解決醫學問題”的興趣。隨后羅斯就讀于華盛頓州立大學,一年之后因戰爭爆發而服役于海軍,擔任無線電技師。戰爭結束之后,根據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他入讀芝加哥大學,于1948年獲得理學學士學位,1952年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兩年后,羅斯來到耶魯大學醫學院的生物化學系任教,從1954年一直工作到1963年。1963年,羅斯加盟了位于費城的福克斯-蔡斯癌癥研究中心團隊,直到1995年退休。在福克斯-蔡斯癌癥研究中心期間,歐文培養了多位博士后研究員,包括最早發現泛素鏈的阿爾特·哈斯(Art Haas),最早把APF-1鑒定為泛素的基思·威爾金森(Keith Wilkinson),以及世界級酵素學家塞西爾·皮卡特(Cecile Pickart)。
退休后,羅斯一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的拉古納-伍茲居住。此時,長期習慣了實驗室生活的羅斯一時有些不適應,于是通過朋友在附近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校區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當諾貝爾獎宣布的時候,羅斯是該校醫學院的生理學和生物物理學系的杰出駐校教授。
在1970年代期間,羅斯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擔任物理生物化學教授。
在諾貝爾獎傳略中,羅斯博士感謝他的岳母對他本人及妻子職業生涯的貢獻。她幫助照料羅斯的四個孩子,使得他們夫婦有時間追求自己的科學事業。
同事們對羅斯的評價是:謙遜、不傲,潛心于研究。在諾貝爾獎宣布的那一天,加利福尼亞大學稱:“那天晚上,他把兩支試管塞進襯衫口袋,悄悄地溜進了強力質譜儀所在的一幢校舍去做分析了。”
[資料來源:Washington Post][責任編輯:則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