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人嗎
禾兮
村里有人嗎
禾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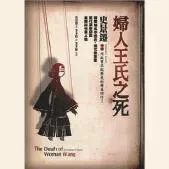
作者 史景遷著,李孝愷譯出版社 麥田出版社出版時間 2009-1-1
這個標題不關涉空巢村問題,而是單純講人,講新農村建設的路徑問題。我們現在一提問題,就拿所謂的大數據說話,而此種大數據來歷卻是可疑得很。以前提到的三農問題,除了農業、農村,還講到了農民:農民很苦。現在的數據是見物不見人,即便是見人,也是統計學意義上的事情。
新農村建設事關重大,那是要寫進歷史的。縱觀我們的歷史,帝王將相粉墨登場,朝代更替春秋大義,唯獨沒有小人物的一席之地。這樣的歷史觀一直在影響著我們,耳提面命一甲子的馬克思唯物史觀基本上是沒人講的,倒是西方的史學家在跟毛澤東的人民創造歷史的論述互通款曲。手頭有本美國史學家史景遷的《王氏之死》,是其中國研究系列之一。這樣的史書看過后,才知道原來歷史是可以寫小人物的,而且讀來竟是如此津津有味有如讀暢銷書一般。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世界著名漢學家,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1936年生于英國,現為耶魯大學教授。史教授喜歡研究中國歷史,景遷二字乃是自認為司馬遷粉絲的意思。在他的中國研究系列中,《王氏之死》看起來像是本小冊子,書名也有點像話本,故事的主角也很不起眼,王氏,十七世紀山東郯城縣的一個普通農婦。然而書小、人物小并不等于思路也小,該書有個副標題叫作“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命運”。史老師開宗明義就揭了中國史學的短:“地方研究一般不重視農村,而是把重點放在出名的地區:例如有多少才子佳人出生在那里,或者那里曾發生過一場毀滅性的暴動,那里的經濟條件多樣和優越,社會結構具有復雜的歷史淵源。”“從過去的窮人和被遺忘了的人的生活中總是很難得到什么的”。
史老師的研究素材分三塊,一是《郯城縣志》,二是做過郯城知縣的官紳黃六鴻的筆記,最后一塊也是最令人感興趣的:蒲松齡的作品。蒲松齡的故鄉淄川縣與郯城接壤,郯城的一些事情便入了他那著名的《聊齋志異》。小說可以入史,對我們來說似乎不可思議。然而小說確實可以入史,前提是好的小說。那些領了任務去寫新農村建設的所謂小說,就連看都沒法看,更被嚴肅的史學家棄之如敝屐。那些所謂作家,眼里是沒有窮苦農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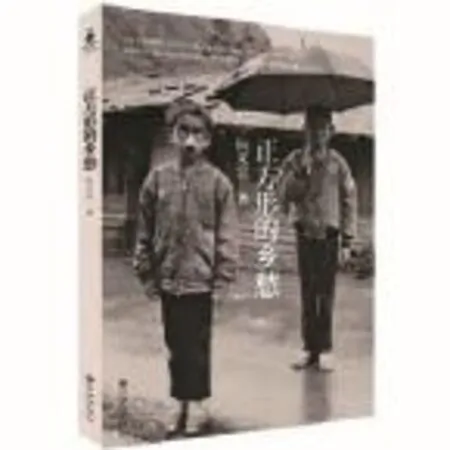
作者 阮義忠 著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出版時間 2014-3-1
本書是攝影家阮義忠繼《人與土地》《失落的優雅》之后,又一再現二十世紀70-90年代真實臺灣的經典攝影。書中所有照片,都是用120相機6cm×6cm膠卷拍出來、未經裁切的影像。80張照片及其背后文字,投遞給我們那些已散落無蹤的鄉愁:成年對童真的鄉愁,游子對家園的鄉愁,車水馬龍的都市對田野農耕的鄉愁。黑白的正方形影像,隱藏著最深沉的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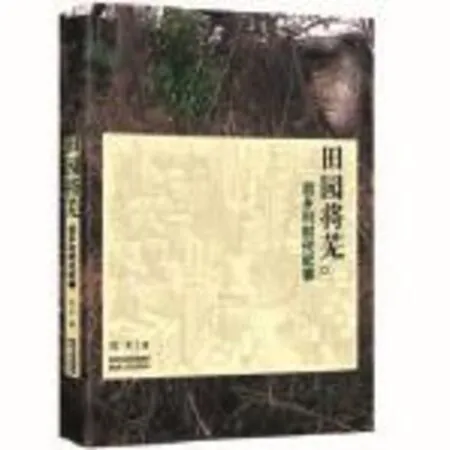
作者 江子 著出版社 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 2013-6-1
“在這一場中國鄉村大遷徙中,在這一場鄉村與城市的博弈中,那些無辜的鄉村孩子,成了被扣押的人質。他們本來還處于游戲的年齡,卻要被沉重的命運驅趕。他們與老人一起駐守在殘破荒涼而寂寞的村莊里,或者被火車押解著行駛在鄉村與城市之間。” 這不僅是一部優秀的散文集,同時也是一部具有社會學價值的鄉村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