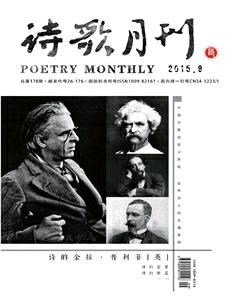陳樹照的詩
陳樹照

日出
四月我在老家信陽
一聲雄雞的啼鳴
從山下那片霧水迷茫的小村莊傳來
瞬間萬物起身與太陽相見
我摸了把濕漉漉的頭發(fā)
放棄了所有的野心
火車
火車的嘶鳴
把我從睡夢中驚醒
越來越沉悶的震顫聲
預示著火車馬上就要停下來
山海關車站
停車五分鐘清冷的月光
籠罩冰冷的鐵軌
走動三三兩兩上車下車的人
火車喘著粗氣
靜靜地趴著不動
我在月臺伸伸懶腰
一一火車穿過多少河流山川
停了多少站?
我的老家在信陽
此刻只走一半的路程
當火車再次前行
我卻無法安睡
我一邊數(shù)點窗外隱現(xiàn)的星星
一邊在想人類與萬物的命運
驛站
火車傍晚開進佳木斯
正趕上天降大雪
鵝毛似的雪花紛紛揚揚
鐵軌白了城墻胖了
凜冽的北風發(fā)出怒吼
它似乎要跟行人較勁
和樹林酒旗糾纏不放
我的旅行已經(jīng)結束
雪花和那些隱藏的人群
肯定還走在路上
站前喊叫住店的小畈
他們捂著臉穿著厚厚的大衣
在昏黃路燈下搓手
跺腳來回地搖晃
星星隱去夜空通明
的哥們蜂擁著旅客
他們常為10元錢的車費討價還價
我豎起衣領步人大街
風抽疼我的臉兒
偶有雪花落進我的脖子
讓我頓時感到?jīng)鏊陀H切
洗牛
一頭膘壯的老水牛
在稀泥坑里伸張四肢
它翻滾的動作像黃泥腌蛋
老水牛它正在腌制自己
主人大聲吆喝
它似乎沒有聽見
一根鞭子狠狠地抽去
它猛然起身奔跑
泥水在它身上四處飛濺……
它終于跑累了停下來
身上的泥水還未曬干
汗水卻從它鼻尖上滾出來
它回頭看看身后的主人
看看腳下那片新耕的泥土
老水牛朝天空吼了一聲
那長長的叫聲
很快就在酷熱的正午消失
主人罵它倔犟一陣抽打之后
又心疼地用井水給它沖洗
這頭黑色的老水牛
它不會跪下也不懂得珍惜
以至那個瘦小的男人
一遍又一遍
也未洗盡它龐大的身軀
夜行火車
這個喘著粗氣的笨家伙
還在黑暗中爬行
我坐在窗前在鼾聲
在鐵軌的撞擊聲里
穿過了一山又一嶺
漁火閃動夜蟲悲鳴
白茫茫的松花江在月光下涌動
逃荒的祖父開墾過的大平原
此刻除了村屯偶爾閃過的燈火
萬物仿佛在夜空下睡熟
看不下書也聽不進音樂
我的睡眠何時被夜鬼掠走?
當年那個倒鋪就睡的少年
再昴貴的安眠藥也無力回春
而白床單下裹著的那些身體
發(fā)出的磨牙聲夢囈聲
想必也是身不由己?
當年我跟父親經(jīng)常乘坐這列火車
父親已不在人世多年
我也結婚生子早生白發(fā)
今夜火車運送的這些男人女人
到站后將作鳥獸散
雪夜
關于雪夜我有過太多的描述
醉酒漫步風雪獨釣劫后逃生
這些我都早已心領身受
現(xiàn)在我又站江邊往日奔涌的松花江
已鋪展成白茫茫的大道
我要想去對岸不用船槳
半個時辰就能抵達
雪仍在下樹枝漸漸肥胖起來
松塔縫隙露出紅墻的水源寺
爐火正旺我雖手腳冰涼
但內(nèi)心卻很溫暖
在白雪面前誰敢妄言圣潔
看不見任何腳印除了路燈下
那些垂柳細粗的暗影
就是另一個我另一雙眼睛
我知道他們曾經(jīng)來過
盡管這里年年新修道路
他們和我一樣不老的松花江
重復了我們的生活
冬夜,我們圍坐火爐
冬夜,圍坐火爐等父親歸來
油燈的影子忽高忽低
在墻壁上擴大,晃動
母親擔心放牧牛羊的父親
“老天爺,這么大的雪,何時停下?”
她一會放下鞋底,向窗外張望
一會聽聽白毛風舞動鞭子
苞米垛發(fā)出呼呼啦啦的響聲
她想起了當年,為了公社食堂
父親在山里守了一夜,被送往衛(wèi)生院
兩天才緩過來,那時母親以為她的天塌了
哭得昏天黑地,敢怒不敢言
要把小弟送人……突然她轉(zhuǎn)過身
“那時人愚啊,沒辦法”
雪越下越大,松油在火盆里爆響
夜貓子從屋頂跳下,偶爾叫幾聲
夜深了,水壺的火車在轟鳴
沸騰的熱氣,并未緩解我們的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