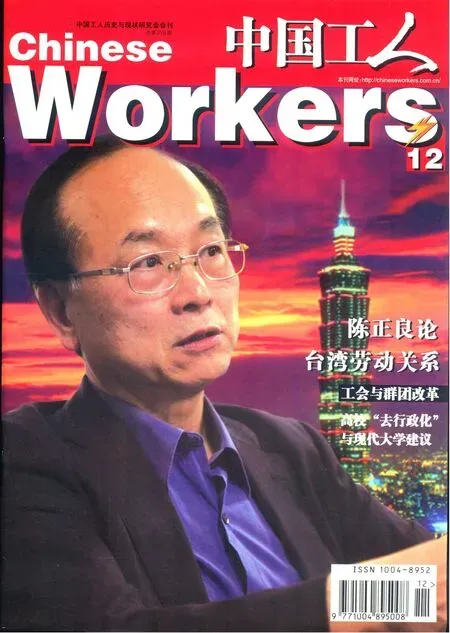老一代農民工的退路
2012年11月30日,一位名叫劉紅衛的中年農民工因為求職無著不幸染病又無錢可醫倒斃在鄭州市中州大道一立交橋下。劉紅衛的死一方面給他年邁的父親和年幼的兒子以及癡傻的弟弟留下了沉痛的悲傷和無盡的憂思,另一方面也對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和諧共建發出警示。人們開始追問,我們的社會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對弱勢群體的扶助是否考慮不周,負有宏觀經濟調控和公共事務管理職責的政府部門在農民工就業及生活保障方面是否力度不大。令人欣慰的是又有許多愛心人士在新聞媒體的倡導下積極為大橋下的農民工捐贈御寒衣物。時間過去兩年,2014年10月11日至13日,《東方今報》的記者再次探訪鄭州市中州大道立交橋下,發現仍有近百名收完秋糧,種完小麥的農民工露宿在橋下的馬路上等著攬活掙錢。事件被媒體披露后,“大橋下的農民工”又一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當我們的眼球被各種媒體紛紛報道的“大橋下的農民工”事件緊緊吸引的時候,我們的頭腦是否思考過“大橋下的農民工”何以會持續存在?“大橋下的農民工”連續多年出現,這不是鄭州市的個案,在全國許多城市都有高齡農民工自發聚集形成的馬路勞務市場。改革開放前30多年,中國經濟走的是一條依賴獨一無二的“人口紅利”實現低成本擴張的發展道路,如今環境與資源壓力日增,“人口紅利”開始漸行漸遠,國家開始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但前一階段發展留下的問題卻不斷凸顯,“大橋下的農民工”便是這諸多問題中的一個典型代表。“大橋下的農民工”不是不愿意去工廠上班,而是他們大多年齡偏大技術水平偏低,難以勝任新技術條件下的工廠工作;“大橋下的
編外保安
訪談者:老張,這么大年紀了,不在家抱孫子,怎么還在外打工?
張學耀:也是迫不得已啊。
訪談者: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到了該休息的時候就得休息。
張學耀:兒子在銀川剛買了一套房,孫子正在上小學,哪兒都需要錢;我不能拖累兒子,自己出來掙幾個,起碼夠我們老兩口的用度。
訪談者:在農村沒有承包地?
張學耀:有,全是干旱的山坡地,耕種一年連口糧都不夠。
訪談者:承包地沒有流轉給別人?農民工”不是不愿意住進溫暖舒適的旅館,而是他們的收入太低,旅館的費用太高,他們能夠承受的住宿費每天僅在5元到10元之間。作為提供公共服務的城市政府,多年來一直在竭盡全力地建設城市廉租房,可是“大橋下的農民工”是一群飄忽不定的打零工者,他們的打工狀態很難為他們提供比較固定的宿舍,搭建臨時工棚在規劃嚴格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是左右掣肘。當然也不能將這些被現代產業淘汰下來的高齡農民工拒之城市門外,他們妻子的醫療費、子女的上學費、家庭的日常用度以及子女成家立業的啟動資金,都得靠他們在城里不停地打零工來積攢。
高齡農民工的困難和問題遠不止這些。隨著年齡增大精力衰退,高齡農民工最終有一天要徹底退出城市勞務市場,到那時他們將何以為生?
來自寧夏同心縣預旺鎮的張學耀就是這樣,現在已經是63歲的人了,依然不能在家賦閑;我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穿著一身不太合體的保安服給寧夏某市科技館當臨時夜班保安。
張學耀:沒有。種糧沒有收益,誰還會承包別人的土地?
訪談者:在農村沒有經濟來源就到城里來打工了?
張學耀:可不是嗎?再說在城里找活路總比農村容易得多。
訪談者:你在這里當保安累不累?
張學耀:比起過去扛水泥砌磚頭一點兒都不累,就是守在值班室里坐一個晚上,中間隔幾個鐘頭出去巡視一下。
訪談者:夜班多長時間?八小時嗎?
張學耀:不是,是14個小時?
訪談者:怎么可能?一天干不動了自己的生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張學耀:那時誰想這個。窮了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過上囤里有糧袋里有錢的寬裕日子,再加上國家的政策一年比一年寬松,所以就覺得日子一年會比一年更好。
訪談者:人都會不斷規劃自己的未來,你那時對自己的未來是怎么規劃的?
張學耀:農民嘛,只要地里產糧手頭有錢,生在農村,長在農村,老在農村,這是祖祖輩輩的規程,還需要規劃?
訪談者:年輕的時候有力氣打工,將來有一天干不動了靠什么生活?
張學耀:靠子女啊,養兒防老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上一輩養了下一輩的小,下一輩就要養上一輩的老。
訪談者:外面干不動了就坐在家里讓子女養老?
張學耀:那肯定不行,還得在家照看孫子,幫著子女料理家務,由年輕人去外面闖蕩。
訪談者:你到城里去打工,看到人家城里人上班有工資,退休有養老金,一輩子逍遙自在,你有什么感受?
張學耀:挺羨慕的。可那時只有城里人有退休工資,農村人都是在家養老,習以為常了,就不會有非分之想。
訪談者:你是什么時候到銀川搞建筑的?
張學耀:1993年就去了,一直到2005年還在銀川的建筑工地上干。
訪談者:那時有沒有讓進城務工的人交養老保險的?
張學耀:聽說過,但那是個別工廠里給合同制工人交的。
訪談者:你當時就沒有想到要給自己交養老保險?
張學耀:咱干的是建筑行業,連工資都經常拖欠,老板怎么可能給農民工交養老保險。
訪談者:老板不交,自己就沒有想著給自己買一份養老保險?
張學耀:家里就等著我掙的工資買化肥買農藥以及日常開銷呢,哪兒還有閑錢買保險,況且還有三個孩子正在上學呢。
高齡農民工退而難休
訪談者:你是哪一年從建筑行業退休的?
張學耀:退休?一個打工的哪兒有退休?
訪談者:年齡大了,離開崗位回家休息就是退休啊。
張學耀:2005年,我五十多了,體力大不如前,有一次往架上搭架板,別人遞過來的架板我沒有接住,連人帶架板都跌到地上。雖然身體沒什么大礙,但后來老板就不讓我上架砌磚了,慢慢的我就在工地上沒活可干了。
訪談者:老板真絕情的。
張學耀:也沒辦法,老板是我跟了近十年的一個老熟人了,他說如果繼續讓我干,萬一哪一天出了意外,他負擔不起。
訪談者:退出建筑行業你就回家養老了?
張學耀:哪里啊?重活干不了還有輕活干啊。
訪談者:還在哪里去找輕活干呢?
張學耀:零散的輕活到處有,比如地面上的一些小型建筑工程,小區里面的物業維修,搬運東西,園林維護,這些活我都去干。
訪談者:你不是說年齡大了就回家幫著兒女料理家務,由兒女們在外打拼嗎?
張學耀:這不是世事變了嗎?現在的年輕人不但要在城里打工,還要在城里居住,把農村早都拋在腦后了,我還回農村幫誰料理家務?
訪談者:他們的孩子也不在農村住了?
張學耀:他們嫌農村的教育不好,都把孩子轉到城里讀書了。
訪談者:你可以回家耕種承包地啊,一年的收入起碼可以維持你們的生計。
張學耀:種地的費用在逐年上漲,可咱那干旱地區糧食產量不高,辛苦一年僅夠口糧;再者,我們年齡大了,種地的活已經干不了了。
訪談者:既然干不動農活了,就讓孩子們用打工的收入接濟你們在家養老啊。
張學耀:現在的孩子靠不住啊,他們掙的工資少,還要在城里扎根,不向家里要錢已經不錯了。
訪談者:那些住在農村的老人要靠誰來養老?
張學耀:自己能干動就自己蹦跶,實在干不動了再說。
訪談者:你現在還能干得動嗎?
張學耀:重活是干不動了,可像看門值勤打掃衛生園林綠化一類的活還能干動。
養兒不防老
訪談者:盡管現在還能干得動,但終究有一天就干不動了,那時該依靠誰來養老?
張學耀:肯定得靠子女,這國家法律講得明明白白;不過子女們在城里過得都很艱難,到時候指不定會給他們增加多少負擔呢。
訪談者:你有幾個子女?
張學耀:三個。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訪談者:他們都干什么呢?
張學耀:大兒子已經成家,兩口子都在銀川打工,去年買了一套房,貸了好多款,每月得還貸,孫子也上小學了。老二是女兒,也結婚了,小兩口在南方打工,那邊房子貴,以后也要回來買房。小兒子高中畢業沒有考上,現在跟著人家學汽車修理,將來怎樣還不好說。
訪談者:農村現在也開始搞養老保險了,你知道嗎?
張學耀:回去聽村干部說過,具體怎么實行不清楚。不過對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肯定沒希望。
訪談者:為什么?
張學耀:人家是讓有錢的農村人拿錢參加養老保險,而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是要用錢來養老,這就像正月十五貼門神——趕不上那年的事了。
訪談者:也是,要想享受保險,得先參加保險。不過我還聽說國家這幾年給農村高齡老人發放生活補助,你們有沒有領到?
張學耀:聽說有這個政策,可我這兩年沒有回去,不知道怎么辦理。
訪談者:一個月能發多少錢?
張學耀:前幾年聽說是50塊,這幾年漲了,但不知道究竟漲了多少。
訪談者:這也體現了國家對農村養老的重視。
張學耀:白拿錢應該知足,可這點錢放到現在沒多大作用。
訪談者:也別灰心,國家正在對養老體制進行改革調整,城鎮養老理順以后就該輪到農村了。
張學耀:但愿能有好的結果。不過國家的錢也是有限的,自己沒積蓄,國家能有什么辦法。
訪談者:國家通過宏觀政策支持農村地區養老體制改革,肯定會有好的結果的。
張學耀:這我相信。自古農民種地都要納皇糧,現在不但不繳稅,國家還給補貼。
訪談者:過去農村養老一直依靠土地,現在經濟發展了,土地的經濟價值更顯重要了,以后農民養老還可以借助自己在農村的承包地啊。
張學耀:那是人家發達地方的承包地,像咱們西北農村的承包地能值幾個錢?
訪談者:土地的經濟價值不是固定不變的,一旦形勢變化了,就會大幅度地升值。
張學耀:形勢會怎么變化呢?
訪談者:國家的經濟開發不是不斷向西部延伸嗎,再過幾年如果西部真正開發起來,土地肯定會增值。拿你們同心縣來說,如果有大規模的工業項目開發,經濟一火,土地肯定會升值。
張學耀:你是說土地一升值,農民就可以借助土地來養老了?但愿我們那里的土地有一天能升值。
農民工歌手旭日陽剛在《春天里》唱道,“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請把我留在那時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把我埋在這春天里。”旭日陽剛設想的那一天還沒有來臨,但高齡農民工的退休以及養老問題已經現實地擺在我們的面前。這個問題如何解決,不僅僅是高齡農民工個人的問題,也關乎整個社會和諧穩定的大局。造成高齡農民工問題的原因從宏觀層面來說是經濟發展超前,社會建設滯后,從具體政策來講,是農民工在為國家的工業化城鎮化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針對他們自身的各種社會保障措施沒有同步跟進,以致現在急需享受社會保障的時候出現空缺。解決高齡農民工的退休以及養老問題肯定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要城鄉統籌多方并舉多管齊下,一方面要盡快建立健全農村居民養老保險服務體系,在該體系之內多方籌措資金,為老年農民工提供必要的養老保障,另一方面要針對高齡農民工開展有組織的勞務輸出,在他們身體健康允許的情況下讓他們通過務工增加收入,為以后的養老儲備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