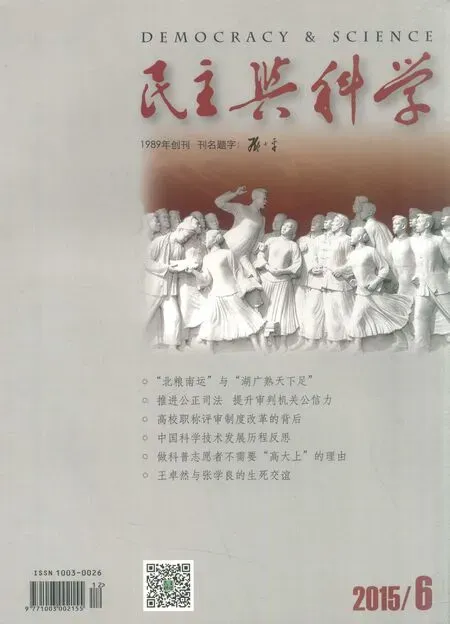誠信原則之價值功能
■ 張成春
誠信原則之價值功能
■ 張成春
市場經濟與誠信原則
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歷史得益于法治保障,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主體用經濟學術語表述就是“經濟人”。經濟人是理性的、自私的人(追逐自身的、自私的利益),假設人們都試圖增加自身的效用并努力追求個人利益(理性的、自私的行為的假設)。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也就是民商法(市民法)中所謂的“人”——“民(商)事主體”。民商法為他們設定了平等的權利,允許其在法律允許范圍內依“契約自由”原則自由追逐自身利益,我國《合同法》的表述即是“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
必須注意,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經濟人”或“契約自由”理念極易借助“自由競爭”之形式被民(商)事主體所濫用。尤其是商法,被認為是“基于個人主義的私法本質,為那些精于識別自己的利益并且毫無顧忌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極端自私和聰明的人而設計的”。由于形式上的契約自由或平等原則,無法掩蓋和解決民(商)事主體之間客觀存在的巨大區別和差異(例如巨無霸的國際連鎖超市與小微供貨商),因此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欺詐、不公平競爭、壟斷等有違市場經濟理念的失信行為。在契約社會,由于市場經濟制度將經濟生活中的一切都轉化為交易過程,它便有著某種程度的對于傳統道德(或是非交易性道德)的沖擊與破壞力,那么,以經濟人設定和自由競爭為前提的市場經濟,是否不需要道德約束?
確實,市場經濟具有一種內在非倫理性。例如,作為市場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就是在冷靜地計算利害關系基礎上規律交易(強調經濟效益而鼓吹主動違約的“效率違約”理論一度曾甚囂其上)。但是,如果利己主義的泛濫使這種非倫理性變質成反倫理性,那么合同法就會違背人民感情而受到抵制和攻擊。因此,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撰寫《國富論》之后,又窮余生之力寫作《道德情操論》不是沒有理由的。尤其是法治社會中,以“經濟人”設定和“自由競爭”為前提的市場經濟并非與道德倫理格格不入,而是相反,法治社會應當通過把基本道德準則提升到法律原則高度,從而提升市場經濟主體的道德水準和精神境界!
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經濟是信用經濟,誠實守信應該是最基本的商業道德。因為只有按照此種商業道德行為,才能保證交易活動能夠高速快捷地進行,從而形成正當穩定的商業信用乃至社會信用交易秩序。另一方面,誠實守信也是交易當事人為維護彼此之間信用關系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商業道德。它是人們行為的最低標準,究其本質,誠信原則由于將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合為一體,兼有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雙重功能,使法律條文具有極大彈性,法院因而享有較大裁量權,能夠據以排除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調整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因此,誠信原則被奉為現代民法的最高指導原則,學者謂之“帝王條款”。
誠信原則地位與作用之法理解讀
從國外立法看,誠信原則法律地位確立,肇始于《德國民法典》“債務關系編”第2條(即著名的《德國民法典》第242條):“債務人有義務依照誠實信用所要求的方式并考慮交易習慣,履行給付。”實踐中,該條款并不僅僅適用于債法,而成為一條適用于整個《德國民法典》的“超級調整規范”。瑞士、日本、泰國、我國臺灣地區等地的民法典也紛紛將誠信原則規定為民法基本原則。日本在戰后特殊情況下修訂民法典,增添了誠實信用的規定。根據這一原則,有關誠信原則的法院判例在恢復與維持市場道德秩序中發揮極大作用。廈門大學教授徐國棟在批判了長期以來學術界把“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過錯責任”這三項運用于不同民法領域的民法具體原則作為“私法三大原則”的傳統思潮后,指出“西方民法的基本原則基本上只有誠信原則一個,它的效力貫穿于西方國家民法始終”。
在我國民商法體系中,處于統帥地位的《民法通則》在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信原則。這就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確認誠信原則的地位。誠信原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