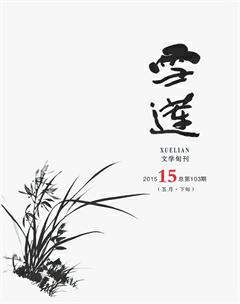洋芋,香味飄散中的記憶
陳生龍
小時候,洋芋是河湟地區農家來說,是一日三餐的主要食材。有人風趣地說:“早上烤洋芋,中午炒洋芋,晚上的生活改善了,把洋芋蛋蛋搗爛了!”
兒時,第一個學會做的飯便是焪洋芋了。母親天還沒亮就得出工。母親出門前從三四米深的土窖里,取出半背斗來,把洋芋洗干凈,放人缸粗的深腰大鍋里,倒人半罐水,如果有昨晚剩的飯,也一同放人鍋內。再在鍋沿上圍好胳膊粗的草圈,蓋上厚厚的木鍋蓋。還要在蓋得不太嚴的地方圍上一圈抹布。臨出門,母親一定來到炕沿根對迷迷糊糊的我喊一聲:“早點起來烤洋芋,吃了上學去!”那時還沒有電燈,尤其冬天,差不多是半夜爬起來,點亮廚房半墻上土洞里的那盞青油燈,拉著風箱迷迷糊糊地開始焪洋芋。一鍋洋芋要烤熟,約需四五十分鐘。開始不知道洋芋烤熟的狀況,時間掌握不好,要么還剩著水,洋芋開不了花,要么洋芋被燒焦了,滿鍋的洋芋一股難聞的糊味。母親告訴我,洋芋熟了的時候,將耳側在鍋旁,聽到鍋里面有“吱吱吱吱”的響聲,且能聞到一股洋芋焦巴的香味,就知道洋芋熟了。焪得剛剛好的洋芋,一揭開鍋蓋,一個個洋芋都會裂開笑得異常燦爛的口子,有的洋芋皮幾乎全脫開了,吃到嘴里,沙沙的,香香的,等不及涼一下,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填,盡管燙得嗷嗷直叫,猛烈地往外吹氣,但一疙瘩一疙瘩往下咽的感覺,不知道有多過癮,好像再沒有比這更好吃的東西了。
那時的早飯自然就是洋芋了。父母親在地里忙農活,等他們回來,我們兄妹早已上學去了。上學前,也沒有功夫消停坐下來吃,先把弟弟妹妹打發走,洗把臉,往書包里塞幾個洋芋就往外跑。一路上邊吃邊走,剝下來的洋芋皮扔在身后,常常有一個或幾個哼哼叫喚的小豬跟在我的身后搶著吃扔下的洋芋皮。有吃不完的洋芋,到校后烤在泥爐子上,可那烤得熱乎乎的焦巴洋芋就不一定能到你的手里了。
父母親差不多半晌午才能回來吃早飯。一般人家的洋芋都會挑著先吃好的,也有人家吃洋芋,怕是把好洋芋挑著吃了,不好的就浪費了,用一只手剛剛能伸下去的小口沙罐裝的芋放,吃的時候,手伸下去“抓住哪個就哪個”,不準挑挑揀揀。
早上焪的洋芋除了洋芋皮和壞的,好洋芋絕不能丟棄,等到晚上做飯的時候,再往灶火里一塞,烤熱了拿出來再吃。從灶火里扒出來的洋芋蛋黑糊糊的,往地上輕輕一敲,將草灰抖掉,剝開已烤焦了的皮,香氣撲鼻,比早上笑開了嘴的洋芋還要香甜。
奶奶在世的時候,等父母親下地后,把剩下的洋芋一個個剝得精光,盛在大盆子里,到中午或者晚上,放到鍋里,澆點油,用鐵勺背將洋芋搗爛,撒點鹽和腌好的花菜,熱好了再盛到碗里,那又是另外一種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