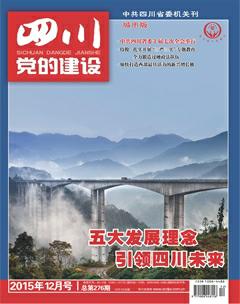“成為真正的城市人”
雷怡安
45歲的王德光算是很早一批從農村老家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看著一幢幢高樓在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王德光說:“我這20年就貢獻給了這些高樓。”王德光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主要負責蓋房子,蓋了幾十幢房子,他一幢也沒進去住過。記者問他想住到自己修的房子里去嗎?王德光憨憨一笑,說:“農村人,遲早要回老家的。”王德光的兒子今年20歲,在幾歲的時候就被大人從農村帶到了城市,十多年的城市生活,他認為自己就是個城市人。“如果我爸要回農村,他就回去,我要留在成都”。對于未來的規劃,兒子似乎很清晰,“聽說戶籍制度改革了,以后我就是城里人了,我要在成都買房子,成為真正的城市人。”
“成為真正的城市人”,說出了絕大多數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的心聲。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和國務院在《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中均提出“抓緊實施戶籍制度改革”,多地明確提出“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的時間表,并明確建立落實居住證制度。而四川也是積極響應的城市之一。如何能夠真正成為城市人,完成農民工市民化的轉變,在當前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中顯得格外的重要。
龐大群體的利益訴求
“我們兩口子出來打工,孩子上學問題如何解決?”“在農村我們有新農合,到城市來以后社保應該如何繳納?”“城市房價太高了,我們買不起。”……
記者采訪了多位農民工,上述問題是他們考慮最多的,也是最現實的。據悉,截至目前,全國有2億6千萬農民工,四川有2470多萬農民工,這樣一個龐大群體是跟隨社會發展的需求誕生和流動的。
他們走進城市,一面為城市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一面也在積極尋求自身的利益保障。
“很多農民工有新農合,這歸衛計委管,城里人的社保歸人社廳管,因此當農民工來到城市打工,就會面臨許多麻煩,所以建立醫保一體化才能更好地維護農民工的權益。”四川省農勞辦主任黃曉東說。
在浙江打工的丁利元今年準備把孩子送回四川老家上學,“因為戶口沒在當地,以后會面臨孩子初中、高中無法參加當地考試的問題。”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一直是農民工進城打工面臨的難題之一,如果不能將子女的教育問題落實好,許多農民工害怕自己的孩子又成為跟他們一樣的“邊緣人”。
像王德光這樣在成都打工了20年依然租房住的農民工不在少數,雖然也存了一些錢,但是他還是無法負擔城市里的房價。“房價對于我們來說還是太高了,買不起,也住不起”。
2015年9月中下旬,四川省統計局在省內部分地區開展了進城務工人員市民化現狀問卷調查表明,目前進城務工人員在市民化意愿方面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半數以上進城務工人員不愿將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省內中等城市是進城務工人員落戶城鎮的首選地,進城務工人員對用農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權換取城市住房存在較大分歧,半數以上進城務工人員愿將農村醫、社保轉換為城鎮醫、社保。
據調查,基本住房保障是進城務工人員最希望享有的市民化待遇。調查顯示,在被問及“您認為進城務工人員要享有本地市民同等待遇,目前最急需解決的基本公共服務問題是什么?”選擇居前三位的依次是基本住房保障、基本養老保障和子女義務教育,占比分別為50.9%、42.2%和37.5%。醫療衛生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勞動技能培訓和失業保險也受到較多的關注,選擇占比在18.8%—28.7%。
據相關資料顯示2014年四川省城鎮化率44.9%,2014年中國城鎮化率54.77%。大量的農民工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還在艱難的推進之中。
融入是一條漫長的路
1989 年,學者黃祖輝第一次提出農民工市民化的概念。而一般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是一個農民工不斷融入城市生活、逐漸培養現代社會意識和生活方式,最終達到整個社會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
隨著社會的發展,一大批農民身份的人進入城市,勞動性質從農業轉向非農業,于是學界將這一群人定義為“農民工”。這個詞本是一個中性詞,只是一個身份的表達,但由于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一方面充實了勞動力,特別是繁重勞動力,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城市問題的不斷發生。因此逐漸地,農民工在城市出現被“邊緣化”的傾向。
在成都市新空間青少年發展中心,記者見到了豆豆。他跟隨進城務工的父母來到成都,面對這座陌生的城市,豆豆感到很無助:這里沒有熟悉的老師和朋友,也沒有熟悉的鄉間小路……這種陌生感讓他越來越沉默和自卑。新空間的志愿者們想方設法讓他參與到和同學的互動中,但一次次努力均以失敗告終。“他們都不喜歡我,我為什么要加入他們?”豆豆問的這句話令志愿者至今記憶深刻。
除了物質層面平等的獲得感,絕大多數農民工還希望得到心理層面的平等感。“被歧視”是農民工進入城市后,感受最深的一點。記者曾在公交車上觀察到這樣的情況,年齡較大的農民工上車后,幾乎沒有人給他們讓座,不少農民工如果乘坐公交車都是選擇站而不是坐。一些乘坐公交車的市民認為:他們是農民工,所以自己沒有義務給他們讓座。
農民工維權機構也是隨著農民工進城后日益興起的一個組織。由于農民工很多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識淡薄,因此在遇到被拖欠工資、惡意辭退等情況時,無處討要說法。要不然就演變成爬上高樓要跳樓的悲劇,要不然就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
農民工要真正實現市民化的過程是不易的,雖然來到了城市,卻依然被城市人對他們的固有印象所鉗制。
市民化進程再提速
王德光想回到老家去,一方面有對老家的思念,另一方面也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他認為自己在城市里已沒什么生存空間了。王德光所謂的生存空間就是指自己年齡越來越大,在建筑工地上也干得越來越吃力,又沒有其他的技術,不能賺到錢,在這個一出門就得消費的城市,他確實吃不消。同時,這么多年的城市打拼,他的獲得感其實并不多,他更像是城市中的過客。endprint
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在北京約有1/3的常住人口沒有北京戶籍,因此不能全面享受教育、醫療等多面的服務。面對人口的大規模遷徙,政府的財力上顯然是有一定的壓力和負擔。
“提升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幸福感獲得感,其實需要三方面共同作用。”黃曉東告訴記者,政府必須要有所作為,在醫療、就業、衛生、教育、住房等方面對農民工全覆蓋,保證社會的基本公平;而城市中的市民需要尊重農民工的勞動成果和利益訴求;農民工更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和技能。只有這三方面都努力了,才能真正完成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
農民工市民化并不是說讓所有農村人都進入到大城市工作安居,而更多的是發展特大城市、大城市以外的中小型城鎮規模。像王德光這樣的農民工,就算回到老家也不會再從事有關農田勞作了。對于這批返鄉的人,四川省大力開展針對返鄉農民工的技能培訓,使他們既能回到家鄉照顧親人又能夠掙到錢。從省人社廳到各地市州的人社局,不定期的都會對回鄉的農民工進行技能培訓和職業化培訓,目的就是希望他們盡早地完成轉變。
201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關于印發《四川省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核心有兩條:嚴格控制成都市人口規模,成都市改進現行落戶政策,建立居住證積分入戶制度;公民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市(州)居住半年以上的,可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享受多項權利。
戶籍制度的進一步改革,使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再一次提速,在城市里,還有很多像王德光和他兒子一樣的老農民工和新農民工,他們的未來到底是怎樣?城市能夠真正容納下他們嗎?(責編:李靜)
鏈接
2015年4月頒布《四川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實施意見》
落戶:認為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為前提條件,全面放開除成都市外的城市城鎮落戶限制,促進農民工進城落戶,享受同等市民權益。
教育:在公辦義務教育學校、幼兒園不能滿足需要的情況下,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在依法舉辦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幼兒園入學。
社保:確保有穩定勞動關系的農民工隨用人單位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醫療保險,鼓勵其他靈活就業的農民工自愿選擇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醫療保險或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
住房:建立健全農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對在城鎮穩定就業并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按城鎮戶籍居民同等準入條件、同等審核流程、同等保障標準申請享受公共租賃住房保障,逐步實現農民工住房保障常態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