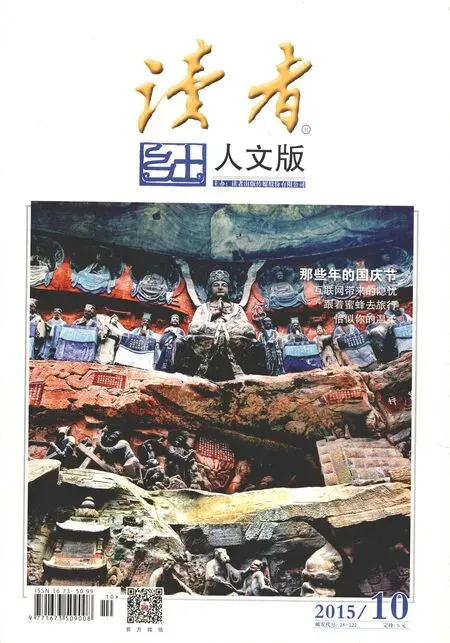恰似你的溫柔
文/葉 子 圖/小黑孩
恰似你的溫柔
文/葉子圖/小黑孩

“荷,手心手背都是肉,把你送給你小姨是出于無奈。當時選擇你,就是覺得這些孩子中你是唯一不會怨我的!”
大哥打來電話要我抽空回運城一趟,我問家里是不是發生了什么事?大哥呵呵一笑:“小荷,你不肯回運城,是不是還在和她較著勁?”
大哥說的“她”現在是我大姨,15年前是我媽媽。
那一年,她帶我坐綠皮火車去洛陽看望小姨,窗外大雪紛飛。我問她:“媽,咱在小姨家住多久?”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表情怪怪的,直到我昏昏入睡,她都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答復。小姨嫁到洛陽,家里條件優越,可結婚多年一直沒有孩子,家里空蕩蕩的。在小姨家,她把我支出去,和小姨嘀咕了好一陣子,最后告訴我,要我留下給小姨做孩子。
兩天后的清晨,她和她的旅行包不翼而飛。11歲的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我被她狠心地遺棄了!
她有一個兒子、兩個丫頭。
起初我排斥小姨和小姨夫的親近,認定都是他們惹的禍。漸漸長大,我徹底明白她是真的不在乎我,就開始順應環境靠近小姨。小姨和小姨夫對我百般寵愛,她的影像在我的記憶中一點點淡出,我完全融入了一種全新的生活。
偶爾,她會和大哥來洛陽走親戚。
大哥從小疼我,為她把我送給小姨和她慪了好多年的氣。她對著小姨罵我倆不開竅,跟著誰不是親的?小姨抱歉一笑:“小塘、小荷,委屈你們了。”這句話讓我和大哥鼻子一酸,從此再不提這個話題。
我上大學那年,她讓大哥送來一床新被褥。小姨要我帶到學校去,我不肯。我雖然不再怨恨她,可對她也再無任何依戀,心里的她只是一位遠親,而她做工粗糙的被褥我不稀罕。
我結婚時,小姨要我通知她和哥哥、姐姐一起過來,我猶豫不定。這些年我已經變成地地道道的河南妹,同學和朋友根本不清楚我的身世。
打通電話,我支支吾吾表達出不想讓她來參加婚禮的意思。她在電話那端愣怔了半天,最后釋然一笑:“你是小姨的孩子,我怎會計較你敬不敬那杯茶?”本地風俗,女兒結婚要給媽媽敬茶,并且要抱一抱媽媽。
她真的就沒來參加我的婚禮,但讓大哥給我帶來一床新被褥。婚禮上鞭炮齊鳴,我給小姨敬茶并緊緊擁抱她。小姨嗚咽著在我耳畔喃喃自語:“要是大姐也在就好了!”
半年后,她來洛陽看牡丹。
我把她和小姨接到我家,去做手搟面。她站在廚房門口默默地盯著我,卻一句話也不說。氣氛有點尷尬,我讓她去客廳看電視。她猶豫著問:“有空,你回運城轉轉?”這個問題讓我措手不及,搟面杖骨碌碌滾落砸在腳面。
看我抱腳而跳,她慌忙改口:“還是我過來看你吧!”小姨趕緊替她解圍:“小荷常說想去運城看看鹽湖呢,等她有空我倆一塊兒去!”我撿起搟面杖冷冷地說:“等我退休了再說吧! ”
大哥在電話里命令我務必回一趟運城,不看僧面看佛面,家里不是還有一奶同胞的哥哥姐姐嗎?“小荷,她都老了,別怨她了!”大哥幽幽地說了一句。
騎虎難下,我只好收拾東西回運城。
推開“吱呀”的木門走進去,小院地上的青石板泛著白光。她在院墻角的灶臺前燒火,紅彤彤的火光映照著她佝僂的身子。我在背后默默地注視著她。冬日的斜陽染紅了她原本花白的頭發,凌亂的發絲在寒風中上下舞動。她抱膝而坐,靜靜地盯著呼啦啦燃燒的灶膛。
那天大哥在電話里說她都快70歲了,我有點不大相信。扳著指頭算一算,原來她真的到了古稀之年。這樣的年紀突然讓我心生酸楚,15年不在一起生活,她仿佛一夜之間就變老了。
她不肯隨哥哥姐姐住進舒服的樓房,堅持在小院里延續自己多年的生活習慣,養花、種菜、燒火做飯。大哥說單位的同事都責怪他不管老太太,他冤枉死了!他說:“小荷,你回來勸勸她跟著我過吧,享享清福!”
我心疼因為她的執拗而焦灼煩惱的大哥,我擔心她獨自在小院里有什么閃失。盡管對她的感情淡淡的,但我不希望她出事。
她起身掀鍋蓋,一眼就看見站在院中央的我,她不敢相信地揉揉眼睛。我猶豫片刻低低叫了一聲“大姨”。她拎在手里的鍋蓋哐啷掉了下來,露出蒸鍋里白花花的饅頭。我過去幫忙取出饅頭,回過神的她趕緊叮嚀:“小心,別燙了手!”等她手忙腳亂炒好菜,天已經黑了。
客廳的墻上掛著泛黃的全家福,梳著麻花辮的我被她緊緊抱在懷里。照片中她穿一件淺藍色旗袍,風華正茂。她湊上來看兩眼照片,說:“那年你才一歲半,照相館的旗袍箍得我透不過氣來!”
我說:“你為什么不帶一件新衣服去照相?”她嘆氣道:“當年家里人多,經濟緊張,哪有閑錢添置衣服?”我不免心里一動:“怪不得你要把我送出去!”聽到我抱怨的話,她身子一晃,趕緊拉把椅子坐下。
白熾燈散發著昏黃的光暈,她坐在椅子上低垂著頭。
我突然有些不忍心了,事情都過去那么久了,何苦再為難她?于是我坐下來吃飯,順便給她斟了一盅酒。她哆嗦著手捏住杯子,顫聲說:“小荷,一個女人沒孩子拴不牢男人的心!”我以為她在說我呢,仔細一想,才明白她是在說小姨。“當初我也猶豫過,可我不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妹妹過不成日子。”她喃喃自語。
我給自己斟了一盅酒,說一千道一萬,她還是愛別人比愛我多一些。“杏花村”酒辛辣,我忍不住打了個噴嚏。她慌慌張張按住我的酒盅,用極小的聲音說:“小荷,對不起!”
洗漱完畢,我和她去臥室睡覺。
老房子沒有暖氣供應,她插上電暖器。我盯著那張大木床有點走神,兒時的我最喜歡和姐姐擠在這張大木床上,聽她唱“信天游”。一眨眼,人去床空,我想象不出一個人的夜晚,她是怎樣度過的。
她抱出新被子,給我鋪了一個單獨的被窩。
“明天,你上小塘家睡去,他家暖和。”她說著和衣鉆進自己的被窩里。我想起大哥的種種抱怨,就勸她:“你把這里租出去上大哥家住好了,免得大伙擔心你。”她問:“你怕小塘不放心?”“不是他不放心,是我!”不知道為什么,我脫口就說出這句話來。
對于我這樣的回答,她或許深感意外,老半天沒有出聲。沉默中我也覺得有點別扭,坐在床邊不知所措。“荷,手心手背都是肉,把你送給你小姨是出于無奈。當時選擇你,就是覺得這些孩子中你是唯一不會怨我的!”
她的聲音嗚嗚咽咽,像飽受委屈的孩子。
我的眼前猛然浮現當年她帶我坐綠皮火車時,她不停地給我嗑瓜子剝著橘子的情景。耳畔似乎還有她近乎討好的聲音:“荷,再吃一瓣橘子好不好?”“荷,再吃點瓜子仁好不好? ”
舊事像海浪一般洶涌而來。
小時候,她在黎明前把熟睡的我移到床邊,悄悄給我梳好麻花辮,等我起床就可以優哉游哉喝她熬的小米粥。晚上我賴在大木床上不肯跟姐姐去睡覺,她就笑瞇瞇許愿:“荷,乖了,等你上大學、結婚,媽媽給你做軟軟的棉花被。”
爸爸去世那一年,她天天抱著我走來走去。懂事的大哥要我自己下來走,她卻不放手。如今想來,她是把我作為抵御悲傷的一種慰藉,如果我不是她的至愛,怎能有這樣神奇的力量?
我終于肯相信如她所言,她當初確實舍不得把我送給小姨,只不過是姐妹情意作祟,兩難中稀里糊涂就把我舍出去了。但她認定我是三個孩子中唯一不會怨她的。這樣的念頭,我認為真的好傻。
她在我的身邊輾轉反側。“冷嗎?”我說著伸手替她掖好被子。她突然問:“荷,你一直在怨我嗎?”縷縷暖氣在黑黢黢的臥室來回穿梭,我的心頃刻間柔軟了。
再一次躺在她的身邊,竟和上次隔了15年的時光。漫長的時間一點點把怨恨沖淡抹平,剩下掩蓋不住的憂傷。不是為她當年的離棄,只為眼前,她怯生生握住我被角的那只手。
大哥說她不肯搬遷是在等我回家。這話,我現在深信不疑。
我悄悄把自己的手掌覆在她的手背上,把我的溫暖一點點傳遞給她。她都已經給我道歉了,我還怨什么?“要不是你這樣做,我現在咋會有兩個媽媽呢!”我盡量把話說得委婉含蓄,太直白的表達,我一時間還真有些不大習慣。“不怨就好,媽就安心了。”她果真激動不已。“過幾天你去洛陽待一段時間吧,給我做做飯。”我發出邀請。她連連應承,在被窩里開心地笑了。
夜未央,心情澎湃的她竟然哼唱起“信天游”來。熟悉親切的歌聲恰似她當年的溫柔,只是她身旁的孩子卻落下淚來。
(宋宏圖摘自《人生與伴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