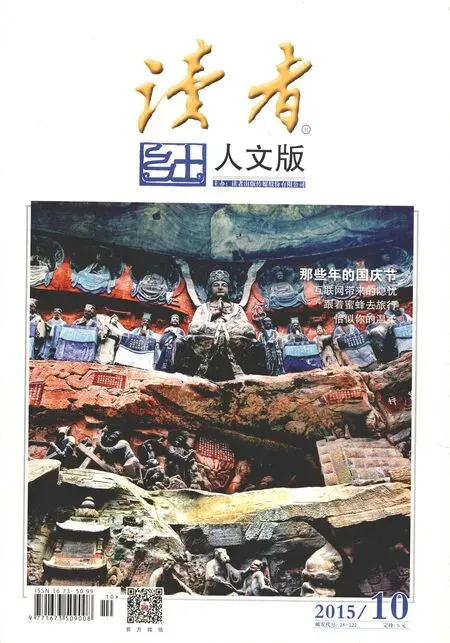向上的炊煙
文/米抗戰
向上的炊煙
文/米抗戰

一
見過許多鄉土題材的畫作,大凡描繪村莊的作品,總能找到幾筆淡淡的炊煙,其中一抹炊煙會為畫面平添煙火氣。
緣此,畫面一下子就靈動了,意境也增了幾分。
初見畫里的炊煙,是20多年前。那是一張鄉土題材的國畫,有田地、有樹木、有房子,當然少不了炊煙。那幅畫印在母親糊墻的一張報紙上,皺巴巴地從墻上鼓起來,有兩個火柴盒那么大,被煙熏成了褐黃色,極像黃土地的調子。
母親做飯,我幫著燒鍋,手拉著風箱的桿子,頭一扭就看見了它。
那畫貼倒了,母親一定是無意的。想看得順眼,只得彎下脖子,將眼睛倒過來。眼睛倒過來的時候,畫里的炊煙就正了。
看罷,我就再沒有留意過它。
我得專心燒鍋,因為辛勞的父親即將歸來。
二
炊煙,總在風雨云霞的背景中律動。
炊煙裊裊的生活,永遠是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日子沒法過了”的話,女人說,男人也說,說了是說了,從來就沒人在意。飯吃不吃都在鍋里,碟子碎了還有碗。偶爾的冰鍋冷灶,不過是短暫的休整。
日出日落,月缺月圓,一搟杖能搟平的疙瘩都不算疙瘩。這坎兒那坎兒的,也不過是灶前的蔥胡子蒜皮子,一把火就能化腐朽為神奇的小磕絆。一旦炊煙升起,鍋碗瓢盆重新奏響,寧靜平和的生活就又回來了。
一抹炊煙激活了生活。這才是生活的常態。
生活,壓根兒就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男人下了原,女人做了飯”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三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炊煙不升的當兒,遠望一個村莊,總覺得是殘缺的。譬如此刻,我又一次站上了村外的山岡,為的是遠遠地望一望久違的炊煙。其實不必趕這一趟的,只要閉上眼睛,憑著記憶就能想象出村莊溫情的樣子。況且,來路逼仄,雜草叢生。
可我終究還是來了。
雖有淡淡的晨霧氤氳,村莊依然是不完整的。炊煙之于村莊,如同鼻息之于頭顱,這一對密友,從遙遠的石器時代攜手走來,早已融為一體,共同經歷了人類繁衍生息的歷史。
晨霧,怎么取代得了?
晨霧氤氳的村莊,總讓人覺得是惺忪的,瞥一眼,都能染你一身睡意。試想,彌散的霧,怎么可能具備炊煙的精氣神?
四
煙,因火而生,從來就不乏熱情。
一把柴火填進灶口,裊裊娜娜的炊煙就升騰起來,合著風箱“吧嗒吧嗒”的節奏,總能將農耕生活的情趣演繹得淡定而灑脫。縱然日子平淡到“一口清水鍋,三碗柴火飯”,每一縷炊煙都向著天空升騰。
脫胎于草木的炊煙,理應攜帶著向往天空的品性。雖立根于黢黑的灶穴,卻不忘將追求向上的精神薪火相傳。無論沐風還是櫛雨,總是一如既往地向上升騰。若要為農耕文明尋找一種精神象征,我以為只能是炊煙了。
此起彼伏的炊煙,連綿不斷的炊煙,經久不散的炊煙……林林總總,彰顯和繚繞著的是一幅人間最催人向上的生活畫景,寧靜、溫馨、和諧,哪怕只是淡淡地望一眼,也讓人通體愜意。
(吳正引摘自《時代青年》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