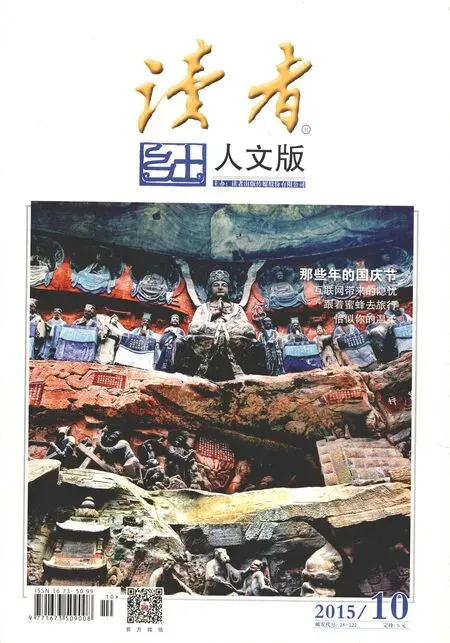一個人的移動照相館
文/任 春
一個人的移動照相館
文/任春
一
1月29日,四川達州地區飄起了2015年的第一場雪。
早上7點多,萬燕明發動了他的那輛小排量的紅色小轎車,帶上攝影包、易拉寶、相片打印機等他下鄉拍照的“標配”,離開了達州市區。這一回,他難得不是一個人下鄉,在四川師范大學讀大一的兒子萬千一,自告奮勇給他當攝影助理。
兩個多小時后,車下了高速,直奔宣漢縣的下八鎮。
請萬燕明來拍全家福的符純珍,其實與他并不相熟,只因萬燕明多年來進山下鄉給村民義務拍照,被十里八鄉的村民親熱地稱為“萬老師”,頗有名氣。春節前,符純珍在廣州打工的大女兒回來了,在縣高中上學的小兒子也放假了,好不容易一家人都湊齊了,她便打電話,請萬老師來拍一張“全家福”。
今年40歲的符純珍,被宣漢縣下八鎮建設村的村民們一致推選為婦代會主任。6年前,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年輕漂亮的她在追求者面前立了一條硬指標:必須同意她帶著公公婆婆一起改嫁。
在跑運輸的那段日子里,她和樸實善良的郭興茂相識相愛。成婚后,兩人組建了一個特殊的大家庭:符純珍的父母、先夫的父母、郭興茂的父母,一共3個爸爸、3個媽媽,還有5個小孩。
2013年,夫婦倆籌資建起了自己的苗木基地,丹桂、紫薇、海棠、蠟梅、紅楓等名木落戶園中。去年的“三八”婦女節,夫婦倆還掏錢慰問了村里32名80歲以上的婆婆。
拍照這天,無論是86歲的郭爸爸,還是尚在襁褓之中的符純珍的外孫女,4代人一共15個家庭成員,都打扮得格外漂亮,精氣神十足。
面對這樣一個和睦溫暖、相親相愛的大家庭,萬燕明被深深感動了。他不用常規背景,而是將符家的這張“全家福”定格在他們自己一手培育起來的苗木基地。茁壯成長的樹木,漸漸成熟的果實,不就是這個歷經磨難卻日臻美好的大家庭的真實寫照嗎?
“咔嚓”一下,一家老小15張笑臉,如同春天,綻放在廣袤的天地間。
一旁的“攝影助理”麻利地擺弄著相片打印機,不一會兒,色澤鮮艷的“全家福”徐徐地從機器里探出身來。
年紀最長的郭家仁用布滿老繭的手,摩挲著那張發燙的照片,喃喃自語:“活了這么老,總算盼到好日子了,一大家子太難得!”
下午,萬燕明帶著兒子又趕赴另一個山村拍照。他說:“過年了,打工的人都回家了,大家都想拍張‘全家福’,這也是過年的一道菜嘛。”
二
盡管已經過去了10年,但萬燕明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給村民拍“全家福”時的情景。
2005年,酷愛攝影與戶外運動的萬燕明與一群“驢友”來到重慶市城口縣大山深處的櫻桃溪。爬上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萬燕明看到,一個穿著補丁衫的小姑娘正帶著弟弟在院子里玩耍。小姑娘對這群“山外來客”充滿了好奇,那雙像山泉般清澈的眸子令萬燕明心頭一震。




萬燕明拿出相機對準小姑娘:“給你們拍幾張相片,叔叔過后給你們寄過來,要不要得嘛?”
“好嘛!好嘛!”兩個孩子雀躍歡跳。
小姑娘名叫袁詩詠,這居然是7歲的她第一次照相。
隨后,兩個孩子將他們的殘疾父親扶到屋外。袁詩詠告訴萬燕明,她媽媽去廣州打工了,她在學習之余還要照顧殘疾的爸爸。
給父女3個人拍完“全家福”后,萬燕明悄悄地往袁詩詠的衣兜里塞了200元錢。
回家后,萬燕明立即沖洗并按照地址寄出了照片。很快,袁詩詠姐弟回信了,字里行間充滿了感激:“要不是認識了萬伯伯,我們家的生活那么困難,誰還拍得起照片啊!”
因為這次大山里的邂逅,姐弟倆就成了萬燕明心中的牽掛。每年暑假,萬燕明都去櫻桃溪拍照。這似乎成了萬燕明與袁詩詠姐弟的一個約定。
這次大山里的邂逅,也令萬燕明萌生了一個念頭:他要將鏡頭對準深山農村,對準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每次拍完照片,他都會仔細記下地址,將照片寄回去。
半年后,他添置了一臺相片打印機。這小小的“附件”能量超大:老人和孩子們看到自己的樣子從打印機里傳出來時,感到新奇、羞赧、開心、激動……每當那一刻,萬燕明覺得自己所有的奔波和勞頓都是值得的。
三
10年間,只要天氣好,萬燕明就會帶著照相機上山下鄉拍照。
10年來,多少大山里的村民走進萬燕明的鏡頭,他已無法統計。在他的記憶深處,百歲老黨員孫安壽面對鏡頭的那一瞬間,令他至今難以忘懷。
2011年初夏,聽說達縣趙固鄉錘虹村有一位1949年以前就入黨、已經百歲高齡的老黨員孫安壽,萬燕明立即開車前往拍攝。
聽村里人說城里的一位攝影師專門來為自己拍照,孫安壽讓家人找出一件過年才穿的新衣服,早早坐在老屋的大門口等著。當萬燕明爬上爬下、將印有天安門的背景板掛在他家老屋的后墻上時,這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老戰士的眼睛里忽然滾出了淚花。他輕聲嘆了一口氣,喃喃地說:“干了一輩子革命啦,我還沒去過北京噻,這次我能和‘天安門’照個相,也就算去過北京了。”
一陣酸楚涌上萬燕明的心頭。他大聲對孫大爺喊著:“老英雄,今天我給您老人家好好拍兩張!”
“看我的手勢,預備……”萬燕明一手握照相機,一手舉起示意,“咔嚓、咔嚓”,“天安門”前,孫安壽的胸前掛著陪伴自己度過了半個世紀、已有些銹跡的獎章,笑容燦爛。
大山里的留守老人,也常出現在萬燕明的鏡頭里,他說:“在川北一個偏遠的村子里,我曾遇到兩位耄耋老人,帶著6個小孩。老人滿臉皺紋,駝著背拄著拐杖,照顧著留守在家的外孫,臉上落寞與無奈的表情,看著讓人心疼……”
每次拍這些留守老人,萬燕明總是盡己所能,說一些有趣的話調動他們的情緒。當透過鏡頭看到老人們在陽光下難得的笑臉,他感慨:“他們都是我們的父母輩了,一輩子為了兒孫們操碎了心,能留住他們臉上一絲歡樂的笑容,哪怕布滿滄桑,也是有意義的。”
四
10年來,萬燕明走遍了達州附近的100多個鄉村,跋山涉水去上學的孩子們天真無邪的眼神、豬圈旁煮飯的留守兒童、緊緊相擁在老屋門口的留守老人和孫子的微笑……這些打動了自己的照片,也打動了許多人,一些照片還被中國檔案館收藏。
漸漸地,“移動照相館”出名了。萬燕明也因為有多張作品獲獎,被選為四川省攝影家協會理事。2010年,他還被評為全國“抗災救災優秀攝影家”。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朋友主動要求和萬燕明一起去拍照。萬燕明反復強調的只有一點:“下鄉拍照,別把農民當模特兒,拍一張就跑了,一定要把照片給人家。我們要學會尊重被拍攝者,千萬別把自己看得太高,到了山里,山里人最大。”
拍了那么多年的照片,萬燕明說:“現在舉起照相機,我已經不大追求那種構圖、光線等攝影技巧方面的‘漂亮’,我想通過自己的作品,反映山村人真實的生活狀態,也許會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一些改變,或許可以引起有關方面對他們的關注。總之,能改變一點是一點,這是我以后著力想做的。”
萬燕明的舉動,也為自己贏得了一群特殊的“粉絲”。
在達州開著一家廣告公司的顏懷見,學著萬燕明的樣子,辦起了自己的移動照相館。略有不同的是,他的噴繪背景墻是長城圖案,比萬燕明的更高更長。
顏懷見說:“四川有那么多大山,萬老師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做的是有意義的事,以己之力,給別人帶去了溫暖和快樂。”
有溫度的影像,是有力量的。
(鄒敏君摘自《解放日報》2015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