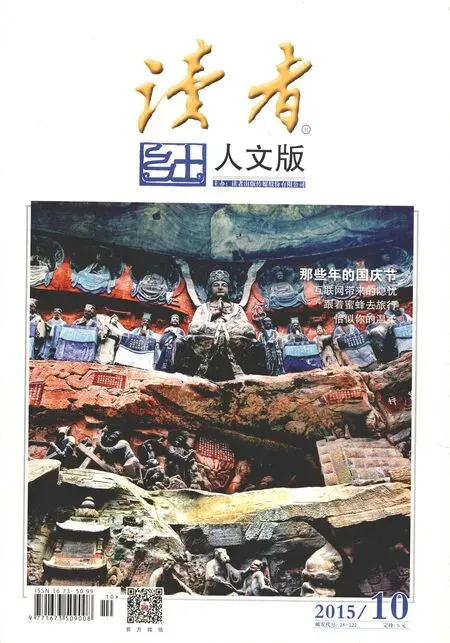節(jié)外生姿
文/謝 凱
節(jié)外生姿
文/謝凱

臺中市的中華路以繁華熱鬧聞名,不過在這條路上卻隱藏著一處“世外桃源”—觀竹堂。這里是竹雕大師陳銘堂的工作室,也是對訪客開放的竹雕藝術(shù)館。推門進(jìn)去,撲鼻的竹香讓人頓時忘掉室外的喧鬧燥熱,腳步慢了下來,頗有尋幽谷訪仙境之趣。每有訪客來,陳銘堂都會泡上一壺清茶,在茶香氤氳間,分享他竹雕創(chuàng)作之路上的那些名堂。
再現(xiàn)童年生活
“講話請大聲一點哦,我的聽力不好。”陳銘堂一邊微笑著說,一邊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因為他覺得讓訪客重復(fù)說一句話有些不妥,于是讓妻子陪伴在側(cè),沒聽明白的時候就讓她在耳邊重復(fù)給他聽。
話匣子剛一打開,陳銘堂就像頑童一樣,拿出一只只他新近創(chuàng)作的竹雕青蛙,滿懷喜悅地介紹說:“這是剛睡醒的青蛙,正在打哈欠伸懶腰;這是吃飽喝足后的青蛙,正摸著圓鼓鼓的大肚子;這只青蛙準(zhǔn)備向心儀的對象求愛,你看到它拿的棒棒糖了嗎……”與常見的竹雕青蛙不同的是,這些青蛙全由竹頭雕刻而成,立體逼真,表情逗趣,看到就想笑,但又不敢笑出聲來,好像它們一聽到聲音就會四散逃去。
“來,再摸摸。”陳銘堂大方地說。見慣了其他大師對自己作品的呵護(hù)有加,陳銘堂的話反而叫人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地把青蛙拿在手里,竹頭纖維特有的細(xì)膩質(zhì)感讓人愛不釋手。問到雕刻青蛙的原因,陳銘堂說:“小時候我生活在農(nóng)村,因為聽力不好,我在學(xué)校讀書時屢屢受挫,于是我把探索的目光轉(zhuǎn)向了沒有教鞭與考試的鄉(xiāng)間田野,釣青蛙、養(yǎng)青蛙成為我最喜歡做的事。青蛙是我童年的好朋友,雕刻它們就是為了回憶那一段快樂的時光。”除了青蛙,童年生活的其他經(jīng)歷和見聞也一直是他創(chuàng)作的主要靈感來源。在觀竹堂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小狗逗小烏龜玩,一群孩子在歡樂地捉迷藏,貓直身仰視站在高高芭蕉葉上的小鳥……甚至還有陳銘堂小時候看人家吃西瓜時垂涎欲滴的模樣。
重塑新竹雕
孟宗竹和刺竹是陳銘堂創(chuàng)作的竹材,雖然它們纖維細(xì)密,是做竹雕的好材料,但硬度高,不容易雕刻。不過,從13歲學(xué)習(xí)竹雕,至今已有40多年雕刻經(jīng)驗的陳銘堂,卻有自己獨特的“馭竹術(shù)”。“把竹子當(dāng)情人,經(jīng)常和她談心,心中有情,再雕刻就容易多了。”說完,陳銘堂轉(zhuǎn)頭看了看妻子,兩人目光交會,都抿嘴笑了。

除了用竹頭,陳銘堂的很多作品都以竹身為載體,而要在有限的弧面上創(chuàng)作,自然會受到諸多限制。陳銘堂想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沒有采用傳統(tǒng)竹雕短小的形式,而是以長片弧面竹塊為載體,縱向延伸創(chuàng)作空間,有個別作品的高度竟然達(dá)到1.5米。在雕刻時,他又以透雕技法為主,雕刻出大面積的鏤空部分,以空襯實,虛實結(jié)合,從而達(dá)到以小見大、以簡見繁的藝術(shù)效果。
在創(chuàng)作《身閑心定》時,陳銘堂先將一根長近1米的竹子,上下各留近10厘米,把中間部分切掉半面,從而巧妙地營造出長方形的深幽背景。然后,再在下方雕一只貓蜷臥在一把高背方凳上閑睡,凳背上端還有一只老鼠,正在警惕地觀察著貓的動靜。
一凳、一貓、一鼠,構(gòu)成了看似緊張卻又和諧的關(guān)系,塊狀的深色背景與椅子線條之間的對比,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一般竹雕給人留下的印象。通常,傳統(tǒng)竹雕不上色,著重欣賞竹材本來的色澤,然而陳銘堂卻開創(chuàng)性地給竹雕作品上色,通過顏色來體現(xiàn)遠(yuǎn)近層次,讓作品更活潑,更有動感。

近年來,陳銘堂還將竹雕和其他材料結(jié)合,雕刻出完全獨立的竹雕部件,然后以深色木板為背景,重新構(gòu)圖后再粘貼在木板上。竹雕的質(zhì)感與木材紋理相互映襯,營造出中國傳統(tǒng)水墨畫般的意境。
雕竹亦雕心
和陳銘堂聊天,可以明顯感到他是一個“慢性子”,說話一字一句,語氣舒緩平靜,猶如他的創(chuàng)作步調(diào)。“我不喜歡用機(jī)器,機(jī)器很快,可是少了一種感覺。”他一邊說,一邊起身,走到作品《荷葉連屏》前,“像這些荷葉,如果不是一刀一刀削出層次與肌理,而是用機(jī)器快速打磨而成,就少了一些力量,整體感覺也會差很多。”
因年少時曾參與廟宇修建,陳銘堂很早就接觸到了佛教,如今他早已一心向佛,連創(chuàng)作時也不忘聽《大悲咒》。他說:“我這一生就像創(chuàng)作竹雕一樣,用時光的雕刻刀,將生命中的種種世俗羈絆一點一點削去。減去貪欲,便得淡泊;減去固執(zhí),便得開闊;減去匠氣雕琢,即見真我。”如今,他更將自己對“減法人生”的體悟融入到竹雕創(chuàng)作中,追求作品的線條化、極簡化,讓作品在空靈淡泊之外,更多了一分“放下身心見乾坤”的禪機(jī)。如他創(chuàng)作的《煙云出沒有無間》,便是將長竹片橫放,上立一人,兩端逐漸削平、削尖,體現(xiàn)出天地的遼闊和人的渺小。
“創(chuàng)作是一種使命,不僅要將過去的觀念與技法傳承下來,還要表現(xiàn)新的思想。”陳銘堂說。不過,由于創(chuàng)新的作品往往超越了市場的期待,顧客一時難以接受,讓陳銘堂因此無法獲得穩(wěn)定的經(jīng)濟(jì)來源。當(dāng)問他這一路走來苦不苦時,他微笑著搖搖頭,然后拿起一只笑得憨憨的青蛙,說:“這叫《樂壞了》,就是我雕刻人生的真實寫照。”
(馮敬哲摘自《中華手工》)
- 讀者(鄉(xiāng)土人文版)的其它文章
- 潮汕家鄉(xiāng)味:咸菜
- 重慶人的小面
- 顧頡剛的『弟子規(guī)』
- 百家姓之姚姓
- 武大郎其實不矮
- 結(jié)草銜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