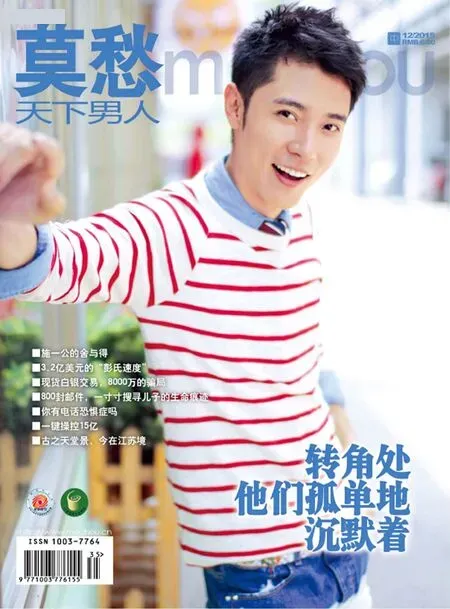張曉晶為國家記賬
□陳全忠
張曉晶為國家記賬
□陳全忠
老百姓過日子,要有一本家庭賬簿;一個國家要發展,更要精打細算,同樣需要宏觀的賬本,張曉晶就是那個給國家記賬的人。從2011年起,張曉晶就擔任中國社科院國家資產負債表課題小組副組長,并于2015年8月再次發布《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文藝青年的抉擇
中學時代,張曉晶和很多文藝青年一樣,喜歡讀《紅樓夢》《聊齋志異》等文學類書籍,那時候在研究所上班的哥哥建議他多看看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經濟類書,畢竟國家百廢待興,經濟改革的路剛剛開啟,需要更多經濟學人才。在哥哥的指點下,張曉晶試著去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沒想到還真看出興趣來了。
高考的時候,他果斷放棄了中文系,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專業,并被錄取。在大學期間,他又把《資本論》翻出來精讀了四五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獲,就像嚼甘蔗一樣,越嚼越甜。
自此,他對經濟學的興趣一發不可收拾。本科畢業后,他又師從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陶文達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攻讀碩士學位。碩士畢業后,他感覺自己的學術功底還不夠深厚,又繼續報考博士。這一次,他選擇了投奔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知名經濟學家樊綱教授。
當年張曉晶去中國社科院報考時,社科院的工作人員就給他打預防針:“能考第一嗎?若沒把握就別報了。”這時,張曉晶才了解到,樊綱教授第一次招生,近二十人報考,而那一年樊綱教授規定的招生名額只有一個!對于自己心儀的老師,張曉晶咬定青山不放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考試之前,他閱讀了當時出版的幾乎所有樊綱教授的論著,并深深地為之折服。因為準備充分,考試結果出來的時候,他的成績排名第一。
張曉晶的選擇沒有錯,跟隨恩師樊綱讀博期間,是他學術成長最快的階段。樊綱教授的治學方法、育人精神都深深地影響著他。博士期間,許多同學都急著發表文章、參加會議,樊綱在入學第一課就告訴他,先要打好基礎,要有廣闊的理論知識背景,要讀經濟學大家的原著、抓基礎,要和偉人對話,而不是和俗人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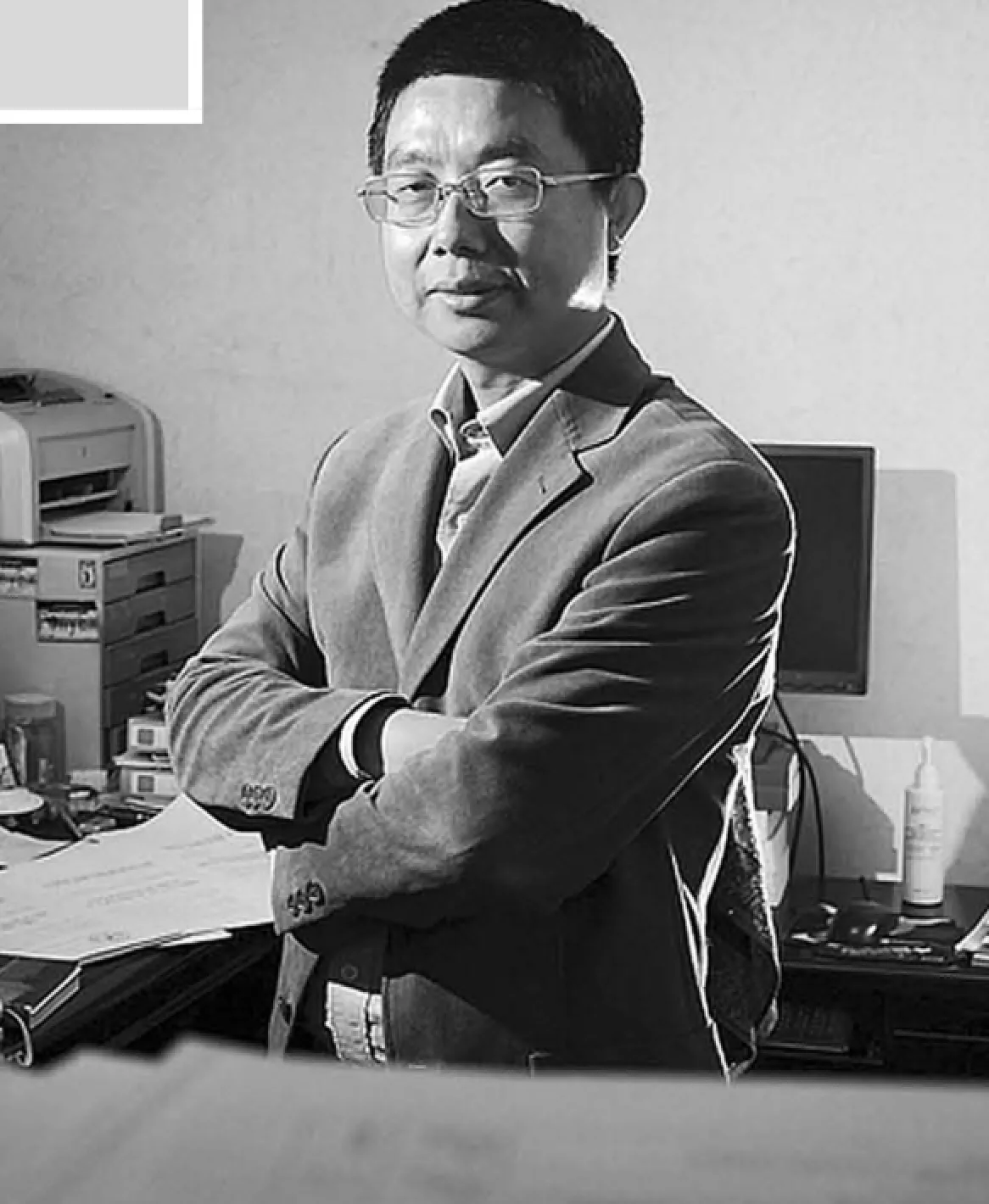
張曉晶
樊教授治學嚴謹,注重基礎和方法論。分析問題時,他強調拿到問題后,先要看這個問題能放到理論框架中的哪一格里,然后才有的放矢。討論問題時,他則是單刀直入、直奔主題,絕不拖泥帶水;如果學生還游離在一些枝節問題上,樊教授會馬上把他拉回來。尤為人稱道的是,在樊綱的主持下,當年社科院開辦了福特基金班,邀請諸多“海歸”、名師用英文授課、英文考試,真正實現與國際接軌。
正是因為在博士階段打下了深厚的學術基礎,畢業后,31歲的張曉晶即被聘為副教授,進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資本理論研究室工作。2005年,他晉升為研究員,并調任宏觀經濟學研究室主任。那一年,他才36歲。
宏觀經濟學研究室被譽為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八個研究室中的“品牌室”,劉國光、董輔礽、張曙光等著名經濟學家都曾主持過該室工作。樊綱教授曾以贊賞的口吻介紹張曉晶:“這是我的學生,社科院經濟所宏觀室主任!宏觀室厲害啊,我都沒做過宏觀室主任呢!”
為國家記賬
在美國訪問期間,華爾街爆發次貸危機,接著演變成國際金融危機。在美國,危機最初出現在房地產、銀行等私人機構,但政府不能坐視不管,于是私人機構的危機還得政府埋單,最后演變成主權債務危機。一時間,國家債務問題凸顯出來。這個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開始使用國家資產負債表分析方法來研究債務危機。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英美等國就在國民收入方面進行了國家的資產與負債的統計。現在,美、英、德、日等國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工作已成體系,并且會定期發布。
這讓研究經濟學的張曉晶更加重視國家資產負債表的重要性。國家積累了多少財富?借了多少債?一旦發生危機,有沒有能力處理?都能在資產負債表中找到答案。在張曉晶的倡議下,2011年,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成立國家資產負債表課題小組,張曉晶擔任副組長,并于2013年發布了首份《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在國家記賬上,中國終于開始起步。
這是一份精心梳理的數據。“每家企業都有資產負債表,一欄記資產,一欄記負債,自己有多少錢,借了多少錢,賬目一清二楚。我們也制了這么一張表,記錄了整個國家的財富與債務。”在部門分類方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參照全球通用標準,分五大部門——政府部門、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機構部門與對外部門,除了各科目的資產與負債統計,資產負債結構分析也會在報告中體現。張曉晶說:“做這張表,我們就像賬房里的記賬先生。眼皮子底下的東西是不是都要錄入,該放入哪個科目,都要考量。”
2015年8月,課題組的第二部成果《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出爐,重點分析了2012年~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的軌跡,旨在深入揭示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與控風險過程中面臨的挑戰,特別關注杠桿率調整與相應的金融風險管理問題,并對如何化解資產負債表風險提出了政策建議,這份報告再度引起社會和國家經濟部門的高度關注。
“過去我們談國家治理和國家能力,討論的多是稅收能力,是流量概念。而資產負債表中的數據更強調存量,反映國家積累財富與償還債務的能力。”張曉晶說,這張表不僅為應對危機提供參考,日常國家治理也得有一本賬,哪些數據反映了什么問題,我們該如何調整,才能避免問題擴大化。
生活在塵世
作為經濟學界崛起的新銳,張曉晶先后出版《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分析》等著作,在國內外權威報刊上發表論文多篇,并榮獲多個獎項,包括兩次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中國圖書獎。
近幾年來,張曉晶帶領他的研究團隊,先后完成了國家發改委、國務院辦公廳等交辦的重要課題及應急報告,此外,他還獨立主持了中國社會科學院A類重大課題《開放經濟新階段的宏觀穩定研究》,并被聘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的首席專家。
有了這些豐碩的成果,張曉晶并沒有因此高高在上,只研究不食人間煙火的項目,或者變現利益,四處走穴。目前最牽動他心的,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就業問題,農民工與大學生就業是當前面臨的最主要的挑戰。張曉晶的建議是,在經濟下行的危機階段,企業、個人應與政府“共克時艱”。政府可以采取彈性就業、準就業機制、國企承諾不裁員等措施,企業與個人也要承擔一些成本,核心是允許協商薪酬,容忍困難時期工資的下降,即保證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彈性,只有這樣才有助于盡快走出危機。
多年來從事經濟學研究,張曉晶自然能體會到經濟學人的尷尬:有時,經濟學家因入世太深而備受指責;有時,又因太出世,離老百姓太遠而受到質疑。他喜歡畫家吳冠中先生將作品比作風箏的說法,風箏能離地升空,但不能斷線,而“風箏不斷線”也正是張曉晶的經濟學立場。張曉晶認為,經濟學家并非生活在別處,而就生活在塵世里,生活在你我之間。
盡管科研、工作繁忙,張曉晶還是盡可能抽出時間,接受媒體的邀約與訪談,近幾年來,他越來越多地受到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國內主流媒體專訪,并為海外媒體所關注,多次接受紐約時報、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英國金融時報、日本朝日新聞等知名國際傳媒的訪問。
這也算是盡到自己從事經濟學研究的責任,讓宏觀預測作為一門尊重事實和數據的藝術傳達給大眾。有些學者的預測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純粹是為了吸引眼球;而有些預測不過是利益驅使,屁股決定腦袋。但張曉晶的訪談一直是出自學理與良心,他贊同樊綱教授的觀點:“學者就是要把真話講出來,把現實擺出來,讓公眾和政府做好思想準備。經濟學家應該講良心,說真話。”
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編輯陳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