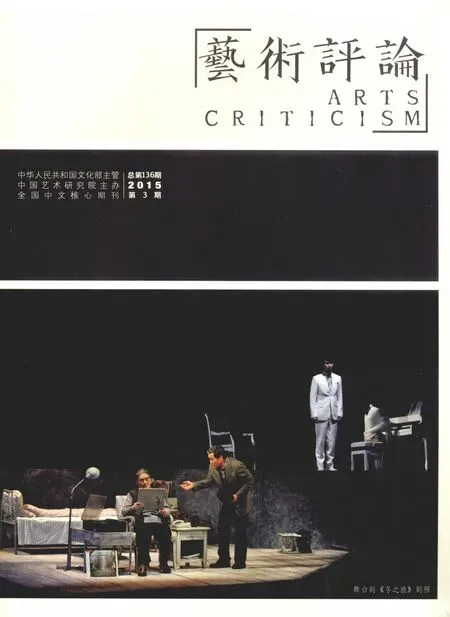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中國電影民俗景觀
尹曉麗
尹曉麗: 渤海大學藝術(shù)與傳媒學院博士、副教授
民俗是一種在人類生存過程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并與人類相始終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質(zhì)與精神、現(xiàn)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實用與審美于一體,散布于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很強的滲透性。自從電影產(chǎn)生之后,民俗便與電影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中國電影鮮明的民族風格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不同文化和地域的民俗形式和風情來呈現(xiàn)的。儒家的生命哲學和禮樂之論對于民間傳統(tǒng)儀式與習俗有著極大的滲透和影響,儒家文化密切相關(guān)的民俗如年節(jié)、婚俗、祭祖、喪葬等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中國電影文化形態(tài)的塑造,而且又常常和對儒家文化的負面價值批判結(jié)合在一起,構(gòu)成中國電影特有的民族審美空間。
中國電影中的民俗有些是對民間地域生活風情的展現(xiàn),如《駱駝祥子》中的北京天橋的平民生活圖景,《神鞭》中富于“津味”的皇會民俗,《雅馬哈魚檔》中20世紀80年代的廣州市民文化景觀;有的帶有強烈民間色彩的文化藝術(shù)形式,如《活著》和《桃花滿天紅》里的皮影戲,《炮打雙燈》中的民間炮竹文化,《霸王別姬》中老北京的京劇戲班,這些往往與影片的敘事情節(jié)和生活空間密切結(jié)合在一起,共同塑造被文化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事件所影響的人物命運,還有一些民俗是被作為片中極有象征意味的儀式典禮來加以強化的。這些并非社會民俗學意義上的民族志電影的故事片,往往通過對民俗儀式進行藝術(shù)化改寫,突出其文化象征性。這里往往包含對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與批判。
以儒家占主導地位的祖先崇拜有自己的文化內(nèi)涵和社會功能,它減弱了對祖先靈魂崇拜的神秘性質(zhì),而逐漸成為一種加強了現(xiàn)實功利性的禮治策略。祭祖敬祖一方面是祈求能得到先人的庇佑,另一方面也借此宣揚忠孝之道。但是在男尊女卑、提倡女性守節(jié)的封建文化的浸染下,對祖先的祭祀也有了許多嚴苛的要求,女性往往被排斥在這種隆重的家庭文化活動之外,尤其是守寡的女性。在影片《祝福》中,魯四老爺舊歷新年拜祭祖先的民俗刻畫就是與祥林嫂的人生悲劇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電影《祝福》將魯迅小說中描寫祭祖情節(jié)較為儉省的筆墨,擴充為三段對比效果構(gòu)成的祭祖獻福的場景,通過對大量造型各異、極富民族特色的祭器、福禮的反復表現(xiàn),揭示出宗法倫理文化對女性的摧殘力量,揭示這種緬懷悼念祖先的儀式,已經(jīng)淪為傳承根深蒂固封建文化負面因子的蠻性行為。祖宗是我們民族靈魂不死的神話,在影片中,這種神話不僅具有文化構(gòu)成的風俗意義,而且升格為中國文化形態(tài)的象征。電影把小說中魯四老爺“拜祖宗、祭天地的時候,這些事情都不能讓她做,否則不干不凈,祖宗是不吃的”這句話延宕成影片備受贊譽的高潮段落。小說中祥林嫂始終沒有和魯四老爺發(fā)生正面沖突,也沒有為自己捐過門檻進行解釋,祥林嫂是在一點一點的精神壓抑中,頹鈍了半年后被趕走的。而電影中卻強烈突出了祥林嫂對于能擺祭品的熱切期待和魯四老爺一家對于祥林嫂接觸福禮的忌諱和憤怒。當捐過門檻的祥林嫂欣喜地端著福魚走向祭桌時,四嬸馬上厲聲呵斥了她。祥林嫂則不斷申訴:我捐過了,我捐過門檻了。魯四老爺則面露怒色:住嘴,什么門檻不門檻的,……你捐一百吊也沒有用,你的罪孽一輩子都洗不清!正是這句話讓始終不放下福禮的祥林嫂徹底絕望,失神落魄地將福禮跌落在地,而愈加惱怒的魯四老爺則咆哮著:叫她走!馬上讓她滾!劍拔弩張的對峙為電影中祥林嫂砍門檻鋪墊了敘事邏輯和節(jié)奏氣氛,說明了祥林嫂經(jīng)濟和精神雙重毀滅的現(xiàn)實來源。小說中的魯四老爺基本上是個偽善的道學先生,而電影在刻畫他的封建宗法意識之外更突出了他的冷酷和兇暴,電影主題有階級性內(nèi)涵的強化。
“祖宗”這一民俗影像中最具文化傳統(tǒng)隱喻意味的意象在電影《祝福》中的功能是多面的。影片不僅強化了祭祖的線索性功能,而且把祭拜祖先這一深蘊儒家倫理精神的中國家庭禮俗作為封建文化負面影響的重要象征,那原本寄寓著后人對祖先悼念之情的儀式變成了殺人無形的文化利器,把祥林嫂的個人悲劇的刻畫上升到對整個封建文化進行批判的高度。而在張藝謀導演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皇帝脅迫皇后參加的重陽祭祖大典也帶有明顯的象征意味,皇帝以此警戒皇后對家法宮規(guī)等級秩序的恪守,一排排的祖宗靈位暗示了這種壓抑性男權(quán)秩序的歷史傳承,以此表達導演對權(quán)力秩序的批判意愿,可惜的是,這一用意被過于形式化的影像造型所沖淡,其文化反思的力度沒有達到50年前影片《祝福》的藝術(shù)效應。
古代社會中,沒有舉行婚禮儀式的婚姻不能被認為是合法婚姻。“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后世百姓多遵納采、納征和親迎三禮,其中迎親儀式最為隆重。婚慶典禮的民俗演繹也是中國電影中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民族性符號建構(gòu)。在吳天明的《人生》和陳凱歌的《黃土地》中,有關(guān)婚慶民俗場景的渲染都飽含著創(chuàng)作者對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尤其是《黃土地》,影片開篇就把上世紀30年代末期黃土高原的一次民間婚禮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象征著一種千古不變的,近似宗教儀式的東西。沒有真正的幸福和歡樂,一切都不過約定俗成而已。”[1]我們在影片中看到即便在極為貧困的黃土高坡,迎親和婚典的形式感依舊。站禮先生的高誦吉諺、新人跪拜天地、“自古婚嫁由天定,而今貴福在命中”的門聯(lián)、堆在床上的聘禮,都延續(xù)著古老婚俗的文化氣息。傳統(tǒng)婚姻家庭本位的價值觀、舊俗中早婚的傳統(tǒng)、父母之命的婚姻締結(jié)方式等等因素決定了舊時代包辦婚姻對于貧民而言是一定程度的買賣關(guān)系。
與《黃土地》相呼應的是《人生》在影片的尾段展示了一場陜北舊式的婚典,其熱鬧富庶程度已遠非50年前的黃土地百姓所能比擬,但是女性在婚姻中的悲劇感依然濃重。導演在此用傳統(tǒng)婚禮形式象征舊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態(tài),突出了巧珍最終絕望地被古老鄉(xiāng)村文化所覆蓋的人生悲劇。與《黃土地》不同的是,巧珍對婚姻的選擇畢竟帶有一定的自主性,她不是為了錢財而嫁人,這種對土地的依戀和桎梏于土地的矛盾心態(tài)更突出了婚姻儀式所涵納的文化反思價值。此外臺灣導演李安的作品《喜宴》也借助中國傳統(tǒng)婚宴民俗不無夸張的演繹方式,強調(diào)了中國文化中婚姻締結(jié)中的家長意識和群體觀念,顯示了個人意志和愿望在中國式婚姻中的弱勢地位,以此與西方文化作一參照,展示東西兩種文化的沖突和最終的妥協(xié)。
喪葬文化也是與儒家倫理文化息息相關(guān)的一種民俗形態(tài)。宋人李覯說:“死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于是為之衣衾棺槨,衰麻哭踴,以奉此喪。”[2]儒家歷來主張厚葬隆喪之禮,主張事死如事生,在舉喪、居喪、喪服等禮節(jié)上一絲不茍。同時通過這種儀式,也達到增強家族、親屬系統(tǒng)內(nèi)的凝聚力及團結(jié)鄰里關(guān)系的社會整合目的,最終傳達儒家以孝為先、慎終追遠的倫理精神。在張藝謀導演的影片《菊豆》中,喪葬儀式不再具有血緣關(guān)系的凝聚力量,而是通過對喪葬中的攔棺、哭棺民俗的詳細刻畫,突出了傳統(tǒng)家族倫理的巨大鉗制力量。葬禮“不僅僅是一次和死者告別的儀式,而且是給生者以暗示和教育的一堂課,它還要承擔清理和規(guī)范社會倫理和秩序的責任。”[3]
阻礙菊豆和楊天青幸福的“禍根”楊金山雖然死了,可是他所代表的家族宗法文化的強大威懾力還在,高高坐在棺頭的一臉威嚴的孩童楊天白成為父親的代理人,菊豆和楊天青所追求的超越世俗倫理的生活依然無法實現(xiàn)。長長的送葬隊伍、漫天的紙錢和兩人不無表演性質(zhì)的撕心裂肺的哭嚎極為儀式化地傳遞出張藝謀的父權(quán)文化批判立場。這種擋棺儀式和哭喪禮儀也是儒家文化中重視“禮”的一種體現(xiàn),“衣衾棺槨、衰麻哭踴”等古式的喪葬儀禮演示過程在一次次的反復中,將事關(guān)生死的觀念、信仰反復灌輸。這種灌輸不是靠外在力量的強行注入,而是逐漸地教化養(yǎng)成,從而使人內(nèi)在地主動服陷于傳統(tǒng)。葬禮上的擋棺儀式體現(xiàn)了死者雖死猶生的威嚴,家族長老們對楊家染坊的日后生活安排(讓天青搬出院子去住),都體現(xiàn)了宗法制度下祖先的越超性法權(quán)。
張藝謀最善于捕捉傳統(tǒng)民俗的典型儀式來構(gòu)造電影的視覺沖擊力,通過渲染民俗儀式中最具民族性的造型、色彩功能,傳遞出東方形式美感和文化陋習雜糅的影像奇觀。他還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臆造出點燈、吹燈、封燈的大院規(guī)則,模仿皇帝后宮的妃子“聽召”儀式,突出了男權(quán)社會文化下被擠壓和操縱的女性命運,揭示出女性靈魂異化的文化根源。盡管這種“偽民俗”遭到很多人的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張藝謀所建構(gòu)的民俗意象并未偏離對傳統(tǒng)文化負面影響批判的軌道,只是比較而言,《人生》和《黃土地》對這種陋習弊端的展示和批判更為決絕。正如吳天明《老井》中對鄉(xiāng)村宗族之間械斗習俗的刻畫,對保守、狹隘、蠻性的宗族文化的展現(xiàn),其本身就蘊含著編導的批判立場。
此外,中國電影中蘊含儒家文化意識的民俗還通過年節(jié)時令、民居構(gòu)造等更為普泛化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例如黃建中的《過年》、吳貽弓的《闕里人家》、張元的《過年回家》,一個在舊歷新年中展現(xiàn)子孫滿堂大家庭的紛爭,一個借助元宵佳節(jié)刻畫三代人的恩怨糾葛,另一個則在犯人過年歸家的敘事中刻畫家庭倫理的缺失與重建。在民族文化特有的團圓年節(jié)中,在有限的時空內(nèi),悲悼和反思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長和弊端,無論從敘事結(jié)構(gòu)上還是主題營造上都富有濃郁的東方神韻。在第五代導演作品中,傳統(tǒng)宗族祠堂的大量利用將魯迅有關(guān)鐵屋子的中國隱喻進行了電影藝術(shù)的外化,例如《大紅燈籠高高掛》取景于山西喬家大院,《菊豆》取景于安徽黯縣南屏大姓葉氏宗祠“序秩堂”。祠堂高大,威嚴,肅穆,是封建禮教的象征,人處其間必產(chǎn)生敬畏之情。《大紅燈籠高高掛》在喬家大院的拍攝,構(gòu)圖極度的規(guī)矩,顯示了傳統(tǒng)和陳規(guī)的堡壘式強大可怕的力量。舊宅院中那極度規(guī)矩的構(gòu)圖與故宮的建筑有完全相同的意味,都顯現(xiàn)出一種異常穩(wěn)定、簡單延續(xù)的秩序和這種秩序的強大力量。[4]事實上,中國電影中的皇宮景觀也有這樣的象征意味,《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的宮殿都是肅穆封閉的牢籠式的生存空間,里面人物之間的無望掙扎和權(quán)力爭奪都因此帶有明顯審視中國文化的主題意蘊。
中國電影中的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儒釋道文化及其民間演變盡納其中。不過,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民俗風情展覽,大部分民俗景觀都被賦予了民族文化反思的象征意味,而這也往往與民俗本身所積淀的文化因子有關(guān),尤其是第五代導演曾用儀式感極強的民俗景觀創(chuàng)造了“民族寓言”式的影像風格。自強調(diào)寫實主義的第六代導演崛起后,作為群體性的電影結(jié)構(gòu)元素,渲染民俗蘊含的文化意識的藝術(shù)手段在中國電影中逐漸有所失落。
注釋:
[1]陳凱歌.懷著深摯的赤子之愛──陳凱歌談《黃土地》導演體會.話說《黃土地》[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277.
[2]轉(zhuǎn)引自徐吉軍.中國喪葬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420.
[3]葛兆光.古代中國文化講義[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4]參見熊燕.中國傳統(tǒng)民居在電影中的情感演繹[J].山西建筑,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