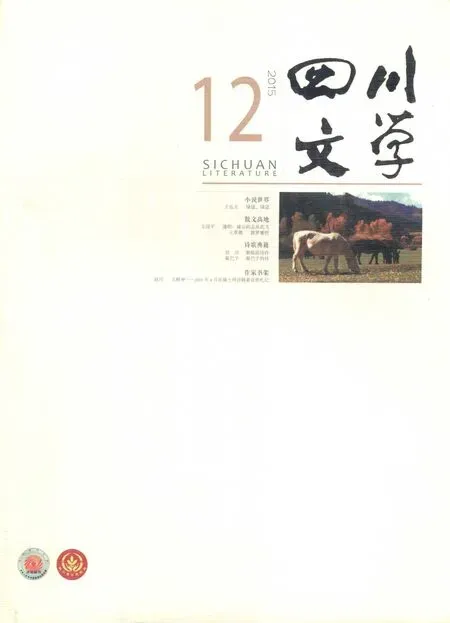波羅蜜經
○ 王章德
一
初時,我對開箱檢蜂充滿恐懼。那些行走空中的朋友,天生著鋒利,萬一給你打上一針,足夠痛半天的。后來接觸多了,發現它們其實很溫順,有的甚至可以停駐在你手臂上,允許你用指頭輕輕碰觸。于是越來越迷上那里面的風光。
青草小園,陽光盛開。即便你能數清眼前的一地芳草、滿庭陽光,卻未必數得清那滿箱蜂兒。那是一座盛世羅馬,十萬人家,鋪陳云集。那縝密浩蕩的蜂巢,則恍若左賦鴻篇,令洛陽紙貴。
一個龐大的家族蔚成帝國。這里公民分三類:蜂王、雄蜂,工蜂則占絕大多數。生產者占絕對優勢比例,更符合社會組織法則。
采集和釀造是它們生產的兩部曲。
采集的范圍很廣,平常半徑兩三公里。巍巍雄峰,茫茫廣野,沒有它們到不去的風景。那是春天的星座,它們閃爍在爛漫叢中,擔任著姹紫嫣紅的愛情信使,在收獲甜美的同時,成就了花兒的姻緣。不知是鮮花為它們而設,還是它們為花果而生。
當偵察員發現某一處盛宴時,采樣趕回。把樣品交給同伴后,用舞蹈把新大陸報告給身邊。舞蹈有圓舞、8字形舞和鐮刀舞幾種,總的說來是一邊爬一邊擺動尾腹。表達的內容一是蜜源的遠近,二是蜜源和蜂巢、太陽間的位置關系。而得知消息的蜜蜂再以同樣的方式說給周圍。那時的蜂箱內,自然是舉國歡舞。
這表達方式在人類也曾有過,只是后來因唇舌地崛起而退居其次。其實肢體的訴說在某種意義上未必亞于聲音的描繪。而“扭屁股”也并非一定關乎性感。
采集者們接著開赴過去,它們把花蜜盛進蜜囊。在盛的過程中,并加進自己的口水——那是多種寶貴的生物酶。回到家后,采集蜂嘴對嘴地把花蜜吐給負責釀造的內勤蜂。內勤蜂又把它吞進蜜囊,再次加進更多酶元。內勤蜂再把它吐出,涂抹到蜂巢里,并使勁揮翅鼓風。空氣流動,水分蒸騰,蜂箱內風起云涌。幾天后,蜂蜜成熟,再搬運到專門貯蜜的“房間”里,封蓋貯存。
整個過程好像沒有廠長、工程師、車間主任等。秩序井然的分工與協作,靠的是高度的自覺和默契。
二
它們是一個母系社會,除蜂王更新期的先朝遺民和極少數外來雄蜂外,蜂國臣民,無一例外是現任蜂王的子女。“子民”一語,人類的修辭,在這里獲得完整的真實性。
長時間端詳蜂王,意象中會躍出那些雙手過膝、兩耳垂肩的風云詞語來。
女王風采,氣象萬千。她個頭約是工蜂的兩三倍以上,不同尋常的腹部,舒暢、飽滿、優雅。六足赤金,有別于工蜂們的棕褐。這是她生前就已奠定的莊嚴。誰說麻衣相術沒有道理呢?
蜂王的一生似乎養尊處優。從蜂群要她成為王的那一刻起,她就住在寬闊的王臺里。那是比工蜂巢大數倍的深宮。設計也和普通蜂巢不同,普通蜂巢水平朝向,王臺則垂直向下,外觀有點像母牛的乳頭,——一個具有生殖繁榮意味的造型。還是幼蟲的蜂王住在這乳房里,頭朝下,尾向上,為的是有更寬裕的空間來發展其生殖系統。乳房里洋溢的“乳汁”,是一只只工蜂給注滿的蜂王漿。
靠了這神奇的精華,居住王臺的幼蟲,卵巢得以充分發育。這是她日后成為王者的必須——就像宙斯手里掌著雷電,就像元首們生就非凡的大腦一樣。
大腦,卵巢。二者都似乎不僅高低有別,更雅俗有分。生殖屬于下身的事情,因此凡涉及這方面的語詞,總不免下流之嫌。但不得不承認,二者實在異曲同工。前者運作著個體生存,后者肩負起種群延續。并且,它們都富于褶皺。而褶皺,在許多語境里,約等于高級:曲折多與復雜并提,而“平凡”、“平淡”、“平庸”、“平鋪直敘”等帶有“平”的說道,總包含著低級的潛臺詞。
不過女王的前身和普通工蜂確實沒有兩樣,它們都是前蜂王產下的受精卵。以致在一個蜂群中,蜂王意外時,工蜂們可以臨時把原來的工蜂巢改建成王臺,通過喂養蜂王漿,再立新王。
不同的養育,決定著一個生命的前程。
整個蜂群,除雄蜂外,只蜂王才享有婚配。出世十來天后,她正式出巢求偶,這就是有名的“婚飛”,這是蜂王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遠足,航程可達十數公里。君王遠行,險象環生。如果遇上游蕩的黃蜂、翱翔的燕子等,極可能王星殞歿。但要成為一族之王,她必須完成這次歷險。
婚后兩三天,蜂王開始產卵。她一生可產幾百萬只卵,這就是說,她一生擁有數百萬子女,那是其他任何母親都望塵莫及的。女人生產要一兩天,母雞下蛋也要半小時左右吧。而產卵高峰期的蜂王大約每分鐘就分娩兩三次。她一晝夜的產卵,相當于自身體重。輝煌的背后是艱辛,蜂國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蜂王的能量。
三
和工蜂、蜂王不同,雄蜂們由未受精卵發育而成——蜂之初,僅性別是先天的。
雄蜂紈绔公子一般。它們沒有采集能力,食量卻是工蜂的兩三倍。奇怪的是工蜂們一般情況下對它們寬容且愛撫。在蜂的“國際慣例”中,工蜂、蜂王如果誤入他國,招來的將是殺身之禍,唯雄蜂可以自由出入別的城邦。據說蜜蜂們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洞悉了近親婚配的貽害,所以歡迎外族兒郎入贅。蜜蜂至今已有六七千萬年歷史,那它們對近親婚姻的回避,是遠早于人類了。也就是說,當我們的歐也妮·葛朗臺正眷戀著堂弟的時候,當那些林黛玉和賈寶玉們還在生死難舍的時候,小不點的蜂兒們早已在規避近親生育了。
不過雄蜂的自由出入,也給蜂國帶來隱患:它們王國至今尚無體檢制度。這些自由入境者,弄不好會攜帶傳染疾病。
一弊一利,自然之道。
上天只給雄蜂一次和蜂王交配的機會,而且這機會還不是每一只雄蜂都有。也就是說,雄蜂們的全部生命意義,就是爭當一次新郎。
蜂王一生只行一次充分的婚配。所謂充分,它要獲得足夠的精子。為此它要和多只雄蜂交尾。是雄蜂們實現“人生”價值的時刻了,但只有那些體格足夠強壯,身手足夠矯健的兒郎,才能把握著這佳期。它們要在飛行中生殖器和蜂王準確對接。這種高難度的技術,恐怕是我們那些喜歡技巧的同類永遠也無法學會的了。而為了使兩個飛行器在太空中接吻,人類經歷了幾代人的殫精竭慮。
所以雄蜂們平日的大吃大喝,都是為了養精蓄銳,以盡可能保證在那畢生一瞬的時刻,有足夠的體能去完成此生的使命。但大喜之日,便是大限之時。交配時,雄蜂們把平生積蓄來的足量的精液輸給蜂王,隨后力竭而亡。
蜂王終生一次婚禮,雄蜂一場云雨之后化歸塵土。所以在蜂的王國,俄狄浦斯的故事絕對不會上演,張愛玲《心經》中的故事也絕對不會上演,整個蜂群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托馬斯·阿奎那用萬物的合目的性來論證上帝的存在。蜂群的法則,讓人仿佛窺見上帝的行蹤。為了整個種群,上帝精心安排,冷酷而決絕。
四
仲春的軟風鼓動起潛涌的荷爾蒙,大量的雄蜂在巢門口激動著。一只新蜂王要出世了。可原蜂王健在。蜂群是“天無二日”的一族,它們面臨分家了。
分蜂是蜜蜂們保證種群延續的重要手段。世事難料,風云不測。王謝金張,沒有哪一個家族能保證世代昌盛。在適當的時候把群體一分為二或為多,萬一哪群遭遇不測,其他群落還可發展。它們以此方式保證薪火不滅。
分蜂更具有禪讓意味,但遠比人類史上的禪讓令人敬佩。唐堯虞舜,也要等到鼻孔不再出氣了,才肯把江山臣民讓給他們認為合格的繼承人。蜜蜂更像古印度的修行者。那些修行者年青時努力當好家長,恪盡社會義務。老年后把家業事務交給繼承者,自己去云游修煉,思索宇宙的奧秘。大約正是因此,吠陀時期的印度人創造出燦爛的文化。
蜜蜂不書寫文化,只釀造物質。它們的禪讓不是去修行,而是去另辟疆土。當新王即將出世時,它們把蜂巢內大部分“人口”和所有的創業交給她,一拔隨老王遷出。
那是一種成編制的遷徙,蜂王、雄蜂、工蜂,混成一旅,蔚為壯觀。它們先是飛停在原蜂巢附近。如果養蜂人不及時召回,另行安置,它們開始長途流浪,尋找下一處棲身地。那是《詩經》中公劉式的大遷徙嗎?它們隊伍里也有荷馬嗎?它們又傳唱著怎樣的風、雅、頌呢?
整個分蜂過程,做主的并不是蜂王。什么時候修建王臺、培養新王,什么時候分出去,哪些追隨老王,哪些留下來輔佐新王,蜜蜂們像是通過大會來決定。
眼下它們巢外結團,巢里扎堆,嚶嚶嗡嗡,像是陳述紛紜,爭執不下。它們的會議里是否也有左派、右派,保皇黨、太子黨?
時值春光大好,花開熱鬧,可它們的生產卻陷于癱瘓。我決定幫其早點結束運動——為了收蜜。
揠苗助長——人類所能犯的錯誤類型其實不多,很多時候是在重復同一種錯誤。而我的一念之差,帶給它們的是萬劫不復之災。
那時王臺尚未成熟,我硬把它另分一箱,結果蜂群陷入更大的混亂。當我把飛離的一群召回原籍時,原箱內的蜜蜂們驟然翻臉。在來不及搶救的瞬間,蜂王被一大群工蜂圍攻致死。
那只蜂王,是我在召集時主動飛來住在我身上的。對我的輕信,成了它的惡夢。
和許多事物皆有兩面性一樣,分蜂對蜂群來說同樣是雙刃劍。
分蜂的弊端還在于,若分群太多,每一群的勢力就弱,抵抗災害的能力也隨之減弱。韓、趙、魏三家分晉,最終被強秦吞食。
蜜蜂的病害很多。歐洲幼蟲腐爛病,美洲幼蟲腐爛病、孢子蟲病、螨病……對于嬌小的它們,太多的病毒、細菌、原蟲、寄生蟲,十面埋伏一般,嚴重時造成全群覆沒。
如果蜂群鼎盛,它們大多能扛過病害。強大的群有頑強的群體免疫力,偶爾染病,一般都能自愈。常常是一個蜂場,弱者每況愈下,強者卻生機勃勃,往來間有漢唐士民的自信。是它們分散了病菌、病毒,稀釋了毒力嗎?
它們的敵害同樣不少。除了常來國門外侵掠的大小黃蜂、胡蜂外,蜻蜓、蜘蛛、燕子、麻雀、蟾蜍、青蛙、蛇等,都可以成為它們的奪命殺手。而這其中許多,通常是被人們看作益蟲益鳥的。
萬物生克,金木水火。害益本不能籠統而論。
一只大黃蜂在蜂巢門口盤旋,翅膀扇動空氣咝咝有聲。在蜜蜂的眼里,它該是兇神惡煞、厲鬼惡魔。它既搶吃糖更以蜜蜂為美食。若在野外,單只的蜜蜂就只能喪生“虎”口。但現在是在一大國城下,上百只工蜂齊集蜂箱前,敢死隊般嚴陣以待。它們站成一道“人肉長城”來保家衛國。悍敵接近時,它們同時振翅驅趕。聲勢所至,大黃蜂竟一時無法靠近。
對于敵害,強群更具優勢。
五
但它們的戰爭更多發生在同類之間。不知這是不是眾多生命的共同死穴。
最常見的是盜蜂之戰。當外界蜜源稀缺時,某些饑餓者會潛入他群偷吃。是天生劣性還是逼上梁山?這時被盜和行盜發生你死我活的搏斗。為了求生,結果毀滅生存,這應該是作戰雙方始料不及的。
更令人扼腕的是它們的誤判。
排它性是太多生物的本能。而本能,有時飽含智慧,畢竟那是歷經億萬年沉淀在無意識深處的。但正因為如此,它又非常的固執盲目,尤其在情況逸出經驗的時候。
在那場失敗的分蜂中,它們把蜂王毆死后,接下來是一場惡戰,蜂箱前橫死一片。它們視彼此為邪惡異己,展開了一場凡爾登肉搏。其實那是半小時前才分出去的同群同胞——本自同根生啊!
兩天后,蜂箱內一片死寂。開箱一看,尸橫遍野。是不是它們最終明白自己誤殺了女王,也就沒有了可以養育的幼蜂,上無宗主下無子嗣的它們,潘多拉的匣子轟然落蓋,最終瘋狂決死?
“戰爭是萬物之父”,赫拉克利特的這句話,或許有一定的道理,但最多只說對一半。另一半,戰爭也萬物的粉碎機——包括心理大廈。
它們同類間作戰一般用嘴咬。至于動用毒針,在它們是認為王國到了最緊急關頭了。
嘴上的鉗子和尾上毒針,仿佛它們的常規武器和核武器。核武器輕易不動用。那帶毒的針頭,是天授的佩劍,是與生命同在的唯一法寶。劍在“人”在,劍失“人”亡。一旦它扎入敵體,就無法拔出,最終連根脫落。說到底,跟雄蜂一樣,上帝也只給了它們一次使用尾器的機會。是上帝吝嗇嗎?畢竟,鎮山法寶、神功絕技,是不好隨便濫用的。
所以一旦它們長劍出鞘,那就是萬般無奈下實施的一種自殺式的狂飆襲擊了。
你敢在開箱前粗魯地敲打蜂箱?你敢在受到驚嚇時扔掉手中巢脾?那你是在逼使它們認定你是危及家園的大患。它們會讓你見識到真正的蜂擁而至、同歸于盡!
再就是在比較寒冷的時候開箱查看。那是在初學和它們打交道的時候了。這也是對它們的極端失禮和嚴重侵犯。那群戰機挾狂怒而來,蜂帽被撞擊如狂濤前顫栗的大堤。驚駭中我放棄查看,躲出老遠后脫下蜂帽。但兩只余怒未消的仍奔襲過來,給我后腦上惡狠狠的教訓。
對不起,都是我的錯。像挨了愛人憤怒的耳光,我在心里向勇士道歉,向蜂國道歉。
六
前年陽春三月,不請自來的它們入住我家壁櫥。附在隔板下,喁喁訴說。家人害怕,主張用噴霧器解決,我力阻下來。掌握了噴霧技術的人,不是想噴就噴的。把它們小心招集起來,安置在一個暫時的紙箱里,灑了點糖水。這很有點臨時安置移民的味道。它們頗隨遇而安。至于給它們換成正式蜂箱,是好長時間后的事了。
自此開始學養蜂。
一直以來,漢語對“蜂”字似乎好感無多,“一窩蜂”、“馬蜂窩”、“狂蜂浪蝶”、“蜂擁而出”等,似乎都不算好詞兒。
可漢語對“蜜”字絕對鐘情。
這本身是一個名詞,在許多語境中卻用作形容:很甜的橘叫“蜜橘”、汁多而甘的桃叫“水蜜桃”,“蜜月”讓人流連繾綣,“蜜色”讓人心軟意綿。而某一時期的古人死后,還要用蜂臘作印章殉葬,取名“蜜璽”。也不知是想把那悠長的舌上記憶帶往另一世界,還是想轉世作一只蜂王。
飲蜜養顏,很多人都這樣說。但鮮有人知,養蜂更是養性,不亞于參禪。
騷人們嘗到了蜜的美妙,大刀闊斧謳歌蜜蜂們的無私奉獻。這樣做的好處是:獲得者和付出者都顯得高尚。實則蜜蜂們釀造和貯存的初衷,主要是飼喂幼蟲、雄蜂等。至于蜂王,前面說了,它主食蜂王漿。工蜂們自已則非常節儉,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去動那些簽封貯存的甘美。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節儉的它們世代相傳共產主義。
斯賓塞在論及國家與社會形態時曾說,如果實行按需分配主義,人類將會成為一個螞蟻和蜜蜂的社會。這位高傲的哲學家,言詞頗含蔑視。其實蜜蜂的社會,何嘗不是人類的縮影?都是天地靈氣化成,都是大自然并非完美的作品。
蜜蜂一生改頭換面四次。那些附在蜂巢底部的細小白點是卵;那盤成C字形熟睡在巢里的是幼蟲;安靜躺在封蓋的巢床里,頭足初成的是蛹;最后破巢而出,能飛善采懂釀造的是成蟲。這在昆蟲學上稱之為完全變態。四次變身相當于三次出生。作為蟲卵的形式產出來是第一次,由卵孵出幼蟲是第二次,最后破繭而出,羽化成蟲是第三次。每一次出生,都是在生與死之間驚心動魄的突圍。
表面看,它們一生要經歷許多階段,似乎它們壽命很長,但一如蚯蚓的環節也很多,那身體卻實在不算長。
人們通常所說的蜜蜂多指工蜂,它們壽命的長短隨季節而異。晚秋和初冬出生的,可長達約半年。生于春夏兩季的,一般只活三四十天,最長不超兩個月。因為秋冬季節,它們較少采集,相對輕松。而春夏兩季,工作繁重,它們夙興夜寐,夜以繼日。壽命的長短,和勞作強度成反比。兩個不同季節出生的,都可以理解成生逢其時或生不逢時,那要看持什么標準了。
養生的反義是勞碌!
好在時間本來無所謂長短,測量時間的單位,不必是天,不必是月,也不必是年或世紀,最適用的是 “一生”。
工蜂一生清淡而奔波。
一般說來,它們只有從解剖學的角度才稱得上雌性。它們體內的幾條輸卵管僅剩殘痕。這是進化的結果嗎?進化的另一面是退化。它們沒有巫山之夢、云雨之求,正常情況下也不會生殖,清心寡欲如一群修行者。但它們并不是清修,而是把全部心情用于家園,準確地說是用在養育上,那是它們采集和釀造的最終旨歸。
工蜂和幼蟲關系復雜。就它們都是同一蜂王的子女而言,工蜂是長姊。蜂王對下一代,只會生,不會養。它們實行生、養分工制,哺育幼蟲的任務自始至終由那些成年工蜂承擔。我們人類有哪位長姊會全程負責養育弟妹呢?它們早期喂給幼蟲蜂王漿,如哺母乳。后期喂大幼蟲以蜜和花粉混合而成的蜂糧。它們更像奶娘,像幼蟲們出生伊始的養母。
可工蜂們更像男人,它們差不多具備了理想男人所有的優秀品格:勤勞、顧家,不辭奔波,不畏強敵。和想象中女人的溫軟相比,它們更具男子陽剛之氣。
或許,作為修行者,它們已經褪盡了性別特征而集兩性之長于一身。那可是菩薩境界了。菩薩沒有性別,可以是男,可以是女。觀音菩薩先前是男的,后來為滿足人們對慈愛的需求,易作女性。菩薩要棄絕聲色享樂,勇猛精進,饒益有情,利益眾生。工蜂們不正是這樣嗎?
或許,人類的性別期待并不適合于蜜蜂。畢竟人類的眼睛并不能讀懂它們的全部世界。宇宙萬有,并非都能用人的尺度去衡量。倒是反過來,萬物的尺度不妨偶爾借來對照人的短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