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游情結”淺談中國動畫的傳承與發(fā)展
□熊敏
從“西游情結”淺談中國動畫的傳承與發(fā)展
□熊敏
經典作為民族精神之源,始終滋潤著各個時期藝術家心中的藝術家園。在中國文學史上,明代小說家吳承恩在汲取歷史文獻、神怪小說、佛學典故中的元素后寫就的《西游記》,因其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動活潑,故事情節(jié)跌宕起伏,并富有時代意義,時至今日仍是最為大眾津津樂道的文學作品之一。而動畫作為當今文化傳播的一種新手段,以其震撼的視覺效果、精妙的后期剪輯和不斷進步的技術手段,更直觀地向人們展現(xiàn)了文學作品的特殊魅力,使得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同樣經典內容能在不同動畫作品中詮釋出不同的精神內涵。文學和動畫的結合,讓西游故事這一經典題材在新時代背景下,迸發(fā)出炫目的魅力。
一、角色形象的進階
1964年《大鬧天宮》中對孫悟空的造型(見圖1),采取了夸張、變形和擬人化的手法,借鑒了京劇臉譜形式并加以簡化,輔之以京戲的動作特征,使孫悟空這一形象具備了飽滿的視覺表現(xiàn)力。孫悟空臉部中央用代表忠義勇敢的紅色把眼睛、鼻子和嘴統(tǒng)一在一起,金色的眼影,綠色的眉毛,更襯托出其“火眼金睛”的光彩,另以簡練的線條概括嘴部,炯炯有神的雙眼極富表現(xiàn)力,傳達出角色的喜怒哀樂。頭上的軟皮帽顯示了猴子的頑皮與靈活,長腿細腰,短裝打扮顯示出猴子靈敏、機智、善武的個性特點。鵝黃色的上衣,虎皮紋樣的腰束短裙,大紅色的褲子配以長靴,以及脖子上醒目的翠綠色圍巾,高純度的黃、紅、綠、黑色對比鮮明,襯托出猴子“神采奕奕,勇猛矯健”。在用色方面注重固有色的搭配運用,突出色彩的裝飾意味,在深諳傳統(tǒng)的設色習慣和用色規(guī)律的基礎上,結合角色的性格、身份、形態(tài)進行色彩配置,最終塑造出個性鮮明的齊天大圣形象。

圖1 1964年《大鬧天宮》孫悟空形象
2012年《大鬧天宮3D》是在原作的基礎上進行膠片修復、色彩還原,保留了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風格,造型上延續(xù)了原片的京劇臉譜。圖2中,畫面風格和場景都與原著相差不大,但采用了3D技術之后,全新的視覺效果更加扣人心弦,打斗時的立體畫面也使影片更上一層樓。

圖2 2012年《大鬧天宮3D》孫悟空形象
2015年《大圣歸來》中的角色設計,則完全遵從了戲劇原則,人物不再單純迎合受眾審美習慣,轉而為劇情服務,例如孫悟空的形象設計(見圖3),一反常態(tài)地采用了長條形的“馬臉”,這點讓一些傳統(tǒng)至上的觀眾不滿,但觀眾觀影后的反應表明,“馬臉”孫大圣達到了一鳴驚人的效果,因為這個馬臉大圣擁有曾經的美猴王從來沒有呈現(xiàn)過的無奈、悲愴和抑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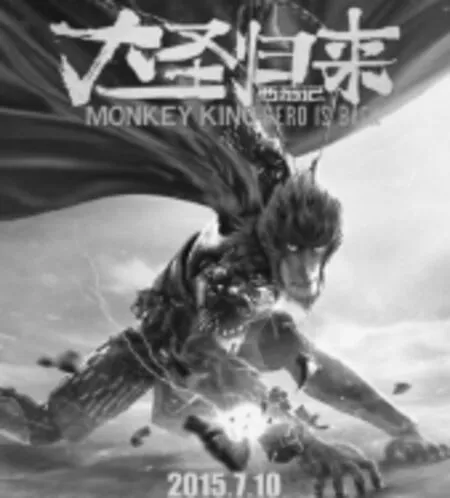
圖3 2015年《大圣歸來》孫悟空形象
二、制作技術的突破
1964年的《大鬧天宮》沒有任何的電腦制作,在籌備工作結束后就立即投入到“大生產”的繪制階段。當時約有二三十人參與原畫、動畫的制作,人員被分為五個組,每組由一個原畫、助理和若干動畫人員組成。原畫創(chuàng)作關鍵動作時,把主要情節(jié)按導演的要求繪制出來,動作從初始到結束的中間的過程要畫3到7張,由動畫人員協(xié)助完成。沒有電腦協(xié)助的情況下,全憑手中的一支畫筆。一般而言,10分鐘的動畫要畫7000到1萬張原動畫,可以想見一部《大鬧天宮》工程的浩繁。工作人員每天都在重復同樣的工作,41分鐘的上集和72分鐘的下集,僅繪制的時間就投入了近兩年。
2012年《大鬧天宮3D》是在原作的基礎上進行膠片修復、色彩還原、數(shù)字處理、3D特效制作。與1964年版相比,3D版的《大鬧天宮》故事情節(jié)基本沒有變動。除了更新為3D技術外,還將片長由原來的120分鐘縮短為80分鐘,更符合了現(xiàn)代觀眾的觀影需求。為了配合現(xiàn)代寬銀幕,更是重新繪制了部分畫面。這部上世紀60年代大受歡迎的經典動畫片變身為3D立體電影的嘗試取得了良好的反響,既保留了原有故事情節(jié)的流暢自如,又根據(jù)觀眾需求做了大膽的嘗試,在技術支持下,聯(lián)系起了兩代觀眾的西游情懷。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動畫鮮有深入人心的作品,而2015年橫空出世的《西游記之大圣歸來》在汲取西游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力量的基礎上,運用動畫電影領域的新技術,讓人眼前一亮,為之振奮。影片采用好萊塢式的公路片敘事手法,貫穿宏大的場景,搭建全景3D,既讓觀眾尋覓到北歐式魔幻森林的蹤跡,又可見天宮與魔堡的恢宏,而民風彪悍的長安城、大佛林立的五行山山洞、妖氣繚繞的懸空寺等場景,更加精致細膩,讓人產生身臨其境之感。此外,影片充分尊重了東方美學取法大自然的淡彩風韻,市井街頭皮影戲、煙雨籠罩下的屋角寒梅、桃樹孕出的誘人果實、石拱橋上的烏云壓頂、山前江畔的帆影船只,以及混沌的書生造型,都讓觀眾在細啜慢品下,既輕松自如地帶入對傳統(tǒng)文化的個性理解,又充分享受到動畫新技術帶來的視覺效果。
三、音樂元素的雜糅
在配樂方面,1964年版的《大鬧天宮》,運用大量的京韻配樂以配合人物形象,發(fā)展到《大鬧天宮3D》,雖仍以中國傳統(tǒng)戲曲作為基調,但也與時俱進地加入了大量西洋樂器伴奏,吸引了許多年輕觀眾的眼球。到了2015《大圣歸來》,配樂更是根據(jù)人物經歷和性格進行個性化創(chuàng)作:孫悟空經歷了從巔峰跌至谷底的巨變,昔日戰(zhàn)神失去神力,因此開場音樂中參考了西部片孤單牛仔出場時,又冷酷又神秘的創(chuàng)作風格;孫空悟雖冷漠狂躁卻仍難舍俠義情懷,又特意設計了一段男低音的吟唱,放大了他內心的孤獨和滄桑;直至遇見純真善良的江流兒,單簧管、雙簧管的配樂,讓童真更具感染力,也讓觀眾在這樣溫暖的培育中,逐漸感受出孫悟空的變化;還有其他配角,如“土地公公”出場用了高音的笛子,俏皮活潑;豬八戒因難忘前世天蓬元帥的瀟灑而介懷今生家畜的形象,采用了男低音即興詠嘆調,表達他的滑稽和無奈;在表現(xiàn)混沌時,在唱段中加入了日本“能劇”的元素,陰森而詭異;山妖出場時,使用了日本的“太鼓”讓人神經緊繃。配樂中融入的現(xiàn)代音樂藝術和流行音樂元素,都讓新一代觀眾更易融于劇情中。
1961年,那是一個國民經濟貧弱但國家努力想要開拓新局面時代,所以才有了昂揚奮起的孫悟空在《大鬧天宮》里的橫沖直撞和無所畏懼;2015年,這是一個物質豐富但人們精神逐漸迷失的時代,但《大圣歸來》帶來的不僅僅是經典的重現(xiàn),更是對中國動畫電影再次復蘇的信心,是中國動畫電影人在沉寂多年之后,逐漸走向成熟的標志。兩部動畫雖同根同流,卻在不同年代折射出不同含義。傳承經典的意義不言而喻,然而更重要的是傳承之后的發(fā)展,向經典致敬后,為發(fā)展的努力,為傳承的創(chuàng)新,才是時代賦予我輩的使命。
1.謝選駿.神話與民族精神[M].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
2.孫立軍,易欣欣,生喜.影視動畫經典作品剖析[M].海軍出版社,2004
3.陳瑛.動畫的視覺傳播[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作者單位:福建工程學院設計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