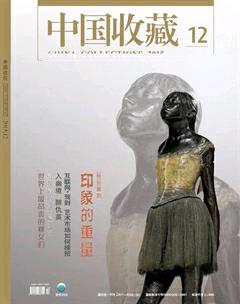書法是不是手工活兒
董水榮
書法是一種文化,因為書法的根連著中國的漢字,連通著屬于中國的情感與審美。它在中國文化史中同不少學科建立和保持了較為親密的聯系,甚至是連著中國的哲學與思想。
書法是一種藝術,在日常實用的書寫之外,有獨立自足的審美意趣,用以抄寫與實用無關的詩詞聯語,以供優雅的賞玩,起到愉悅身心的積極作用,深諳書法語言的書家還可以在書寫中表達情感。
書法是個手工活兒,因為書法被千篇一律地書寫,過度追求技術。同時,書法的價值觀被置換為謀取名利的手段,成為一種謀生的職業。書法再次從藝術的層面被剝離到手工制作的層面。
當代文化精英對當代書法的興趣越來越小,很大原因就在于這些當代的書法作品所提供的精神容量越來越少。書法創作走上了以形式與技術為中心的表達,所謂的“當代書壇高手”、“獲獎作者”等一個比一個缺少對文化、對人性的關注,很多書法作品沒有一個精神面孔。“寫手”只是不斷地通過對古典、經典作品的影子重復臨摹來獲得書寫的技術,很少將文化和審美的氣息輸入到自己的創作中,以此來獲得書法的文脈,很難與當代的文化精英進行更高遠的精神對話。書法本來是最富有文化象征的藝術,如今卻變成越來越沒有文化的一門技術。
“圖像時代”隨著“數碼時代”的到來,在科技社會簡約化、統一化的話語時代里,臨帖成為復制古人書寫技術的目的。甚至可以借用許多科學的方法,放大點畫形質的細節,剪切編輯章法的構圖,這已成為書法專業化的一種趨勢。書寫也愈來愈喪失了藝術的自然屬性,喪失了書法的精神生殖力,喪失了書寫中的審美屬性與盎然詩意。書法技術的功能性偏執,釀成了當代書法風格的類型化、相似化、跟風化。在書法追求過度技術化以后,以工具理性地書寫造成了當代書法家精神世界的萎縮,書法的衰變同時也導致審美情趣和藝術創造的敗落。 當代書法已經有了一種書寫簡約化、實證化、專業化、固定化的危險。
這些年來,書法正在失去對自我的一種表達、寫意能力。從技術到技術,使得書寫日益技巧化、精細化、共性化。消費文化的崛起,使書寫熱衷于時風的追逐、審美的平庸,書法家不但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種與書法品質無關的書寫,而且把它當作了書法的目的。那些帶有審美思索、心靈表達、風度體現的書法,已經很難引起書法家們的注意。書法正在從精神領域退場,正在喪失表情達意的自覺。從過去的“流行書風”到今天的“新帖學”,盡管面貌各異,但從精神的底子上看,對大多數的書法作者來講,它其實都是一種技術潮流書法,只是技術上的取法資源不同罷了,或者可以說就是一股“技術流”而已。
只有極少數書法家從這些潮流里脫穎而出,有了對書法真實的表達,并貢獻出當下書法所缺乏思考與表現。書寫出高貴而真實的靈魂,也關懷人類內心的希冀和夢想,這是對書法家的人文要求。現實如此喧囂,假若書法的書寫只是關注在拍賣場上價格的走向與平方尺的價位,書法就將與人的精神無關,這是一種悲哀。所以,比起那些書寫看起來精致、作品氣質卻萎靡不堪的作品來,這些年,我更愿意去閱讀所謂專業書法家以外的文人信札,或者一些傳統書法中的邊邊角角。它們至少告訴筆者,除了技術之外,還有鮮活的生命感。
也許我們真的不能把書法賦予太多的文化色彩,讓書寫回歸到一種技術常態。其實當書法越來越純粹地走向一門學科,有時就意味著脫離了日常書寫的狀態。如果書法脫離了書寫的常態,在筆者看來,它的走向與文化的走向恰恰相反。那么,書法創作將走向審美品位的狹窄、形式的變異、觀念性的表達。也許書法本身就是一種關于書寫的技術,所以朱以撒先生在他的《腕下消息》中說他更愿意把書法家稱為“個體手工勞動者”,此話是句謙虛的自嘲,同時又是對書寫的悠閑狀態的肯定。筆者覺得一語道破了職業書法家的天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