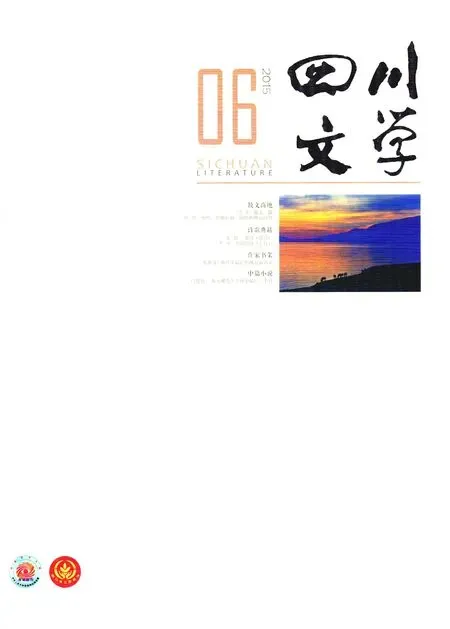視死如山
谷運龍
視死如山
谷運龍
谷運龍,男,羌族,1957年10月生,四川茂縣人。他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迄今已有百余萬字。小說《飄逝的花瓣》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近期作品則有《花開汶川》《天堂九寨》等四部。新近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說《燦若桃花》在京舉行了作品研討會,頗受好評。
幾天前,和父親坐在一塊,他又說起為他修山(墓)的事。
“前天,我又去找馬老婆子打了卦,連打幾卦卦象都不好。馬老婆子看著我,連話都不敢說。我就說,是咋個回事就原封原樣地說。她卻賣了一個關子說‘把你的生辰八字報來,我再推推’。我報了生辰八字,他用紅、白布條推算。我怕她日弄(欺騙)我,我就眼鼓鼓地死死看著她,就在紅、白布條交叉的地方,活生生地就是一副枋子(棺材)的樣子,前面還有一個端著靈牌的人。馬老婆子車過頭看著我,我心里很難過地說我都看見了。”
“后年(2015),估計是翻不過去了。”
我有幾分責怪地看著父親,但又不敢把話說重了,強顏為笑。“前不久才作了全面的體檢,所有指標都很正常。老年皮膚瘙癢和腿桿痛都不是致命的病,何必那么緊張,自己嚇自己。”
他依然帶著幾分恐怖地說:“男怕三、六、九,后年滿79。”
“不會的爸爸,爺爺、奶奶都活了83哩。”
“倒也是。”
說后,他就離我而去了,帶著幾分應付。一席話,勾起我很多聯想。
18年前,我們一家人往承包地里背糞水,這塊地是他所有承包地中最好的,因此,他特別厚愛。加之這塊地以前曾有一座廟宇,名龍園寺,香火旺盛,菩薩靈驗。休息的時候,他說“來,谷運龍,我給你說個要緊事。”
我莫名其妙地跟著他,走到廟基坪的拜臺下方,一籠金竹、兩棵香椿,還有廟子上以前用過的石水缸,水缸里有半缸青花亮色的水,他站定在竹和樹之間說:
“以后,我和你媽死了,就埋在這兒。”
“你還不到60歲,咋就安排這種事喲?”
他并沒有聽我的話,只顧向我介紹這里的好處。
“墳頭正對千佛山的山峰,山勢圓潤,這里以前又是菩薩顯靈的地方,要竹子有竹子,要樹有樹,啥都有了,什么都不需再添。”
還有一句話他沒說,我們所在的這座嶺又叫鳳凰嶺,尖嘴巖和無僧廟梁子恰是其兩翼,主體
從中垂拱而下,頭在四坪村的?坪組,整個身軀都在我們桃坪組(大集體時期,?坪窮桃坪富,便有吃?坪屙桃坪的說法),龍園寺恰好在鳳凰的尾端的肥坨坨上。自古建寺的地方都是極佳的地方,“天下名山僧占盡”呀,如今,父親居然也算計了這么好一個地方。
“要是運氣不好,地分不到這兒,鼻子想干還莫得天河水哩。”
我再次領略了父親的精明,于是我把弟妹們都叫過來,一五一十地又給他們作了交待。大家都不理喻地笑話父親,父親卻在笑聲中說:“你們以為老子只考慮老子的事嗦?”
汶川5·12特大地震以后,他的身體十分不好,開始是頸椎骨質增生使他的腿痛成為大疾,手術以后,半年都不自在,繼而又是滿身發癢,癢至極致,藥到病不除。一個小瘡動了三次手術,弄得他欲死不能、欲活難忍。大半輩子雄心不滅的他徹底地喪氣灰心了,就連重損的房屋都沒有心去恢復重建了,只是略加修補,湊合而居了。
這么一點點小病,就把一條可以隨處橫刀立馬的漢子活生生地給擊倒了。我笑話他時,他卻一臉的不愉快,你來試試看!
這種時候,我們誰還顧得了他和家呢!只有靠他和媽媽自力更生了,這期間他甚至想到過死,但死也得有個交待啊!
春節以后,他就給我們幾兄妹攤牌了。
“還是趕緊把山修了吧。”他說。
我們都毫無思想準備地啞然而對。
“我說還是趁早把山修了吧?”他又加重語氣說。
“太早了吧?”
“早個屁,快70的人了,這氣說不來就不來了。”他有些氣惱地盯著我。
“我們這里沒有這個習慣,外人還以為在咒你們哩。”我鼓起勇氣說。他就悶在那里不說話了。
“我看也是,不曉得的還說兒女們咒我們。”母親說。
他抬起頭狠狠地剜了母親一眼。母親便低下頭不言語了。
我接著說:“現在修山,修好了怕人說三道四,修孬了也怕人說我們不忠不孝,舍不得錢,還不如到時一口氣修完,想修成啥樣就修成啥樣。”
大家都說這樣好。
父親站起來,離我們而去:“老子不管了,你們想咋個整就咋個整!”
沒過多久,茂北(茂縣至北川)公路改造,將穿街而過的道路改道至村后的山邊,路恰好穿過家公家婆的墳地,父親就此將他倆的墳搬至龍園寺他所選墳址的旁邊。
又是春節回家,我們初三去上墳,祭拜過后,我問父親為啥搬這么高,不就近選址安埋,這太勞神難為他了。他卻說你們不愿意為我修山,我把他們搬到此,讓他們先把這個地方占住,怕被別人先死占了去。
一塊墳地值得嗎?
從此以后,我還真正把為他修山的事當成一回事了。
說是這樣說,工作一忙,就又把這事給耽擱了,有時甚至是忘了。他對我們的不夠重視不夠關心十分生氣,就自己籌劃了修山的事宜,找了他十分信賴的人幫他從很遠的地方購回了蓋石,找人從河壩里淘沙。
我的確不明白父親為什么要在他還活著時就必須把老屋修好以候他居,就說他再急也不至于一兩個月都等不得吧,再不放心也不至于不放心他兒女吧。他就說這兩年村里比他小的都過世幾個了,現在這人說死就死了,快得很。他說他去看那些入土之人時的情景,年輕人根本不當回事,埋得潦草,埋得亂七八糟,所以不把山修好,即
使死了也不放心,自己的老屋咋個修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在世一輩子就沒有住上舒心的房子,死了也還住不上,不更冤枉嗎?事實的確如此。這讓我們為兒女的萬分愧疚!
于是,我們幾兄妹決定擇一吉日,破土修山,讓他老人家心里舒坦,讓他目睹以后放心,不給他留下任何遺憾。
正當我們準備行動時,他又悄悄地對我說“還是找個陰陽先生再看看吧,萬一……”
我凝視著他。
過了不久,母親打電話說,父親為了和別人爭墳地吵架了,我問處理好沒有,目前說已平息了,就是心里窩了一口氣,在家里坐立不安,沖天下地地和她生氣。回到家里,我向他了解此事,他都還氣鼓鼓地。
“本就是別人的自留山,權力在人家,你就是要那塊地也只能跟人家商量。”
他不容我說完就搶過話頭。
“你這就打胡亂說了,是我爸爸先埋,自留山是以后的事,哪個在先?”
我大悟,“還有這事?”
他不回答我,悻悻地揚長而去。
我再次感到了修山的緊迫和重要。
晚飯以后,我讓他盡快請陰陽先生來看墳地,選定了以后,即破土動工,告慰他懸了幾十年的心。
沒多久,他便請到了先生,日期確定以后,他打電話告訴我并讓我如期而歸。本想說脫不了身,又怕再次傷他的心。在他的心里還有什么比選墳地更重要的呢?
首選點還是18年前他選中的地方,先生聽他將好處一一道來以后,只仔細觀察了四面的山勢環境以后,一句話不說就往山上走去。走到爺爺、奶奶的墳處,先生停下來又看了看,顯得很神秘的樣子。父親剛想說什么時,先生又向前走了。父親有點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像是想什么,我知道,在他站立的地方正是他與別人所爭之地。先生往前走不遠停下了腳步,瞬間便向西橫穿,父親卻在下面喊“不能離我爸爸和媽媽太遠。”就在他這話落地時,先生已站定在爺爺奶奶的墳后。
我站在先生的旁邊,四處眺望,并沒有感到什么異樣,也看不出有什么好,和父親自己選中的地方相比似乎差了很多。
父親趕到后說“就這兒?”
先生一言不發地點點頭,生怕把龍脈給嚇跑了一樣。
“我們的規矩是懷抱兒,背背孫,我應該埋在爸爸的前面一點。”
“規矩是人興的,地勢是自然生就的。”
我們都不說話了,坐在這塊有龍脈的寶地上休息。先生又給父親交涉了一些有關修山方面的事,起身便走,我們便尾隨而下,有幾分釋懷和解壓的感受。
晚飯以后,先生幫我擇了個破土的日子,在幾個月以后,父親臉上有幾分不高興,又不好啟齒。
其間,他又打電話征求我的意見說:“我認為還是我選的那個地方好一些,是不是還是修在那個地方。”
“你不信陰陽先生的?”
“信是信,心中總不很踏實。”
“你自己定吧!”
“那就算了吧,還是聽先生的。”
“你自己考慮好。”
“不光是我自己考慮好,你以為莫得你們的事嗦,埋錯一座墳,斷了一支人,未必然你們不曉得。”
好一陣電話里沒聲音,我知道父親又生我的氣了,正準備勸導勸導,卻傳來他十分憤怒的聲
音。
“老子還不是為你們考慮,就老子這百十斤,隨便扔在哪里都得了,不醒事的東西!”說后,電話被他狠狠地壓了。
破土那天,我們都不在家,他也不在家,只托付給一侄孫幫助照管。他正在成都看病,但病還未看完,他就堅決地要回去親眼盯著修山,我們勸他他不聽,越勸越生氣。
“好不容易出來,千難萬難地約了專家,是醫病重要還是修山重要?是不是回去就要睡到里面去,臨死的人了,連輕重都分不清楚。”
母親的話讓他平靜下來,病看完開好藥的次日,誰也勸不住他就急匆匆地趕回去了。
十來天以后,他打電話讓我們都回去,我問他什么事這么重要。他說山修完了,后天要扣蓋板了。強調的是蓋板蓋上就只好等到下葬時才看得到了。恰好那天我去不了,兩個弟弟也去不了。如果這樣,會給他當頭一盆冷水,他會感到兒女對他的冷淡。晚上,想了很久如何告訴他這件事。
電話打通以后,我先問他山修得如何,滿意不滿意,他都一一地不厭其煩地給我講,底子做得牢,邊墻砌得直,特別是蓋石,材質雖不很滿意,但蓋上去青絲合縫的。我說如不行,按蓋石的尺寸重新買一副花崗石的。他沒有表示反對,只說:浪費了可惜。
從他的語調中,我聽出了父親的喜悅,聽出了他死有所歸的高興,聽出了他對老屋的滿意和滿足。這時,他會不在乎什么,兒女們批評他他都不會生氣。
“恰好我們幾個都回不來,對不起,你要理解和原諒我們。”
好一陣他沒有說話。
我生怕再一次傷害他,這么一件事,我已經讓他生過不少的氣,傷他幾次心了,這已經為兒不孝了。好不容易呀,才讓他高興起來。在給我打電話之前,他是抱了多大的希望呀,他是想了我們幾兄妹分享他喜悅的場面呀!他是設定了多少在鄉親們面前顯示自豪的表情呀!我們一個都不回去,他的老臉擱哪里去?在鄉親們的面前還怎么個活法呀!
我在電話里連叫了幾聲爸爸,他都沒吭聲。
“是不是要舉行個儀式,辦幾桌?”
他有氣無力地應著:“舉行啥子儀式辦啥酒席,就這樣我都怕人家說,把你們牽扯進來。只是修完了,讓你們看看,滿意不滿意。”
“你看吧,如果必須回來,我們就請假。”
“算了吧,忙你們的,不影響你們的大事。”
父親放下電話以后,我久久地佇立在那里,心里不是滋味,甚至隱隱作痛。幾十年以來,父親在兒女們身上耗盡了油、熬干了水,一輩子茹苦含辛,一輩子以我們為本,在他即將走完人生之路時,我們不僅不能陪同他,就連一座十分普通的老屋,在他近20年的牽腸掛肚中我們都沒能為其運一塊磚拿一粒沙,什么都是他一手一腳為之。對他這個十分要面子的人來講已經是全然不顧了,即使是選一塊墳地,他都不是為自己考慮,是為了這支人,為了兒孫和兒孫的兒孫。
我也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和父親相比,身上還有多少自私未去,還有多少虛情未除,什么時候能像他一樣,始終以兒女為本,終身為兒女著想為兒女奉獻呀!
我給弟妹們紛紛電話,讓他們能回家的一定回去,回去不了的也得給他老人家去個電話,讓他空寂的心稍許得到一些慰藉和填充。
放下電話,朦朧中父親向我走來,他那清矍的身子越來越大、越來越高,成為一座山,擋在我的面前,讓我永遠也無法翻越。
我默默地佇立在那里,淚眼婆娑地懇訴著:原諒我們吧,敬愛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