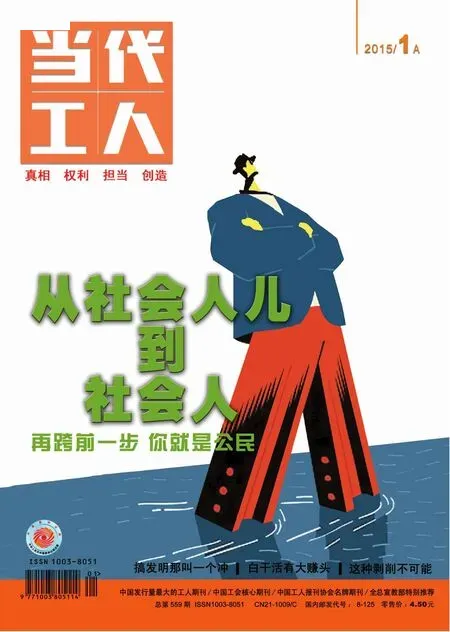路徽:那時的身份證
文|老楊頭子
路徽:那時的身份證
文|老楊頭子

徽:標志、符號。如國徽、校徽、帽徽、徽章、徽記、徽幟。徽是宣示,也是凝聚,更是圖騰。有圖騰就會有精神、有意志。社會轉型期,當崇高、尊嚴等被一一解構和嘲弄后,因徽而信仰,在徽里找到自我,便是我們最該重拾的希望。
獎品是800斤小米
1990年中秋剛過,我們這些臨近復員的老兵沒事就聚在一起探討,將來的就業問題。七嘴八舌中,戰友老蔫慢吞吞地說:“我哪都不去,就上鐵路。”老兵們詫異,“你是哪路神仙?你說進鐵路就進鐵路?咱得聽民政局安置。”“我爸在鐵路上班。”
能進鐵路,那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我也想。我喜歡那衣服,那徽章,那氣勢。老蔫送我一枚胸章,紅色圓形的,上面是白色路徽。我細細打量,中國鐵路路徽整體就像一臺迎面駛來的機車。上面是象形人字,下面是工字,像鐵路鋼軌的橫截面。從上往下看,喻意人民鐵路;由下往上看,喻意鐵路工人。我感嘆這設計用心,老蔫說,“路徽要表達的就是人民鐵路屬人民,人民鐵路為人民。”看看每年春運一票難求便知,鐵路對人民多么重要。
典典滴滴
新中國成立前,一條鐵路線一個管理局,各有各的路徽標志;新中國誕生前后,鐵路陸續回到人民懷抱,路徽甄選而出,成為新中國工業系統中最早統一使用并沿用至今的標志。據說某些藝術院校還會將路徽作為創意設計的經典范例來評述賞析。
多年后,我曾上網查閱新中國鐵路路徽的設計者,介紹寥寥:陳玉昶,滿族,出生于1912年,遼寧省沈陽市人,自幼愛好美術,曾在日本的高等商業學校就讀,在交通部業務處任職期間應征參加鐵道路徽設計,作品最終當選。1969年,57歲的陳玉昶在長春病逝。
至于甄選過程,今日敘述起來并無太多“臺前幕后”。當時的軍委鐵道部向社會各界廣泛征集路徽式樣,一共收到3200多種圖案,每個應征作品都編上號,在鐵道部舉行了展覽,向職工征求意見。民主后的集中便是鐵道部專門成立了路徽圖式審查委員會,反復審查后,呈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和財經委員會批準,確定了現在這個“人”“工”合成的式樣。據說時任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審閱入圍作品時,沒多加思索就選了這件。
這件事最大亮點在于第一名的獎品是800斤小米,這相當于從事繁重體力的勞動者個人全年足額口糧。我好奇,陳玉昶是怎樣保存這么多小米的?穿越到現在,小米手機異軍突起,iphone6供不應求,萬能的網友們調侃:幸虧不是800斤蘋果啊!
這胸章是老蔫的心愛之物,轉送到我手里更是視若珍寶。那時路徽的配發、使用和管理很嚴格。鐵路職工出入廠區、值班、公差或集體活動都要佩戴。一旦丟失,要到人事部門備案,將編號記錄下來,在鐵路局內發行的報紙上登聲明作廢。作用和重要性不亞于身份證。
然而,我們對胸章的感情遠不及老蔫父親。老蔫說父親那代人以鐵路為家。每當父親要出門接發列車時,都會照鏡子端正一下胸章的位置,然后從掛鉤上摘下帽子,對著帽徽吹兩下。小小習慣在老蔫眼里顯得極其神圣,那代表父親將要去為人民服務。有一次,父親把帽子戴在老蔫頭上,老蔫站得筆直,生怕自己的小腦袋把帽徽戴歪。
名字只一個
復員后,老蔫順理成章進了鐵路,而我被分到一家企業。那家工廠的煙囪在我當兵前就不冒煙了,我鐵了心沒去報到。民政局二次分配,把我分到了鐵路。我狠狠親吻了胸章上的路徽,它將成為我身份的象征——鐵路人。
報到那天人挺多,鐵路廣場上黑壓壓全是腦袋。一個穿鐵路服的老者,在二樓平臺舉著麥克風組織站隊。我記不起他的模樣,但他帽子上的路徽在陽光下格外顯眼,讓我印象深刻。
接收人員不關心每個人在部隊的職務、表現,就問一句父母是鐵路哪個站段的。我說我爸媽都是地方廠礦的。話音剛落,我名字前就被打了個挑兒。
隔天,各站段來領人。我跟著隊伍進了火車站后面一個青磚瓦房的四合院。領隊的大個子介紹:我姓嚴,歡迎大家來到工務段。不管以前各位在哪個部隊從事什么職務,以后咱們的番號就一個,1435,咱們的名字也只有一個,工務線路工。今日回憶,這情節像極了周星馳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的片段,進了華府,唐伯虎的編號是9527。他為秋香來,我是被那衣服、那徽章、那氣勢所吸引。
培訓我們的教員是來自養路一線的老顧。他向我們展示了鍬、鎬、耙子、鐵棍一類的家伙,然后畫了個路徽,“記著,路徽下這個工就代表著我們——每天和道軌親密接觸的工務人。”剛才情緒還有點低落的新人被老顧忽悠得挺興奮,“咱們就是支撐鐵路的脊梁唄!”
鐵路特點可以概括為“高大半”——高運量、大動脈、半軍事化。以前工務段招人,能扛動枕木就行。隨著鐵路發展建設,養路一線不光要體力,也拼智力、講文化。老顧說鐵路是個大聯動機,工種繁多,每天為旅客貨主服務的不僅僅是路服筆挺的車站服務人員和列車員,也有咱們,頭上的路徽都是一樣的。你們好好干,埋沒不了。
我相信老顧的話,那路徽就像一種信仰,證章、帽徽、紐扣、機車、建筑物上,路徽無處不在,也烙印在心中。很難想象,那是怎樣一種自豪感和歸屬感。
理想很美麗,現實很殘酷。1997年4月1日至今,鐵路先后進行了6次大規模提速。每一次提速,工務人都揮灑了無盡的汗水。相對付出,工務人得到的回報卻是微不足道的。
提速后,客貨運量陡增,工務段任務量逐日加大,除了常規的維修保養,還要參加無休止的道岔大修、轉線施工等大規模施工會戰。很多工友常年吃住在沿線現場,一年到頭休不到幾個完整的星期天。榮光下,工務人默默隱身,我們的衣服油脂麻花,我們的活計苦臟累,我們的月薪勉強糊口。社會上稱呼我們“鐵道驢子”,還有一套順口溜: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逃難的,仔細一瞅,工務段的。某些領導也不待見“素質偏低”的工務職工。
何以激勵我們?路徽,路徽看得見。
當各級部門成立了不同規模的監察大隊,每日拿著高清攝像機、高倍望遠鏡輾轉各地,現場“圍獵”一線干活的工務職工時,我心就好痛。倘若真的違章違紀就罷了,偏偏這些人為了完成上頭規定的硬指標,雞蛋里挑骨頭,每月都有冤假錯案發生。

路徽設計者,陳玉昶(1912-1969),滿族,遼寧沈陽人。1938年畢業于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專門學校。1949年10月,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任職。1961年調吉林省交通廳工作,1966年調省汽車修配廠工作。這是他當年榮登媒體。
那段日子,我許愿穩穩當當,不出問題。輕則扣錢,重則下崗啊!入路之初,路徽映襯下發光的理想,在這種高壓氛圍下,消磨成了只是養家糊口。我不曉得,這是不是體制運行的悲哀。
幸而今天一切都在好轉。
老情結新變化
在道軌上敲敲打打的我,有一個愛好——寫作。2010年,路局宣傳部派我去采寫溫泉寺橋梁工區當年學大慶的事,他們是1960年代鐵道部命名的百面紅旗之一。現任工區工長領我來到了曾經的榮譽室,門把手早已爛掉,工長找來一根撬棍,別開了門;房子漏了,地板塌了,滿地都是剝落的墻皮,只有英模的臉在布滿灰吊和蜘蛛網的墻上笑容燦爛。
那天很巧,當年學大慶的老工長,80多歲的于明遠老人也來到工區。老人指著一些老照片告訴我:“那時他們想出了冬防洪,夏防寒的思路,但維修費不夠,他們就到河里篩沙子,到山上撿石頭,割條子編土筐,爆破廢舊圬工梁當鋼鐵料用。”
看老人講述往事時的神情,我感受到那個年代鐵路人的激情。他們創造的不平凡對應著今日的滄桑,曾經的鐵路人這一身份證明,或許是一生最大的安慰。路徽的設計者肯定不曾想到,這簡單的一人一工,由多少血汗淚鑄就啊!
2013年,鐵道部撤銷,掛了6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的牌子被送到了中國鐵道博物館。“中國鐵路總公司”的牌子悄然換上。多年后,或許鐵路和航空一樣,出現多家公司,至今已有66個年頭的路徽也可能發生變化,許多帶有鐵路路徽的老舊物件會成為收藏界的搶手貨。于我,那是職業生涯的最難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