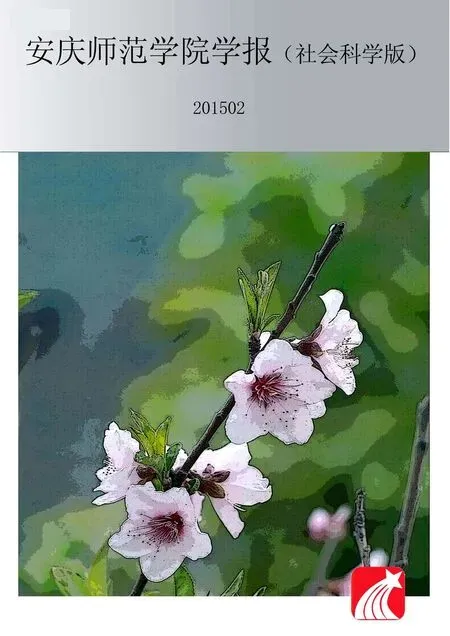中國山水詩理論的特點與現代研究評析
張兆勇,李群喜
(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
中國山水詩理論的特點與現代研究評析
張兆勇,李群喜
(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在中國文藝史上,士人寫山水詩如同畫山水畫,但山水詩理論并不如山水畫論突顯。個中原因,一是寫山水詩理論往往隱在于宋代以后一直繁榮的詩話之中;二是詩人創作山水詩更遵循“詩言志”這一總價值旨趣。上世紀西學傳入以來,中國山水詩理論研究成就顯著,但也有其局限性,一些論斷并不符合中國山水詩發展變化的事實,因此作為理論來說是蒼白的。
關鍵詞:山水詩;理論研究;畫論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2.010
中華作為一個民族文化大國,有一個顯著文化特征,就是有著不同于西方的獨立的自然觀,其中包括獨特的應物方式、感物理念等。眾所周知,中華自然觀除保留在儒道先哲的著作中,還被歷代學人保留在豐富的詩文書畫的創作中。與此同時,歷代學人亦對詩人、畫家的山水感悟成果表現出深切關注和濃郁的探討興趣,并將其作為感悟自然觀的渠道與角度,將山水意識留在對他們的批評著作中。從文藝學的角度來說,寫山水詩與畫山水畫應是同一品位與境界。假如把《魏晉勝流畫贊》、《古畫品錄》、《畫山水序》,以至于《林泉高致》、《畫禪室隨筆》作為總結畫山水的理論經典,那么按常理推論,歷代學人以探討山水詩而形成的理論成果也應當與之相對應、與之相呼應,有一些扛鼎之作。可這是一個被忽略的問題,若仔細梳理,會發現其中飽藏著中華士人關于寫山水田園從創作到批評等方面的重要信息。比照一下宗炳的《畫山水序》,我們覺得歷代關于創作山水詩的理論內容至少應包括:關于山水詩歷史的闡發,寫山水詩的緣由,寫山水詩的價值,寫山水詩時主體表現出的特征,欣賞山水詩時欣賞者的表現特征,寫山水的審美切入角度及用以承載的意象探究,等等。
一、一個不爭的事實
縱覽歷代山水詩理論,不難看出,雖然山水詩在魏晉時代就已經獨立,雖然山水詩的提法早在白居易的時代已經提出(《白氏長慶集》卷七《讀謝靈運詩》:“泄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雖然歷代有關山水詩的理論亦很豐富,但把這一理論聚焦起來加以闡發總結的論述并不充分,亦不很自覺。一個十分顯著的不足就是缺少理論的單篇,更缺乏一個只針對山水詩創作與審美的理論系統。
若就此找尋起來,會發現中國古代山水詩理論非常不突顯,它僅有以下兩個方面特征:
(一)看似豐富,實際上并未曾自覺成篇,即沒有膾炙人口的單篇行世。當然,這主要是相對于山水畫理論來說的。可以說,山水畫從誕生時起,理論與實踐就齊頭并進。而在山水詩方面,歷代的創作大家雖均以不同的方式、方法、目的感悟著山水自然精神,給世人留有豐富的創作實踐成果,但他們并沒有推出一個相應的單篇理論文章,來總結、指導、詮釋創作。
(二)與山水畫論看似區分實際不分。中國山水畫論家往往同時就是山水詩人,或與山水詩人有密切往來。尤其是中國山水畫理論,往往能一頭聯系時代來談畫山水的意義,一頭聯系著中華自然觀,從更宏大的背景來指證山水畫的價值,這些同樣適用于山水詩。這樣一來,山水畫理論家們的山水畫理論同樣起著指導山水詩創作的作用,使山水詩人無意中產生了理論總結的惰性,這一點從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與王漁洋的《帶經堂詩話》間的關系即能見出。漁洋詩話中的思維方式、結構框架有意無意間均在延續著董其昌。
為什么中華山水詩理論建設會有這樣一些尷尬,歸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山水詩并不如山水畫那樣,誕生以后很快就獨立作為單獨一類。把山水詩作為一類,歷代學人也始終沒有做自覺的努力。例如較早的《文選》,雖將詩分作許多類,但我們找尋山水詩只能從行旅等類別上再聚焦獲得。再如唐人選唐詩多種,但大多是從體裁角度。實際上,中華士人對自然的感悟,對山水的領悟及描寫,往往潛藏在他的游歷、詠懷、詠物之中,甚至散到了更寬的領域。因為理論家們將自己的思維往往停留在詠物、詠懷、游歷等的關切上,這樣一來,客觀上就影響著對山水詩理論的聚焦。
其次,從宋代開始,隨著道學對天人關系的梳理,天命性情意識的加強,士人的山林境界與山水情懷得到了充分的涵養,寫山水詩理論有了新的轉機與命運。可也就在此時,詩話以它的隨意性、隨筆性體現生命力,成為此后各種詩歌批評的主要方式與平臺。學人對山水詩的批評也就被大量融入詩話,客觀上影響著山水詩理論再出單篇。歷代詩話中雖有不少表現出對山水詩人、山水詩作的熱議與深沉關切,但若仔細品評下去會發現,他們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借此建立山水詩的理論。換言之,宋代以來詩話雖廣泛涉獵了詩人的山水詩作,但作者目的在于針對山水詩人的審美境界和詩人情懷,只是間或地表現出明確、自覺的山水意識,但其目的并不止于此。其例不勝枚舉,比如明代前后七子大量引入唐人山水詩,卻旨在談唐人法統。
再次,除上面兩點外,還有更重要也是更本質的一點,即在中華士大夫的心目中,詩言志、詩抒性情才是被認可的詩本質。這一點一直沒變,只不過有時被提出來加以強調,有時則潛藏在刻意的抒情之中。所謂“情”,也即泛指喜、怒、哀、樂。若談與山水理論的聯系,在于表面上情由各種各樣的原因所導致,但根本原因則在于士人心目中情由人與自然關系的表現不同而引發,這在魏晉以后廣大的士人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具而言之,中華傳統的原始積淀認為人與自然一體和諧,圓融是其本質。因此所謂喜、怒、哀、樂等情也許有著各種直接原因,但從根本上說均是針對這一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來說的。比如,哀感在詩人的抒情世界里雖各種各樣,但憑什么言之哀,無不在于詩人所理解的人與自然之關系由和諧轉為不和諧、不圓融,反之亦然,詩人的欣慰在于感到周邊自然氛圍正走向和諧。比如韋應物有詩云:“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秋夜》)[1]504又有詩云:“喜隨眾草長,得與幽人音。”(《喜園中茶生》)[1]350即如此。
縱觀一下不難發現,中華士人始終沒有脫掉這一根本法則,累代如此,以至于無論表達什么樣的情感,均能分析為人與自然的關系,似乎要將所抒情感拉回到自然背景中才能使其鮮明,才有意義。就這一點來說,歷代詩人的感悟、詠懷詩最為典型。
差不多所有受后人景仰的詩均有自然意識、山水情懷,而在此所謂的“山水詩”,也就不是一個派的問題,不是從陶、謝開始,更不是王、孟所開創的派。在筆者看來,在中華詩歌史上不存在山水詩派,而自始至終有大量包含山水意識的詩。論山水詩以派,更準確的定義是指闡述者把握詩以某種觀念。或換言之,在中華詩歌史上無詩不具山水、無詩不依山水為其終極背景。這是因為中華士人往往將自己的情感放入自然宇宙的背景予以表達,乃根源于士人的哲學理想,比如“極高明而道中庸”、“推天道以平民事”等。我們下這樣的結論,就能解釋出批評史上為什么會始終把陶、二謝,把王、孟、韋、柳作為熱門話題,但幾乎找不到借他們的山水詩理論。學人關注王、孟、韋、柳,僅僅關注他們的性情,關注在自然山水的背景上來評品他們的性情抒發。比如從歷代評品之文中可看到韋應物完整的士人體道心旅,但在此卻擷取不到關于山水詩的理論。
山水并沒有被歷史上的哪一個評論家稱為派,以派的思維來定格詩人,宋以后亦有,但不難知道凡以派則有貶意,恰旨在指責這些詩人。魏晉以后的許多山水詩經常能讓后人以山水詩聚焦,能讓后人以山水條理匯總在一起,也不是沒有原因。如果說魏晉的幾代玄學家以儒道交匯,甚至吸納佛教大乘之學,在人的自覺意義上理清人與自然的關系,使之成為當時士人有意識的心理狀態,那么人的感性生命自覺又讓玄學論者將這些理論安排在感性世界周邊的山水中來落實。可以說,兩個方面疊加在一起,使士人再去思索、抒發、理會他們的喜、怒、哀、樂時,一方面更為理性(理性更深沉、明晰),另一方面抒發喜、怒、哀、樂所回融的自然也更親切(取材身邊,即物應稱,目擊道存,抒情當下)。比如大謝《登池上樓》,謝榛云:“‘池塘生春草’,造語天然,清景可畫,有聲有色,乃是六朝家數。”[2]王夫之云:“始終五轉折,融成一片,天與造之,神與運之。嗚呼,不可知已。”又云:“‘池塘生春草’,自從上下前后左右看取風日云物,氣序懷抱無不顯著,較‘蝴蝶飛南園’之僅為透脫語,尤廣遠而微至。”[3]在我們看來,所謂詩言情是指抒發詩人的七情六欲,在這些詩中依然如此,只是在這些詩里詩人越來越將言情安置到親切可感的山水中,或轉化為山水意識,去理解,去鋪展,去領會。
筆者認為也可以把這類詩稱為山水詩,在于在這些詩中山水意象越來越集中、豐富;也可以不把這些稱為山水詩,因為其詩中的山水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借以抒發的平臺載體,抒發性情才是其本質。就此而言,這些詩人雖是山水詩人,但究其實并不準確。我們不妨把陶潛、大小謝詩在這個意義上做個比較。
陶淵明往往直抒他的七情六欲,只是在他的理想中又平添了濃郁的玄學意味。他的創造性在于以獨特的駕馭之功來把握自然背景,以宣其意。學人一般用“奇趣”來概括陶淵明,即在肯定他以這種天賦所取得的成就。
大謝致力于從新異角度來把握自然山水,從而表現一個玄學士人在風雨飄搖時代放縱地追尋山水以期玄言慰藉的心跡。和他們兩個相比,小謝盡管還是抒寫他的七情六欲,但由于少了羈旅閑愁,多了他所回融的自然,也漸脫去了玄學的色彩,因此與陶淵明、大謝相比直以氣象不同。
綜上可見,三位詩人雖均以寫山水而見特色,但后人景仰、褒貶他們均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筆下的山水,而是其性情與含融。換言之,他們其實并不是以寫山水而稱著,而是他們袒露在山水中的性情為人稱道。
描寫山水不只是他們的主要目的,這樣也就影響著后人受啟于他們而對山水理論的再創造與總結。可以說,正是以上幾點原因導致中國山水詩理論的特點——不自覺性、零散性、附依性。
二、哪里是切入的思路?
歷代詩話中的山水詩理論雖零散、不自覺及依附性強,但不影響將它們抽出來加以評估。對照一下中華自然觀會發現:在這些山水詩理論中,也有它獨特的深刻性和傳遞中華自然觀的傳導功能。這些是值得肯定的。
1.對中華自然觀來說,隱藏在詩話與詞話中的一些概念有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傳導性。在中華文藝批評史上,有許多概念,比如氣象、氣韻、傳神、神韻、意象、意境、平淡,凡此種種,它們在各家詩話中表現為相互關聯、古今相續、前后貫通流變。而這些概念所以能相通,雖有多種原因,但其中的一個原因尤為突出,即學人正是利用這些概念對山水詩加以解釋而使之客觀上相通的,或者說這些概念應是在闡釋山水詩時自我滋生養護的結果。
前面本文講過,所謂寫山水詩理論涉及寫山水的歷史,為什么要寫山水,寫山水的價值,寫山水主體表現出的特征以及不同時代寫山水不同的審美切入角度等。如果說上述這些拾掇起來是寫山水詩理論的框架,那么在文藝批評史上,上述這些概念應當是營造與支撐這個框架的基石。如翻過來亦然,即文藝批評史上的這些概念、范疇正是通過對寫山水進行闡釋而承載、轉運的。通過研究寫山水來探討這些概念、范疇,無疑是我們今日研究、挖掘、整理山水詩理論的價值所在。只有通過這些研究才能讓我們對山水詩真正進行近距離的聚焦,搞清關于這些概念的問題域,最終去整合關于這些概念的理論流變,從而實現山水詩闡述與理論概念闡發的雙贏。
2.將零星的、不完整的自然觀隱藏在詩話中,這是中國獨特的理論形式,同樣體現著士人關于自然的深刻領悟。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從根本上來說,在于對人與自然關系間的不同理解。中國人持守人與自然的和諧觀。中國人的這種和諧觀發端于《周易》(可參閱拙作《滄浪之水清兮——中國古代自然觀與山水田園藝術的文化詮釋》第二章,作家出版社,2001年),此后儒道兩家又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切入,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中國特色的自然和諧觀。中華文化中的這種自然和諧觀到了魏晉時代,以人的感性自覺為背景,又加以明朗化、明晰化。誠然,中國人的這種自然觀是在累代的哲人與圣賢那里得以提升的,但也與歷代詩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所謂的對中華自然觀的領悟的特別化角度,就是指這種自然觀闡發與詩的關系。關于詩與中華自然觀的關聯性,若分析起來,非常明顯體現在詩人創作與學人批評兩個層面上。
就詩人創作層面來說,前面我們已經講過,詩人所抒的七情從根本意上來說,均來自詩人對自我與自然關系的理解上。一方面,詩人之性情來自自然,喜怒哀樂之情往往取決于士人自我所感到的與自然的距離;另一方面,詩人往往將性情回融到天地宇宙,來把玩、評估自己的性情。這一點在《古詩十九首》表現得最為典型,本詩也正是以此特征贏得后人尊重,比如劉熙載云:“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4]其次,就批評層面說,與詩人創作相關聯,中華學人往往是將對自然觀的感悟寓于對山水詩的領悟與品評中,并以詩話隨意的形式予以表達。若縱觀一下歷代對《古詩十九首》的評論,幾乎可以理出學人關于自然山水的解釋史。誠然,其所藏在有一些詩人那里也很淺,但它的淺不在于這種方式的淺而在于詩人自身的淺。試以歷代評孟浩然為例即可說明。孟浩然詩雖或以清澹為歷來學人所推崇,但也有兩個批評家公然指責其短,并且所依托的正好是中華文化大背景。蘇軾云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語見《唐音癸簽》卷五)王船山云:“襄陽律其可取者在一致,而氣局拘迫,十九淪于酸餡。”(語見《唐詩評選·〈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評》)
綜上所列舉兩點,就能夠說明從詩話中找尋、研究與挖掘累代以來寫山水詩理論的必要性。換言之在詩話中,這些零散的看似不起眼的山水理論,它既是我們考查歷代學人自然觀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們涵泳中華自然觀營養的一個極佳的角度。
三、幾個值得再思索的誤區
上世紀以來,關于中華山水詩的挖掘、整理、研究、總結均有顯著的成績,約略說起來主要體現在下述幾個方面,它們分別是:關于起源的探討,關于分派別類及其比較研究,關于變化問題闡發,可以說,上述所說似可支撐理論的框架。山水詩研究代表人物有陳貽焮、繆鉞、廖仲安、金啟華、袁行霈、葛曉音等,大陸以外如葉維廉、王國纓、龔鵬程、宇文所安、小尾效一均參與了山水詩諸多問題的探討,他們均有自己的學術特色與成就。如果說他們各以自己的成果,在寫山水理論的框架內共同營造了20世紀以來當代學人山水詩研究的空間,那么他們的共同成就也或多或少呈現了20世紀學人的局限性。茲略舉幾條:
1. 關于山水詩的起源說,20世紀以來,隨西方所謂“形象化”理論深入,學人又糾結于隱逸、逃避說,往往曲解、放大《文心雕龍·明詩》中“莊老告退,山水方滋”命題。在筆者看來,被后人認可為山水詩人的陶、謝活躍在玄學時代,宜屬于玄言詩人。此時玄言詩與后來稱為山水詩之詩并出,而此時詩評大家如鐘嶸、劉勰等在他們的著述中聲討玄言。除《文心雕龍》外,鐘嶸在《詩品·總論》中有那么著名一段經常為學人所援引,其云:“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論。”[5]在文學史界,不難發現20世紀學人無一例外援引《文心雕龍·明詩》中的“莊老告退,山水方滋”[6],并參照劉、鐘等對玄言的抨擊,在文學史闡發中以為山水詩興起于玄言詩的衰敗。
與文學史闡發相類,學術界幾乎是眾口一詞,把玄言詩與山水詩相對。在此問題上,臺灣學者葉維廉《中國詩學》一書在大陸的當代影響很大。在這本書中,葉氏對此問題做過重點闡述。在論述中利用列舉法,異乎堅定地得出結論,即山水詩越來越脫離玄言、淡化玄意而走向成熟。在筆者看來,這種山水詩源起觀以沒有歷史信息、與歷史相悖而經不起推敲。這里要說明的是,早在上世紀40年代,繆鉞老即指出雖山水方滋,莊老并沒有告退,此后葛曉音也持這個觀點,不過并沒起到針砭學人偏激之作用。
2.致力于分類分派,受制于派別陳述。從文學批評史上我們知道,其實早在劉勰、鐘嶸時,批評家就習慣于對文學史上的作家依一定的理念而作品類的總結。這種思維方式到唐宋時代依然在運用,批評家或以題材、或以風格、或以體制立論,但無論如何,更在意于從氣象、格調上去談一個時代的總格局。而學人以派視人,則與之相反,往往是在指責詩人詩作不入主流,這一點在有宋一代均比較明顯,比如說宋初指責西昆、九僧,宋末指責江湖、永嘉四靈等。可見,在中華批評傳統中正面去欣賞的詩,并不以派為高。正面積極以派論詩主要出現在20世紀,文學史家方廣泛使用之。仍以宋代文學史研究來說,建國以前比如有胡云翼《宋詩研究》、《宋詞研究》,建國之后有各種版本的文學史等,均很典型。文學史家甚或將幾百年的宋代文學變成各派的堆砌,學人在此以派框架詩人,并且以派切入對作家作品進行價值評估。這樣做當然也得出了不少結論,但更使批評陷入概念圖解之中。對山水詩的研究自然也沒逃干系,比如盛唐時代,李杜之外即整體以邊塞詩派與山水田園詩派劃定。可以說,以派論詩其理論沾滿了時代的塵滓,在筆者看來此應是對山水詩的遮蔽,顯然不是理論佳構,并隨著時代逐漸消沉。
3.以進化觀套裁歷代山水詩的變化,從而使中華山水詩本有的變化觀淡散于西方進化論學說,成進化論理論承載的平臺之一。
翻開各種版本的文學史著作,我們發現文學史家一般比較注重對歷代山水詩做總結陳述。在這些陳述中有一個特點,就是以為山水詩的流變體現為起承轉合、進化成熟態勢,即有一個萌芽、發生、發展過程。在我們看來,以起承轉合描述山水詩的流變,無疑有達爾文進化論的影子。而歷史上山水詩的變化并非如此,比如孟浩然與王維,王、孟與韋應物等。而在宋代,黃山谷與楊誠齋他們的山水意識更不適合于此。詩人的創作并不能簡單歸于高潮與衰敗,而是各以自己特點呈現著時代特征。他們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先進與落后,而是各具特點。以進化論套裁他們的同與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應是對中華山水詩諸多變化展開問題的遮蔽。其思路推及山水詩的理論建設,自然也是蒼白的。
以上我們花了不少篇幅,是在說中華的山水詩和山水詩批評均有著關乎體悟與傳承自然觀的重要性。因為它方式特別,同時又起著體悟自然觀的特殊作用,具有品味自然觀的特殊魅力,所以,它雖沒有單篇,但有強烈的依附性、隱藏性,依然有考察它的必要。只是從上個世紀以來,學者雖做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不少成就,使山水詩作為一個概念在文學史撰述中明確獨立起來,有著20世紀的學人特色,但在筆者看來,這并不能接近中國山水自然創作成就,不能有效融入關于自然山水的批評傳統。不少學者最多只是圖解了時代,從這個意義上出發,探討山水詩理論諸多問題還大有可為,而找尋山水詩理論及存留特色,亦應是研究山水詩不可或缺的內容。
參考文獻:
[1]孫望.韋應物詩集系年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2002.
[2]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1164.
[3]王夫之.古詩評選[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213.
[4]劉熙載.藝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2.
[5]陳廷杰.詩品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11.
[6]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49.
責任編校:林奕鋒
On Features of Chinese Theories of Landscape Poetry and Contemporary Studies
ZHANG Zhao-yong,LI Qun-x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Anhui, China)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the literati created landscape poems just like drawing landscape pictures, but theories of landscape poetry were not so well developed as that of landscape painting. One reason is that landscape poetry theories were hidden in the abundant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e other is that poets often held the value of “poems expressing ideals” in their creation of landscape poem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 Learning in the last century,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hinese theories of landscape poetry, but there exist limitations. Some do not fit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dscape poems. They are pale as theories.
Key words:landscape poetry; theoretical study; development; painting theory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730(2015)02-0048-05
作者簡介:張兆勇,男,安徽五河人,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李群喜,男,安徽太湖人,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04-20 201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