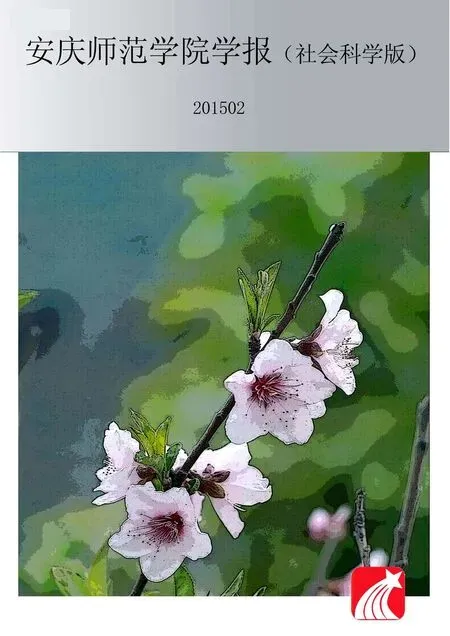《東方雜志》與近代中國鄉村形象的建構
韓楚燕,李發根
(安徽大學歷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
《東方雜志》與近代中國鄉村形象的建構
韓楚燕,李發根
(安徽大學歷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自20世紀20年代起,隨著民族危機的加重以及西方思潮的廣泛傳入,中國社會開始重新審視鄉村的價值所在。作為近代中國最重要雜志之一的《東方雜志》,為這一探討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臺。相關文章在承認農業與國家賦稅間重要關系的同時,分別從農民與社會秩序、農村與中國發展變革、農村與民族精神、人倫道德等角度重新構建鄉村形象。
關鍵詞:東方雜志;近代中國;鄉村形象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2.027
由于長期處于農業社會,中國古代的統治階級極為重視農業,將之歸為國家之“本”。然而,這種重視主要是從維護封建統治,特別是從賦稅、財政的角度來考慮的,即所謂“天下之大利,必歸農”[1],很少系統、正確考量農村價值之所在。近代中國農學家凌道揚在《中國農業之經濟觀》一書中指出:“晚近以來吾國士夫之著書言政治者多矣,而于農事之狀況、農民之經濟鮮有道及之者。”[2]這一趨勢在20世紀20年代才逐漸被打破,隨著國難日漸以及西方思潮的傳入,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農村的重要性所在,紛紛將眼光轉向傳統視角中被忽視的“邊緣”——鄉村。創立于1904年的《東方雜志》(以下簡稱《雜志》)是近代中國“雜志中時期最長久而最努力者”[3],且有“中國輿論大多數趨勢的指示器”[4]之稱,為鄉村價值的探討提供了一個自由、廣闊的平臺。
一、多角度下的鄉村基本價值
農業是人類社會兩大物質生產部門之一,《雜志》的相關文章認為,農業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衣食之源。“農業既是維持人類生命之唯一重要職務,故人類視之,宜較其他事業為重。”“歲產物品以維持人類生命于勿絕”。進一步言之,農業乃人類社會存在之基本動力。傳統中國以農立國,農民占國家人口之絕大多數,一旦農業被災,則農民歉收,進而物價上漲。在傳統自救模式荒廢與政府無力之現實下必將使得以農為生的農民走上絕路,“直接受害者,動以千萬人計”[5]。
自近代中國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后,列強一方面向中國傾銷商品,另一方面掠奪中國的廉價原材料以滿足自身工商業發展需要。列強的經濟入侵加劇了中國的貧困與危機,《雜志》所刊文章主要從商貿角度將之歸為“外國的工業品輸入中國,中國無工業品輸出以相抵消,所以國內商場被外貨侵入,國際貿易常處于債務者的地位。”[6]面對如此困局,中國尚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主要是依賴于農產品的輸出以部分平衡貿易逆差。因此,有文章指出:“現時我國輸出貿易,農產品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年中所得數萬萬外人金錢,足抵每年之巨大輸入貿易之不少。”[5]按當時的統計,輸入中國的商品每年達海關兩四五億之多;幸依靠中國農產品的輸出(約占進口值的80%),進而平衡這一進出口差額[7]。
此外,由于受一戰后歐美思潮的影響,學界開始意識到工業文明的城市繁榮是建立在農村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有文章指出:“都市的繁榮與存在,固依賴于農村”[8]。總之,農業是發展一切事業的基礎。“為發達全國各種事業計,尤不得不先發達農業”[5]。對于以農立國的中國來說,無論是行政、教育、軍事還是其他事業均依靠農業這一財政收入的最大來源。可以說,“農民是筑了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基礎”[9],“農村是中國經濟的命脈”[8]。
二、基石——鄉村與社會秩序
首先,從人口多寡與國家治亂角度來看。自清代乾隆年間至道光中期,中國的人口呈幾何增長,這一增長絕大部分又源于農村。19世紀末,伴隨著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中國的傳播,學界開始注意到中國人口過多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之間的矛盾。1904年,《雜志》即開始載文討論中國人口之多寡與歷史時期國家治亂的內在聯系。文章指出:“蓋中國之治亂與人口之眾寡相比例者也,中國之治非真有求治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寡少耳;中國之亂亦非真有治亂之道也,徒以人口之增加耳。”[10]而后,《雜志》也曾刊登數篇有關人口的劇增與中國社會秩序的危機之間內在聯系探討的文章,從而基本確立了人口過剩是中國社會秩序紊亂的重要原因的結論。
其次,從鄉村生活的質量與社會秩序角度看。傳統中國以農立國。農民占總人口80%左右,廣大鄉村構成中國社會細胞,“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底層,全個社會是支持在農民的基礎之上的。……由中國以往的歷史觀察,實在可以說無論那一次革命運動無不和農民有很大關系,尤其是和農民的生活問題有重大的關系。”[11]鄉村秩序運行直接關系社會的穩定與否。“一個國家是否安定,只要看那國內大多數人民狀況是怎樣就可以斷定”[11]。以農立國的傳統中國,“凡是承平的時代,都是農民生活富裕的時期;一遇災歉,農村就引起不安,從而地方亦隨之而不安了。”[7]中國歷史的種種動亂,都可以說“是因農民生活不安定而起。中國每次的革命農民都是直接的參加者。”因此,有學者提出,如果農業發展、農民富裕、農村安定不但可使“內地人民生活可以非常地安樂,就是在國際地位上也可以衣食世界。”[7]故“中國如果革命,那一定是由農民問題促成的,是因農民的要求而革命的。”[9]此亦所謂“饑饉之年,天下必亂;豐收之歲,四海承平。”[12]
最后,全球視域下的人地(指廣義上的社會資源)矛盾。自地理大發現后,全球逐漸連成一個整體。這一趨勢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而日益密切。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的加劇,新興的國家開始不斷向外擴張以尋求更好的發展機遇,從而加劇新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沖突。有學者從人口學的角度思考,認為人口增長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矛盾是誘發德國、日本等新興強國加快對外擴張侵略的步伐,從而威脅著區域甚至是全球的安全[13]。因此,基于這一原因,人口過剩的鄉村不僅是區域發展的潛在危機,也威脅著全球安全。
三、動力——鄉村與社會的發展變革
首先,鄉村是社會變革發展的基石。在近代世界產業革命浪潮和西方確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巨大優勢的大背景下,傳統“以農立國”理念被“以工立國”取而代之,傳統“以農立國”業已成為近代落后挨打之罪魁,農業之重要性被集體淡忘。隨著這一時期相關學者對鄉村的重視,有人提出:“中國主要生產還是農業,而農民人口又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如果農民底生活沒有根本的改善,則一切社會問題亦將無法解決。”[14]有學者以俄國十月革命為例,提醒說,由于農民知識之蒙昧,使得革命后農產物的分配出現了種種困難,致使“工業政治一時不易實現”[15]。
其次,農業與工商業的互補功效。隨著對農業重要性認識的加強,有學者提出農業為工商業發展之基礎的觀點,若要發展工商業,則發展農業是其根本基礎[16],因為農業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原材料,因此,農業的衰落直接關系國家工業的發展前景[17]。近代中國工業之發展由于資金、技術等因素的限制,使得輕重工業發展比例嚴重失衡,當時唯一能與西方抗衡之工業也即輕工業,如紗業、絲業、面粉業等,而這類輕工業的發展原料導向性很大,可謂“無一不依賴農人供給原料”[5]。豐收之年,往往農產品剩余多,供給市場亦多,且價格較低,從而為輕工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機遇;被災年份,在本國供給原料緊缺的狀況下,唯有進口,從而受制于人,往往導致產品的競爭力大打折扣,甚至引發工廠停工、倒閉[5]。因此,陶希圣認為,中國工業的衰落之源在于農業的衰敗[19]。在農業生產力沒有根本性提高的前提下,人口增長無疑會使得民利縮減。為使農業擺脫這一困境,其中一重要舉措即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入城鎮工廠,在推動國家工業化的同時,解放農村勞動力,此亦所謂“工業愈發達,則農業亦愈進步”[5]。因此,亦有學者將農業與工業提到對等的地位,其所不同僅是生產種類相異[18]。
最后,鄉村是國家民族危亡的生命線。近代中國,外患頻仍,民族危亡日漸。有學者意識到,抵抗外來入侵的動力基礎實際源自于廣大的鄉村,因為,“農民生產占全生產百分之九十,其人數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故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是農民革命。”[19]面對日益加劇的外患,在備戰之際,至關重要的即為發展農業生產,從而為之作重要的物質準備[20],“決定我們抗戰勝利的主要的人力和物力的來源是在農村”[21]。
四、支柱——鄉村與民族精神及人倫道德
馬克思、恩格斯曾說過:“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22]進而指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作為人類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精神與人倫道德根本上決定于社會經濟基礎。近代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經濟凋敝。有學者開始意識到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意識間的內在聯系。1928年,《雜志》即刊文指出,人民經濟水平的低下會導致“一個國家文化的不發達”[13]。1932年,《雜志》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危機是從民族精神的不振和國民的道德墮落的現象產生出來的。”個中緣由,實則“是因為農村經濟的基礎已經逐漸的動搖,且有瀕于破產的趨勢。”[12]而正是由于中國農村經濟的衰敗進而導致教育的破產,種種敗壞人倫道德的現象此起彼伏。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就當時的南京、天津、青島、上海、漢口等五大城市的違法犯罪行為做了統計,其中“妨害風俗”(偷盜、賣淫、賭博等)最多,約占40%[12]。分析顯示,這些違背人倫道德的不法行為,多是由于種種壓迫而導致經濟破產的農民所為。因此,有學者提出:“農村經濟破產之后,恐怕數千年來高尚的文明將從此日漸消失了。”[12]面臨多災的近代中國,傳統自救模式的崩壞,“饑餓的怒火焚毀了親子間的關系”[23]。從《雜志》所載文章可看出,當時全國普遍存在著“賣子鬻女”的“人市”現象。青年婦女為了擺脫致命的災荒,亦多從事賣淫等事。鄉村經濟發展狀況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國家民族精神與人倫道德水平高低。
隨著民族危機日漸,近代中國開始逐漸反思近百年的“西化”模式為何未能使中國擺脫落后挨打的近代困局。隨著近代西方思潮的進一步傳入以及對鄉村社會的進一步了解,部分學者開始重新審視本已被淡忘的鄉村社會,逐漸將之從傳統賦稅之利中解放出來,從鄉村與社會生產、鄉村與社會的發展變革、鄉村與民族精神及人倫道德等方面全面探討鄉村價值。在此基礎上普遍認為,中國所出現的種種社會危機,究其根源是由“農村經濟的基礎動搖”[12]所致,因此,中國社會的根本在三農,解決三農問題是發展、壯大國家之根本所在。
參考文獻:
[1]陳瑸.陳清端公文選[M].臺北:大通書局,1987:13.
[2]凌道揚.中國農業之經濟觀[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3]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上海:上海書店,1990:128.
[4]齊水.蘇俄的中國研究與[J].東方雜志,1925(7).
[5]鄒秉文.農業與公民[J].東方雜志,1922(16).
[6]孫倬章.農業與中國[J].東方雜志,1923(17).
[7]吳覺農.中國的農民問題[J].東方雜志,1922年(16).
[8]陳醉云.復興農村對策[J].東方雜志,1933(13).
[9]農民問題與中國之將來[J].東方雜志,1927(16).
[10]論人口治亂之由與人口之寡少[J].東方雜志,1906(6).
[11]陳仲明.湘中農民狀況調查[J].東方雜志,1927(16).
[12]董汝舟.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J].東方雜志,1932(7).
[13]喬啟明.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研究[J].東方雜志,1928(21).
[14]蔡樹邦.近十年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J].東方雜志,1934(10).
[15]羅羅.農民生活之改造[J].東方雜志,1921(7).
[16]C.L.Stewart.現代各國農業政策之一斑[J].東方雜志,1929(12).
[17]陶希圣.中國經濟及其復興問題[J].東方雜志,1931(1).
[18]董時進.理想的東亞大農國[J].東方雜志,1927(11).
[19]高一涵.平均地權的土地法[J].東方雜志,1928(1).
[20]頌華.英國獎勵農業之金融法案[J].東方雜志,1928(11).
[21]孫冶方.抗戰和農村[J].東方雜志,1937(18,19).
[22]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馬恩列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23]許滌新.農村破產中底農民生計問題[J].東方雜志,1935(1).
責任編校:徐希軍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730(2015)02-0121-03
作者簡介:韓楚燕,男,安徽南陵人,安徽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李發根,男,安徽肥東人,安徽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