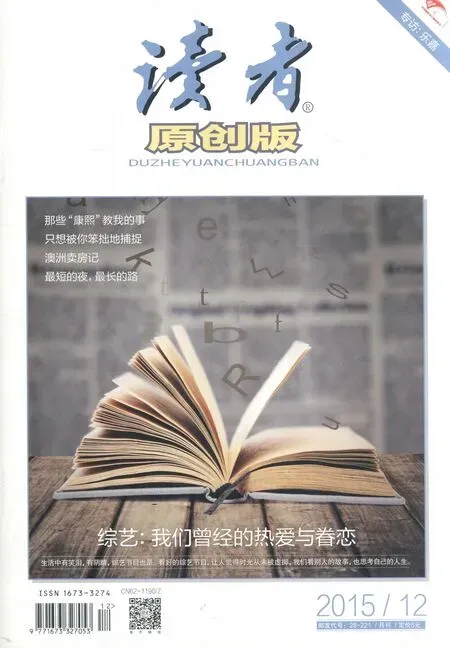最短的夜,最長的路
文_謝亞喬
最短的夜,最長的路
文_謝亞喬
記錄校園生活,書寫青春故事。《讀者·原創版》雜志推出“原創之星—校園寫作計劃”,面向全國高中及大學公開征選優秀作者和稿件,為熱愛寫作、有表達欲的青年學子搭建一個展示自我的平臺。投稿信箱:ycplan@qq.com
編者按:一個大學女生投來簡歷,希望可以來編輯部實習。簡歷的前半部分都是“規定動作”:個人基本情況、教育經歷、實習經驗……打動我們的,是最后附的實習札記。那是她在中國青年報社實習后寫的,有實習之初的忐忑,有對工作的熱情和付出,有對作為師長的媒體人、采訪對象的觀感,以及對未來、對社會問題的思考,還有女生的細膩和小小的幽默。我們已經決定請她來實習了,有一點兒好奇—不知道幾個月后,她會如何記錄這段實習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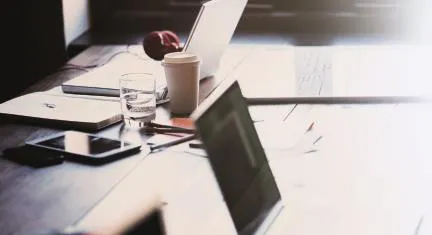
一
很早就坐在電腦前,直到凌晨1點,才給自己的這段實習總結起了個名字。敲出來的速度太慢,記憶早就像紛紛揚揚的雪,洋洋灑灑,卷起來。
十幾天前,我也是這樣深更半夜坐在群租房的廚房里,寫關于北京流動青年生存狀況的稿件,直到凌晨6點。從本心來說,我不喜歡這樣,傷身體。
相比第一次在上鋪通宵寫稿,第二次在廚房的經歷顯然更鮮活。這里的廚房,鍋碗瓢盆一個有一個的氣味,油煙味兒越不好聞,我就記得越深。前半夜,我反復看著自己和另一位實習生采訪來的素材,腦補著幾張面孔,仿佛他們就圍在我的身邊,陪我一起蜷在板凳上,盯著屏幕,看著文檔里自己的故事。
我開始依照相關的背景資料組合他們的故事,寫到凌晨三四點的時候,人有些亢奮。越近黎明,頭腦越發清醒,感覺天地與我同在,大家一起努力著,脫離混沌的黑;又像跑了很久,只在重復“跑”的動作,兩條腿像離開了身體,只是飛速地向前沖。
我寫了整晚,一轉頭,隔著臟污的玻璃看窗外時,被外面的一點兒亮光震了一下,時間過得太快,夜太短,心里卻有種莫名的驚喜。寫到天亮,我的第一反應倒不是累,而是結結實實的富足,私心覺得日子真是干脆利落,一口氣下來,沒有拖延和浪費。
二
在中國青年報社3個月的實習,讓我對這個完全陌生的部門有了很深的感情和敬重之心。得過9次中國新聞獎的部門主任,年齡不大,白頭發不少。這位業界前輩是每天最早到辦公室、最晚回家的人,離開報社時再晚,他也不忘拿一份報紙坐地鐵時看。要對新聞這一行熱愛或者說癡迷到什么程度,才能達到他這樣的境界?他不怎么愛說話,三言兩語表達清楚意思,說完要害就行。
帶我寫稿的老師是部門里的兩位年輕記者。其中一位非常愛干凈,帆布鞋白色的部分總有些纖塵不染的意味,指甲修得十分整齊,被大家稱為“高冷小王子”,我想他該是處女座。
“處女座老師”對稿件有自己獨特的要求,和他一起做稿件,總能感覺到老師對事件有更深層次的思考和理解,不是解釋完一個現象就完了。
記者寫稿時雖然有采訪錄音,但自己得清楚要抓的核心是什么,圍繞這個核心要呈現哪些內容和觀點,而這些內容和觀點能不能引人思考或引發共鳴,能不能讓人放心、舒坦地去讀,甚至讀完以后還若有所思,接住執筆人拋過來的“點”,這些都需要事先考慮好。“處女座老師”就是一個能抓住稿件要害、替讀者省心的人。
另一位老師對實習生很有耐心,暖人得很。他帶我做過關于河南拆遷的特別報道,那是我第一次做這種調查性的報道,現在看來,實習生能參與這種稿件的創作,真是難得的機會!
就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法院判決書,第一次參與司法領域的特別報道的制作。從開始到結束,我都抱著一種好奇的態度,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如何給采訪對象打電話、要注意哪些細節等。
我要給20家拆遷戶打電話。那個陽光燦爛的周六,我坐在電腦前,挨個兒聯系他們。
很多拆遷戶總愛問我那幾個人生終極哲學問題:你是誰?你哪兒來的?你干啥的?開始我還比較有耐心,后來電話打多了,耳朵生疼,我也煩了。忙活了一天,最后見報的文字中,我的成果搖身一變,成了:“不過,前述15名受訪拆遷戶告訴記者,他們均未收到賠償,也沒有拆遷公司與其聯系。”每次看到這個地方,我都會感慨:就這一句話,讀者看起來沒啥,但誰知道得出這句話可不是分分秒秒的事。
三
我每次看著兩位老師忙碌,總在想,自己以后的生活會不會也是這樣的。我不知道的事太多,媒體發展過程中不可預料的事也很多。之前,大家總說這兩年新舊媒體變化太快,如果覺得很難適應,不如考研究生,再在學校讀幾年書,過幾年,也許能消停一點兒。前幾天和好友聊天兒時,還在討論做記者與讀研究生之間的關聯,還在聊著未來的發展計劃。
毫無疑問,我喜歡新聞業,我享受那種探求的狀態,享受奔赴不同的地方、與各種人交流的時刻,但喜歡不代表適合,不代表一定要占有,不代表零距離時沒有爭執與矛盾,不代表沒有現實的考量。將來,我會慎重考慮職業方向,這是對自我意志的尊重,也是對這份職業的尊重。
我的老師們信奉專業至上。我慶幸自己遇見了這樣一批業界前輩,讓我重新認識了新聞報道、認識了專業精神,最重要的是認識了自己。
四
實習的日子里,我經常一個人快速吃飯、快速干活兒,因為當時這個部門只有我一個實習生。偶爾閑下來,也只是去樓上樓下轉轉,找找在其他部門實習的小伙伴聊聊天兒,算是自娛自樂。
這些伙伴中,我和一個在經濟部實習的女孩走得最近,她也來自蘭州,和我住在同一個群租房里。我們經常一起加班,一起逛街,偶爾還在寢室煮餃子、湯圓吃,臨走時,兩個人還一起去報社附近的餐廳“土豪”了一把。
那時,只要過了晚上9點,我倆一定要一起坐地鐵回崇文門。回去的時候,地鐵站總是很空,空蕩卻不空洞,我們倆會一路東拉西扯,看到地鐵站里漂亮的廣告,也會如孩子般睜圓了眼睛評價一番。
我愛肆無忌憚地笑,她愛微張著嘴,作驚訝和嫌棄狀,將我鄙視一番。
我懷念那樣的日子,充實、溫暖、愉快、自由。
3個月的實習,從冬天到春天,那是萬物生長的季節,我在部門外的大廳坐著,時常覺得有些寂靜。
4月的一天,吃完午飯我想去辦公室看會兒書,那天老師們沒來,辦公室格外冷清。我站在窗戶邊兒往外看,柳絮在地面上鋪了一層,像結了層薄冰,漫天飛舞的“白雪”在晴朗的春日午后帶著慵懶和困意。我那樣站著,看了很久,看滿世界明晃晃的“太陽雪”,看報社不斷開啟又關閉的大門,看立在門口正在說話的年輕保安,看取快遞的人來了又去,看大門外的車水馬龍,感覺這一切如時光軸,軸上是被拉長的實習時光。
那會兒,什么都忘了,腦海里只有一行字:“東四十條海運倉2號。”這真是個充滿故事、飽含詩意的地方。當時我想,如果自己是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就這樣靜觀著,恒久遠,可好?
但我終究還是走了,不知不覺到了實習結束的日子,從實習鑒定表上得知,過去3個月自己參與的作品中有數篇表現不錯,好像,自己還行。
我還要向前走,生活沒那么簡單,我走得也沒那么快,但終歸不能停。然而,經歷了此番實習,此后的行囊里多了些牽掛和一份從心底長出的信心。
謝亞喬,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2級學生,曾于2015年1月至4月在中國青年報社實習。喜歡有溫度的文字,有畫面的小曲兒。喜歡有香氣的米飯,有甜味的豆腐腦。珍惜每一場實習結束,離去無期后寫總結的感覺。相信打不死的“小強”有走不完的路,止不住的成長有說不盡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