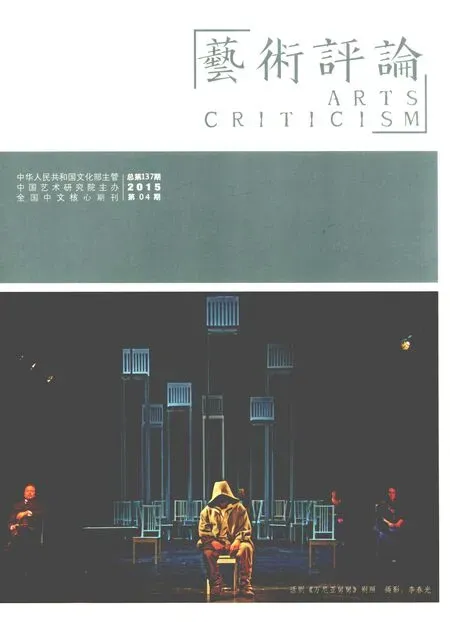期待視域與作品間性
——從海外華人畫家林禹光作品看中國藝術(shù)文化的全球化
程 原
期待視域與作品間性
——從海外華人畫家林禹光作品看中國藝術(shù)文化的全球化
程 原
有多少顯現(xiàn),就有多少存在;還原越多,給予就越多[1]——在此意義上,可以肯定地說,作為幾代前輩藝術(shù)家篳路藍縷、與時俱進心路歷程的一個縮影,年逾古稀的新西蘭藝術(shù)家林禹光先生的作品創(chuàng)作,一直以來不僅是中紐畫界許多人士“期待視域”中的一個關(guān)注對象,而且,其跨界人生之所作所為,也始終由其自身不斷推衍的“期待視域”所同構(gòu)。
我們知道,從動力論角度講,解釋學所言的“期待視域”[2],也可謂是人所特有的從低向高、自內(nèi)而外求真向善主客協(xié)同的存在訴求。當然,哲學水平上,作為人生意義的顯豁,這種“存在”非比尋常。如在現(xiàn)象學家眼里,人生在世是謂“此在”,而人之為人的理想性“存在”,則因大量“此在”的功利勞碌役使而被“沉淪”,被“遮蔽”[3]。這樣,消除迷失,尋求“本真的存在”,就不僅是歷史的一個除魅的過程,同時更是個體人生不可逆的一番祛蔽的歷險。就此而言,了解林禹光才翹弱冠、在油畫粉畫連環(huán)畫等畫種曾多有成就的人都知道,作為國民黨前中將子嗣的他——其人生確實更比常人多了一層“被拋”人世的“煩”[4]。可以說,總是望天下于大同之生愿、且又總是落入歷史之夾縫,使得有尊嚴的存在之于不斷期待的別處,就不僅根本構(gòu)成了他此在之身與士子之心跌宕起伏的悲憫視野和情懷,同時,也成就了其畫作題材選擇、色彩嬗變和語法遷移的魂靈。
不提其為生存而造就的俄式畫功之扎實,也按下他被館藏和被定制的許多歷史題材之巨制,就禹光先生近二十年的風景畫作看,從1994年前后在紐約完成具象表現(xiàn)主義的語式轉(zhuǎn)型,到兼收并蓄、于本世紀初相向紐國與故土的雙重本地化的糾結(jié),再到紛華落盡的荒寒料峭與蒼茫,直至當下綠色紛繁的忘情揮灑與無持——其軌跡,昭然顯現(xiàn)了他在主客關(guān)系和語言方式上的位移。必須說,作為早年曾有中國寫意功底的老油畫家,他基于對后印象與野獸派運筆恣暢的表現(xiàn)性語言的吐納,對安塞姆 · 基弗肌理奧、意緒繁復(fù)的“新表現(xiàn)”技法的淘取,乃至對國際新潮美術(shù)中的一些意氣直書元素的蒸餾,2006年至今,雖其畫作也有曠兮若谷、天地不仁般的審美隱喻和中立,但感同身受于民生之比照,則使其無論在精神意象上,還是在技術(shù)托諭上,主要還是在婉別西方現(xiàn)代派的同時,以飽含追索的站位,意緒深長的詠喚,不僅合力攀援了中國傳統(tǒng)人文所乞靈的那種山水境界,而且,還傾聚現(xiàn)實情懷,以擘面驚人的高質(zhì)高產(chǎn),力逾“去欲養(yǎng)德、抒己野逸”之窠臼。可以說,無論是其數(shù)十幅溝壑盤結(jié)、雪色不語的《北方系列》,還是暗月山色、夢牽魂繞之《意象》,抑或是天地邈遠、靡霾空的《有霧的風》等組畫,均在魏風晉骨隱然中,以貌似莊老般的似即非離的超然瞰望與觀照,實置世風人天于大辯不言的敞顯中——固然,其意形兼得雖完合中國藝術(shù)法理,但循其棄本位主義媒介觀及超二分法思維看,又的確在作品文化間性意義上彰顯了藝術(shù)世界的開放性。

林禹光 2013年 風景 布面綜合材料115×96cm

林禹光 2014年 原生態(tài)(金錢豹系列)布面綜合材料 160×130cm
有必要說明,這里所謂的“文化間性”,不僅“上指”張大千、趙無極等屈指可數(shù)的一代,同時更指“目光向下”到當下林禹光一代海外華人藝術(shù)家們的作品所共有的中國人文精神的國際化品質(zhì)和特征。固然,集合有多種當代學術(shù)觀點的“間性理論”中的文化間性,由于以中外“主體間性”哲學思想為基礎(chǔ),從而也一般地涵蓋了人與人、人與文化、文化與文化等事物間不可回避的互動“關(guān)系”和普遍聯(lián)系[5]。那么就間性論基本觀點而言,正像紀伯倫《大地之神》所隱喻生命自我的神性(god-self)、人性(man)、半人性(pigmy-self)的共在那樣[6],特別是就人類文化“人天和合”、藝術(shù)創(chuàng)造“心物同構(gòu)”等大量間性現(xiàn)象與史實看,筆者更愿借助脫胎于我國古代《我儂詞》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熟語,來說明人類藝術(shù)與文化生存中關(guān)系的多面性和內(nèi)生性。因為,正如人類學者羅伯特·F·墨菲所言,“只有當人進入文化中,才能真正成為社會個體”的存在[7],而文化的歸根結(jié)底面,又總歸落實在人的存在關(guān)系和生活方式上來。故而,這里所謂的“文化間性”,既與人類當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生存間性”一幣兩面,同時也是“地球村”歷史觀的現(xiàn)實寫照。循此,對于日益依存的開放性村落和越來越多頻往于不同文化圈交流的人們來說,由生存間性反映到藝術(shù)形式和文化形態(tài)上的“文本間性”、“作品間性”,就可謂是既反映了從藝術(shù)家到受眾所對作品主體間性的客觀訴求,同時更反映出跨界生存對不同文化的全球化分享的歷史趨勢。
然而,即令如此,單就林禹光個人創(chuàng)作而言,其有待的本真的表達卻仍是難的。謂其難,難就難在到哪里尋找真在的前提,是謂難中之難。千回百轉(zhuǎn),在筆者看來,對此問題,古今中外也許只有一個去處,那就是“暫存世界”。從國學觀點講,現(xiàn)當代美學家們所謂之的“動態(tài)統(tǒng)一”、“視域融合”意義上的“暫存世界”[8],大方無隅頗為似“道”,且恍兮惚兮動變不居,既因人因地因時而異,又常被“熟視無睹”自匿。比附事像,這就像大地震蕩地殼開合的那一瞬,又如同曇花一現(xiàn)的那一刻,隱匿的真相與真在,既如被臨淵之人赫然目貫,又似被參禪不夜者了然神會。從而,既可謂是一次“本真”之“逮獲”,又可謂是一種“還原”之“揭顯”。不惟如此,雖此生情世相,倏爾即彌貴于曇花,且可遇難求不可復(fù)制被曰“暫存”,然此暫存,卻恰是“真相”之襁褓,“永生”之前提。換言之,真正的藝術(shù)實現(xiàn)也蓋莫能左:每每創(chuàng)作死尋活覓“驚”于驀然回首時;次次品鑒凝神屏息“訝”于心有靈犀間——發(fā)展創(chuàng)新無不成全于這看似飄忽、但卻意蘊雋永的“暫存”中。
當然,還需看到,在建構(gòu)論層面,逮獲、永存這生之真意的一刻,卻并不比本體論指向簡單。因為,即便是在接受美學謂之的“期待水平”意義上,從創(chuàng)作到二次創(chuàng)作之接受,抑或變“本文”為“作品”,整個過程,幾乎又都不可避免地已然存在著諸多前在性規(guī)定——畫家自覺不自覺地依憑這樣那樣的前語言、前觀念來創(chuàng)作,受眾則憑借這般那般的前經(jīng)驗、前意識來吐納。其間雖然“期待”無所不在,但是,也正是這些甚或挾裹著種種前在指向性的庸常習見和能量,卻又總是構(gòu)成了對本真的遮蔽和永生的反動。以至于,每次創(chuàng)作都內(nèi)外挑戰(zhàn)、舉步維艱,恰如“上帝在荒野中”,但“荒野的敵人無所不在”[9]。
可見,期待也悖論。那么,又怎樣找到藝術(shù)生命之真在呢?縱覽中外,古往今來,通往羅馬的廣衢與阡陌,也許盡可謂是殊途同歸。方法論上,作為對期待的否定之否定,似惟有“在者”個人所對“在世”的詩性乞靈和超越:放下“不知生焉知死”刻意“事功”之偏執(zhí),走向無持、無待之解放,得沐“此在就在真理中”之澄明[10]。其門徑,用詩性話語講,就是“先行到死”中去,才是向死而生的自由路[11]。在“經(jīng)由死亡達成神性”的意義上[12],此雖類如西人勸往天國的“窄門”,抑或大乘祈愿的“涅”,但卻更如知死樂生的“酒神”路,萬生根源的“玄牝”門。由之,篳路藍縷也好,心騖八極也罷,總歸要懸置掛礙以得天惠。就此而言,禹光先生眼下多媒材綜繪之取向,既與國際新表現(xiàn)主義有邂逅,更融匯中國人文精神于當下,讓人頓覺有進。就其作品形態(tài)的上下文看,這不僅表現(xiàn)在他以自由酣暢的筆法,徹底揮別那種幾被時下追捧、貌似真人高士所對世界的遁身觀上,同時更表現(xiàn)在他自于真見且綠意紛迷的生態(tài)象征上。易言之,他將中西資源化為內(nèi)生性力量,并以內(nèi)斂的歷史感和當下性的統(tǒng)一,不僅與時下一般風景畫卓然相別,而且,在興觀群怨品質(zhì)上,也達到了堪與其歷史畫媲美的高度。正可謂冬去春來,澡雪顯真,不牽不掛盡在生情本色。在這里,無論是飛白潑灑,還是淌滲留白,天地人我主體交互、人神遇合。在環(huán)球同此涼熱的“去圣化”返我歸真中,其人其作,則不其然而然地以自身個性方式的文化間性,自主走向了當代跨語境共享的“作品間性”。
綜其軌跡不難看到,林禹光先生正在建構(gòu)以作品為中介的主體交互與動態(tài)統(tǒng)一之維。借表演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驗論”來比擬,其對世象的表現(xiàn),首先即為創(chuàng)作者與創(chuàng)作對象的主體互入與互化。其間,無論是形色還是象意,實為文化互動與共在;其次,鑒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不確定性”,在創(chuàng)作與接受關(guān)系上,他不覺也照應(yīng)了接受論先驅(qū)著名的“空白說”[13],抑或是“不定點”論[14],以看似“缺位”實為“互在”的深蘊,將不同主體請席于當下,借此同構(gòu)藝術(shù)無界之盛宴——而這也正是其“作品間性”在國際展事上既得公益口碑與拍點,又得藏家追蹤和求售,同時更得中國機構(gòu)不斷簽約的一個內(nèi)在肌理和根因。
最后必須強調(diào)的是,站在視域融合高度,且對應(yīng)還原越多,給予就越多之期待,這一盛宴,似在動態(tài)號準生之命脈追求中,既要寓加于減再提煉,也需布萊希特“間離方法”來助益。及至在火熱融入且不忘身,似曾相識又出人意料的新特視距中,以中國人文恢弘博大的“天下”觀和“水火交融”之特行,進一步推倒各種橫亙現(xiàn)實的“第四墻”[15]——使得藝術(shù)自治與通律、文化間性與互約,能在“共識”之于“陌生”、“個人期待”之于“公共期待”等大道獨行的辯證中,不斷走向無蔽的綻放、本真的共享和藝術(shù)的永生——應(yīng)該說,這恰恰就是以林禹光現(xiàn)象為表征的當代海外華人藝術(shù)家們對中國藝術(shù)文化的全球化正在不斷開拓著的一個既不應(yīng)忽視、也不可低估的重要的價值路向。
注釋:
[1]M·亨利.現(xiàn)象學的四條原理[M].王炳文譯.哲學譯叢.1993.1、2.
[2][13][14]也稱“期待視野”.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M].周寧、金元浦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30、377.
[3][4][11]海德格爾.真理與方法[M].陳嘉映、王慶節(jié)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7.219、213、316.
[5]程原.藝術(shù)中介間性觀:當代藝術(shù)文化與藝術(shù)文化學研究[M].河南大學學報.2013.4.
[6][12]馬征.文化間性視野中的紀伯倫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226、219.
[7]羅伯特·F·墨菲.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導論[M].王卓君等譯.商務(wù)印書館.1994.序頁.
[8]海德格爾的“動態(tài)統(tǒng)一”即“暫存世界”;亦為伽達默爾、姚斯“期待視域”與“視野/水平融合”。參見:伽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M].薛華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98.
[9]出自CCTV9播出的“美國國家公園全紀錄”約翰·繆爾語錄解說。
[10]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M].郜元寶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7.
[15]貝·布萊希特.布萊希特論戲劇[M].丁揚忠、張黎等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181.
程 原:集美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陳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