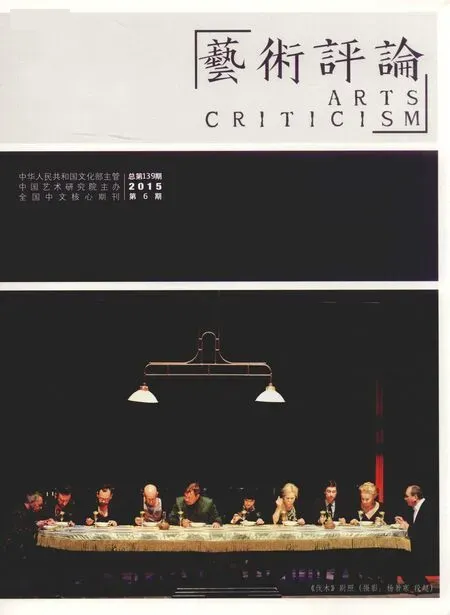“道”“器”關(guān)系的變化對宋代鈞瓷器物形制的影響
李維維
“道”“器”關(guān)系的變化對宋代鈞瓷器物形制的影響
李維維
宋代理學(xué)的興起,改變了先秦以來傳統(tǒng)的“道”“器”關(guān)系。先秦的儒家并沒有像宋代理學(xué)這樣,從本體論的角度提出“理”“氣”關(guān)系解釋世界萬物萬事的生成,孔子在以“仁”為中心的論著里講述的是具體做什么,而非是什么與怎么形成。在《周易》中道器關(guān)系未曾涉及,反倒是道家思想中有道器之辯的訴說,老子的“道”生天地萬物說,極大地強調(diào)了“道”的作用,而將“器”放到次要地位。但老子的“道”基本上講的是客觀規(guī)律,沒有像理學(xué)家這樣,附會了許多人格化的主宰一切的內(nèi)容。
一
既然“理”的地位在理學(xué)家看來如此重要,那么“窮其理”就成為了重要使命。這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與“致知”都是“窮其理”的手段。在二程看來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間,皆是理。”“格,至也,謂窮至物理也。”“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由曰窮齊理而已也。”“物,猶事也。凡事上窮其理,則無不通。”[1]在朱熹看來,窮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達(dá)至極。“格,至也。物,猶事也。窮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也。是以《大學(xué)》始教,必使學(xué)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2]這里的“格物致知”具有認(rèn)知的意義,有探索天下萬物即客觀世界真理的意思。但是朱熹又說:“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后之序,豈遽以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xué)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xué)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3]可見格物不能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間,而須先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才是致知的正道。杭間對此的評論是:“這種重道輕器的思想,實際上把任何技藝的發(fā)展,都看做是微不足道的末技,這不但損害了工藝美術(shù)的發(fā)展,也阻礙了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4]。重道輕器、重理抑情體現(xiàn)在審美趣味上,形成了保守的、理性的,謹(jǐn)嚴(yán)溫潤的含蓄風(fēng)格。
二
具體到宋代鈞瓷上,是輕紋飾而重釉飾。紋飾有刻、劃、印、貼、剔花等多種技法,具有很強的人工刻意的雕琢痕跡,宋以前的唐代,紋飾特征已經(jīng)是構(gòu)圖復(fù)雜、紋飾精工。在對宋代鈞瓷的研究中,無論是官窯所出還是民窯所出,都不以任何奪目的紋樣為主,紋飾融于器型中,簡練的器型大面積留于釉色的展示,這不得不令人思考。理學(xué)的“輕器”,關(guān)注“器”作為“用”的功能性,漠視“器”作為文化的物質(zhì)載體的審美性,認(rèn)為“器”是“淫巧”、“小技”,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工藝美術(shù)的發(fā)展。當(dāng)然,我們必須明確的是,宋鈞從唐代花釉瓷發(fā)展而來,它對中國陶瓷史乃至世界陶瓷史的貢獻(xiàn),是它對銅紅釉的創(chuàng)燒打破了我國瓷器固有的南青北白的格局,它的窯變釉的裝飾是區(qū)別于其他瓷種的最顯著特征。理學(xué)害技藝,但理學(xué)也成就了燦爛的鈞瓷藝術(shù)。造型和色彩是造型藝術(shù)中兩大因素,圖1:為北宋年間燒制的“鈞窯玫瑰紫釉鼓釘三足花盆托”,從造型上看,花盆托敞口,淺弧腹,平底,足部承以三個如意頭形足。口沿下和近底處各環(huán)列鼓釘紋一周,上面一周二十一枚,其下凸起弦紋一道;接近足部的下面一周十八枚。器身紋飾除了鼓釘凸起和弦線凸起,就只有亦足亦飾的如意頭。紋飾完全為了功能服務(wù),土與泥的摶埴取代了唐代的金銀器,抽象化的裝飾取代了唐代的忍冬紋、蓮花紋。符號化、幾何化的紋飾,以點、線的形式存在于開闊的釉面之上,以線條的構(gòu)成與打散為主要旋律,向?qū)徝勒邆鬟_(dá)出了節(jié)奏與韻律的形式美感;從色彩上看,器物通體施滿釉,形體內(nèi)外皆被釉料覆蓋,外壁為天藍(lán)釉和玫瑰紫釉相交融的窯變釉。鼓釘處釉垂釉明顯,邊、棱處釉呈醬色。內(nèi)壁以天藍(lán)釉為主要色調(diào),間有紫紅釉,內(nèi)底部有明顯蚯蚓走泥紋。蚯蚓走泥紋是由于窯火的熔融致使鈞窯瓷器釉面自然形成多種形態(tài)的彌合紋路,妙趣橫生,俗稱“蚯蚓走泥紋”,如同雨后蚯蚓在濕地上留下的紋路,亦為宋代鈞窯瓷器釉面的特色之一,為自然而然的窯變結(jié)果。天藍(lán)與玫瑰紫釉的冷冽與清淡也一改盛唐時器物色彩華麗到痛快淋漓的美妙奇異。那種“蘭陵美酒郁金香、玉 盛來琥珀光”的瑰麗已不復(fù)存在,轉(zhuǎn)而是寂靜清淡的理性之姿。綜觀這件花托,玫瑰紫釉在色彩冷暖上作為暖色調(diào),巧妙的包含于天藍(lán)色的冷色調(diào)中,色彩的濃淡使瓷器自身形成了一個肌理疏密的關(guān)系,釉面色彩的豐富,缺少紋飾的宋代鈞瓷使審美者在觀賞時,更能注重內(nèi)心的審美感受。
三
并非官鈞如此,民鈞也一樣。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的民窯鈞瓷中,雖然制作工藝的精良程度不如官鈞,但是審美趣味是一致的。如圖2、圖3中的北宋年間鈞窯月白釉紫紅斑碗,上寬下窄,斂口、口沿處內(nèi)收,口沿下的碗壁上環(huán)繞一周突棱,凸棱可見胎體,弧形碗壁線條流暢,圈足,器型極為規(guī)整,法度嚴(yán)謹(jǐn)。通體飾以月白釉紫紅斑,足部露胎無釉。碗沿以下的凸棱,清晰可見胎體,證明此處施釉較薄,加上碗的足部未施釉,這些都是民窯區(qū)分官窯的地方,民窯在做工上往往并不苛刻,老百姓的日用品還是有別于宮廷用具和官府訂單的,在上面提到的盆托中,我們知道,官鈞都是施滿釉,即器皿的內(nèi)壁外壁、足部等全身施釉,而民鈞并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工藝要求的高低并不影響民鈞和官鈞審美品位的一致。在月白釉紫紅斑碗的內(nèi)底部分,有窯變生成的紫紅色斑,與整體的月白釉色形成了對比,如“雨破天青云破處”,青中泛紅、寓紅于青。
審美興味和美的理想是歷史行徑、社會變異的間接而曲折的反映。與現(xiàn)實相適應(yīng)的哲學(xué)思潮,是形成審美趣味的主觀因素。隨著士大夫官僚政治的形成,庶族地主心理狀況和審美趣味的變異,就鈞瓷的審美來說,它更真實的感受到了,并反映出了這些變化。它由唐代花釉瓷發(fā)展而來,進(jìn)入宋代才真正成熟,并且達(dá)到鼎峰。它的長足發(fā)展,說明了它的藝術(shù)風(fēng)格與宋代理學(xué)以主體的理智省思為主的內(nèi)向性思維路線的要求是相契合的,是極為符合當(dāng)時社會整體的審美風(fēng)尚的。所以可以說,“道”“器”關(guān)系的改變,最終最大程度的改變了器物的風(fēng)貌。
* 本文為2014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禪宗時間美學(xué)研究——以日常生活藝術(shù)表現(xiàn)為例”研究項目。項目編號:14YJC760046。
注釋:
[1](宋)程顥、程頤著:《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
[2](宋)朱熹著:《大學(xué)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83. [3](宋)朱熹著:《朱文公文集》卷三.
[4]杭間著.中國工藝美學(xué)史[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7:102.
李維維:武漢大學(xué)哲學(xué)學(xué)院美學(xué)專業(yè)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