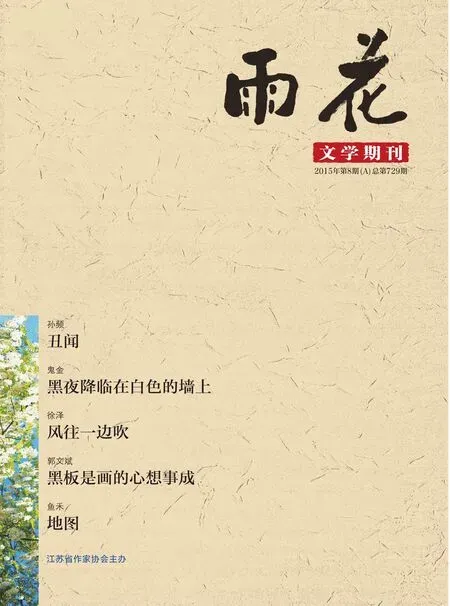閱讀札記:尋找河的第三條岸
■郭 艷
閱讀札記:尋找河的第三條岸
■郭 艷
《雨花》,據東南之要津,納金陵之瑞氣,成文學之重鎮,聚士林之妙文。魯院諸俊彥,吟詠方塊漢字,情動綴文;吐納珠玉之聲,卷舒文壇風云。期文思千載,辭章日月,輝映萬眾。噫!情如雨,滋潤心田;文競花,吐香爭艷。雨花非花育花,花雨如雨勝雨,孰言不感天下哉!是為序言。
—李一鳴
本期《雨花》集中了中國多個地域作者的文本寫作,西北地區的甘肅、新疆,中原地區的河南、山東,東北部的遼寧,東南部的江蘇等地。盡管作者群落從地域上來講可謂輻射全國,但是隨中國社會城市化進程,社會生活在呈現多層級、多方位差異性的同時,整體精神風貌和心理特征卻表現出相當大的同質性。同質化傾向是現代社會的發展模式,資本的全球化帶來現代日常生存經驗的機械復制和單向度,文學經驗表達也趨于日常性的陳腐和平庸。本期作品涉及城市與鄉土,鄉村教育與少年成長,體制與個體生活,身體欲望與庸常生存……寫作呈現出個體精神狀態的迷惘,整體文學生態的蕪雜。
李學輝《獨唱》和楊鳳喜《π》都指向了當下鄉村教育的現實問題,小說暗含著這樣的憂慮:鄉土的衰敗從農村教育的凋敝開始。相對于上個世紀鄉村教育題材的理想主義和啟蒙色彩,當下鄉村教育問題無疑凸顯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整體坍塌的荒涼與頹敗。這種坍塌不僅相對于前現代語境中的皇權專制,也解構了1950年代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之初的革命理想主義,同時一并結束了1980年代思想啟蒙和人道主義對于鄉土遠距離的觀照。《獨唱》中塑造了一個堅守者二叔的形象,他無疑是新中國民族國家鄉村教育的奠基者和啟蒙者。二叔在新的經濟文化語境中的尷尬和怒氣,其原因在于,當下鄉村教育的形式主義消解了理想主義的人文情懷,更為致命的是沒有了可以啟蒙的對象,二叔在新的倫理價值體系面前顯示出不合時宜的寒肅。然而,守望者的背影依然讓我們遙想:二叔從敬惜紙字、詩禮傳家的鄉土社會中出走,作為革命者的二叔在紅色革命隊伍中立正轉身,以新中國教育者的身份重新回歸鄉土社會及其精神生態,但是五十年之后,二叔面對高聳的現代化教學樓和寥落的學生們,他只能是一個失語的獨唱者。由此,鄉土社會在精神上的凋零和寥落已然無可挽回。在一個降低人倫精神底線的時代,獨唱在不合時宜中顯示出西西弗斯式的悲壯,獨唱是堅守者的姿態。李學輝秉持正心誠意的啟蒙意識出入于文本內外,有著一股剛正純陽之氣。同時,面對經歷多次政治經濟轉型的中國社會,物質主義“進步”所賦予的啟蒙和開化功用也會以某種方式與傳統鄉土對接,從而讓凋敝的鄉土文化與現代文明有著異質嫁接的新生希望。1950年代革命理想主義和1980啟蒙主義都是從主流意識形態角度去改造鄉土及其倫理價值體系,而從1990年代開始,物質主義和商品經濟情境中,中國社會終于有可能從個體生存的角度賦予農村個體更多的文化和文明選擇,作家的可能性在于用多視角呈現這種選擇的掙扎與艱難,文學的虛構性體現在對現實最大限度的復調敘事,從而透視一個時代的風俗史與精神史。《π》則進入鄉村教育的內部,通過一個小學生的視角,描述了偶然事件對于男孩明亮身心成長的影響。鄉村教育在明亮身上的失敗,不僅僅是無法升入中學,更多是一種無法擺脫鄉土生存方式的無奈。隨著教育資源在城市的日益集中,明亮們的故事會一直演繹下去。小說設計了一個“π”意象,盡管故事結構和意象頗具現代派小說的筆法,然而在對于鄉村教育和人性深度的把握上,無疑又顯示出某種俗套。文學的想象力應該在此出場,以小說的形式去照亮生存最幽暗或最柔軟的真實。鬼金《黑夜降臨在白色的墻上》中彌散著一種城市病的黯淡氣息,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疾病都在侵蝕著林靜萍。生活的真相面目猙獰,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死亡是永恒的黑夜,然而卻時時在白晝閃現。鬼金小說敘事平滑老道,女主人公與生活和命運抗爭,行走在一個個病人之中,盡管心情暗淡,卻能夠不懈地直面慘淡人生。對于鬼金來說,重要的不是敘事,而是對于敘事后面意義的尋找和發現。林靜萍依附在故事情節之上,依然沒有發展成為一個自足的文學人物,而作家的建構性無疑體現在對于人物文學性的高度自覺。《凍結》以樸素的筆觸描寫體制對于普通老百姓的規約,這種規約在內地可能會日漸被商品經濟解構,而在日常生活更為艱難的西北地域,體制依然以無比堅硬的面目出現在小人物的日常生存中。安慶《來蘇水的方向》以小說的方式重述了中國當下無數個已經或正在上演的真實故事,左輪兄弟的發家和沒落史因沾染時代的腐敗病癥而具有某種現實針對性。小說又在同步摹寫的現實生活中,遮蔽了對于具象生活更為隱秘的私人精神史的呈現。面對具有強烈戲劇性的現實,作家應極為警惕,現實的戲劇性提供給讀者的無疑是最為表象的判斷,而作家的洞察在于海水之下的巨大冰山。
當下小說寫作在一個平滑的表面上潛行,寫作者游蕩在自我、社會與他者的生存狀態中,更多現實層面直觀的敘寫與表達。平滑表面的行走盡管沒有難度,卻依然很危險。同質經驗無限重復的寫作很輕易就會被蕪雜的文字所覆蓋。小說所具有的詩意魅性,依然在于虛構性、想象性和創造性膠合得圓融無礙,寫作是在河流第三條岸上尋覓出口。
本期的散文寫作更具個人才性。魚禾《地圖》中那種揮灑自如的文字氣度,一如將軍面對沙盤的運籌帷幄,線性文字騰挪跳動在山川丘壑之間,歷史與當下在流動的敘述中抵達蘊藉的詩意。遠方意味著陌生化的審美,葛芳以一己之鏡像去敘述博爾赫斯及其城市、花園,漫步在異域文化中的自我呈飛翔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