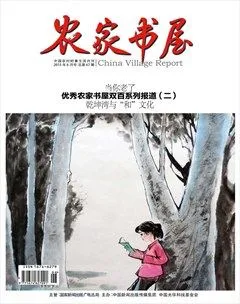張老爺子的人情、交往與手藝
一
張老爺子是中梨樹溝村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發生的故事里,鐫刻著城鎮化進程的足跡。這是兩年前的事情。老張家剛剛住進了新房,又要娶媳婦了!娶媳婦是要操辦的,這種操辦在城里叫婚禮,而在中梨樹溝村還是沿襲著過去的叫法,叫做“辦事兒”。
“辦事兒”的人家當然充滿了喜慶,菜香、飯香和酒香飄灑在院里院外,親朋好友們談笑風生,男男女女不時傳來嘰嘰嘎嘎的逗鬧聲、插科打諢聲和打情罵俏聲。而這樣的氣氛卻沒讓張老爺子興奮起來,張老爺子今年70開外,是新郎官的爺爺。張老爺子在想什么呢?
原來,辦事兒是需要一套人馬的,這套人馬包括知客(城里人說的司儀或主持人),廚房飯房燒火的、劈柴的、供水的、送酒的、洗碗的,還要包括比較尊貴一點的賬房先生。這套人馬加起來不下30人,而每個人都要索取報酬——知客每人200元,外加一箱白酒;賬房每人100元;廚房、飯房按照宴席開多少桌來計算,每桌收取勞務費100元;那些雜役們每人也至少給付100元。
張老爺子算了算,這場事下來,光人員雇傭費就得3000多塊!
在張老爺子的記憶中,這筆費用在城鎮化之前是不存在的,即使付費,也沒有現在這樣明碼實價。過去在村子里,紅白喜事的服務人員都是人情的互換,你幫我,我再幫你,誰提個錢字,就顯得淺薄沒有人情味了……
張老爺子由此聯想到自家剛剛蓋起的新房,光包工費就花掉一萬多塊!而在過去的農村,蓋房搭屋也是靠鄰里鄉親幫工來完成的,而幫工只是供飯不給報酬,因為村人之間相互幫工是友誼與情面的體現。“咳,這些光景都過去了,現在的人啊,不需要人情了!”張老爺子坐下來抽了一袋煙,然后把頭搖了搖,表現出太多的無奈與思索。
張老爺子的孫子深知爺爺的思慮與擔憂,就貼近爺爺的耳朵說:“爺爺你放心,這點費用不算啥,我在單位跑供銷,每個月的工資不算,光獎金就有兩萬多塊!” 張老爺子的孫子原來在城里一家建筑公司打工,由于工作出色人又精明,現在給公司跑供銷。
“兩萬多塊?”爺爺的眼睛睜大了,他輕聲說道,“人情變薄了,收入倒增多了?”
張老爺子百思不得其解,他沒有辦法把這一對悖論想成必然。這是因為,他所理解的人情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人情,而是村落文化層面的人情,是農業文化積淀的人情。人情是要與時俱進的,群居的原始人產生一種人情,落后的村居也產生一種人情,而這些人情已經在城鎮化的進程中發生了蛻變。
社會活動的商業化正是城鎮化進程帶給鄉村的蛻變法寶。農民工穿梭往返于城鄉之間,是鄉村融入城市的催化劑。在這種催化過程中,城里人怎么做的,怎么想的,怎么盤算的,村里人看在眼里,記在心上,于是,那種村落文化中的人情就慢慢消解了,代之而來的是那種重個性、重實效、重利益、重選擇、重競爭的文化意識。
二
張老爺子的孫子已經在城里購置了樓房,新婚小兩口都在城里上班。為了盡一點孝道,孫子要接爺爺到城里住些日子。
“爺爺在農村辛苦了一輩子,現在日子好過了,不愁吃不愁穿,您老人家也該到城里享受幾天了!爺爺您只要能來,您吃什么我就給您買什么,您想到哪去溜達,我就領您到哪去溜達。”在孫子的誠信邀請下,張老爺子真的來到孫子家。
每天好吃好喝伺候著,公園廣場溜達著,可是沒過幾天,張老爺子突然變卦說要回家。問為什么呀,張老爺子答“什么都不為,我就是沒處串門去了!”
仔細想城里的居住就是這樣啊,一家一戶各自為“籠”,住在對門都不知道誰家姓什么。而農村的情況卻截然不同,張老爺子的最大愛好就是到鄰居家去串門,而農村人也以有人串門為榮耀,如果這戶人家一年到頭連個串門的都沒有,那就說明你的人情太“死性”,太不好客了。
串門的時候,主人要給客人點煙、倒茶、拿瓜子,有的人家還要拿出水果來款待。大家叼著煙卷吞云吐霧中,能夠暢談各自心里最為關心的人和事。大家喝著茶水嗑著瓜子,能把一些最為隱秘的心里話倒出來。
這種串門聊天,對于鄉下人來講是不可或缺的精神保健,也是不可或缺的心靈雞湯。可是在城里,你到哪里去串門聊天啊,也難怪張老爺子呆不下去了。
城鎮化程度越高,人們的社會交往就會越加寬泛。也就是說,人交往的社會面越大,交往的深度就會被不斷削弱。張老爺子住在鄉下,他所認識的人無非是界毗鄰右這樣有限的幾個人,張老爺子的串門聊天也一定會由頻繁轉入深化,表現出極強的封閉性與恒定性。
而城里人就不行了,城里人要廣泛接觸社會的各個層面,而各個層面又有著極大的流動性,鄉下人每天只能遇到那么幾個鄉里鄉親,而城里人每天要面對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人們相遇匆匆,離去匆匆,因此只能保持淺層的短暫的關系,以此來維持足夠的心理能量,來應對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如果城里人也和鄉下人那樣一生只接觸幾個人,這樣交往的深度倒是有了,他又如何應對瞬息萬變的生活節奏呢?
在終極意義上說,人的血緣觀念、親朋觀念、情感觀念、責任觀念乃至道義觀念當然不可或缺,或者說這些都是人之為人的必備條件,但這不等于每個人每天都要去經營這些觀念,更不等于把這些觀念當做畢生的事業來做。鄉下人由于地域閉塞,交往面狹小,閑暇時間過多又無所事事,于是就把大量的心理能量揮灑在交往上面,于是就專講某某人仗義,某某人實在,某某人有血性,某某人夠交情.實際上,在有所作為與事業成功的角度看,鄉下人的深度交往是人生的歧途,是耗費大量心理能量與生命膏脂的“鋪張浪費”,更是終生貧困的迷魂湯。
在一般意義上說來,人生價值的最后衡量還是一個人的事業成功率與對社會的付出值,每個人的道德元素與義氣元素都是品格里面的一種含量,然而人的品格不等于成功,道義也不等于成功,那么成功是什么呢?成功里面必不可少的因素是人的勞動與奉獻。
三
故事講到這里,我們有必要全面認識一下張老爺子。張老爺子今年七十有一,身板硬朗,精神矍鑠。在我居住的村子里,張老爺子是遠近聞名的“十八般武藝”,為什么說他是“十八般武藝”呢?原來,張老爺子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逐步研習精通了這些技能——他是遠近聞名的豆腐匠,他做的大豆腐干豆腐味道醇正,塊大量足,他還是手藝精湛的木匠、瓦匠、獸醫,他精通養蜂技術、精通獸醫、善于劁騸、懂得電工原理、精通棗樹技術,同時還是一個種莊稼的好把式……總之,有人給他統計過,他掌握的技藝真的不下18種。
然而就是這些手藝技藝也沒能使他實現發家致富的夢想。老人家在年輕的時候雖然終年勞作,疲于奔命,可就是掙不來多少錢,家里的生活總是緊緊巴巴。兒子大了,境況有所改觀,孫子進城務工后,才甩掉了貧困戶的帽子。
有人說他是藝多不養家,有人說他天生的受窮命。無論如何吧,張老爺子在鄉下的所有技能都不能把他從貧困線上挽救出來。從孫子家里回來之后,他還是繼續著那種串門嘮嗑的優哉游哉的田園生活,直到兩年前的冬天,他城里的閨女把他接去開了一家豆腐坊,他才真正嘗到了掙錢的滋味。
那個豆腐坊是一個豆腐加工廠,流水線作業,張老爺子技術指導,每月的工資是1.5萬元,年終還要參加分紅。憑借他精湛的技藝和旺盛的體能,僅僅二年時間,這老爺子就發了!
今年清明節,我看到了回鄉祭祖的張老爺子。只見他精神抖擻,紅光滿面,我就問他現在適應城里生活了嗎?他笑了笑說,“別提了,我的這些手藝要是早些找到這個用武之地,咱爺們早就妥了!”
張老爺子雖然能做豆腐掙錢,但為什么在城里掙錢在鄉下就不掙錢,這個深層原因他還是說不清楚。我告訴他,城鎮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生產分工十分發達,發達的原因是講求實效,是強烈的功利性特征。就是說,城里人精通什么技藝的目的是講求效益,不是興趣,不是徒有虛名,更不是博得人家的稱贊。
張老爺子說:“你算是說到點子上了。我年輕的時候喜歡名聲,人家夸我兩句心靈手巧仁義仗義,我給人家做點木匠活、瓦匠活啥的就不要錢了,頂多混個吃喝也就心滿意足了。怪不得農村長期落后,原來是這回事!”
“這回事”在他腦海里還是一個模糊概念。他說的“這回事”是什么意思呢?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文化形態長期居于主導地位。而農業文化的滋養則是儒家的“禮義廉恥”和“溫良恭儉讓”。這些品質在身心修養上是優秀的、可取的,在社會競爭和講求實效上卻無法成為動力。因此,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我們的重要資源,但不能代替我們的現代創造。
看著張老爺子的背影,我似乎看見了一個村落生態的蛻變與生機。歷史的進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蛻變的進程,只有蛻變才會出現生機:樹的傷口因流汁才成就了堅硬的疤;鳥兒因不斷地試飛才實現了高飛的夢;大地因無數次的火山冰期才刻畫出壯麗山川;蟲兒在繭中痛苦掙扎才能羽化成蝶……
破繭,是一種必然;化蝶,是一種飛躍;而蛻變呢,盡管痛苦但勢在必行。農村城鎮化其實就是村落文化破繭化蝶的過程,終年勞作含辛茹苦的農民兄弟們,大家不要錯過了這個正在發生蛻變的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