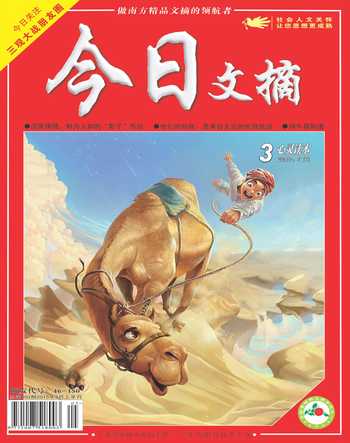不要命的科學家
科學家不僅是一群高智商的人,同時也是一群不要命的人。
一
1813年,一個叫伯蘭特的化學家,發現木炭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但他的發現受到科學界的質疑,伯蘭特為了證明他的發現,鋌而走險——在法國科學院的眾人面前,吞下了10倍致死劑量的馬錢子堿(加了木炭的)。結果他痛苦地在地上滾來滾去。大家目瞪口呆,卻什么也無法做。幸運的是,他挺過來了。現在木炭用于解堿系毒物以及廣泛地用于防毒面具。
二
菲爾德醫生覺得硝化甘油(也就是炸藥的一種成分)對于神經和心臟有幫助。1858年,他嘗試喝了一點硝化甘油,結果立刻臉色發白,癱倒在地,感覺腦子要爆炸了,脈搏越來越弱,所幸,最終他挺過來了。后來莫雷爾接過班,在嘗試了40多次服用硝化甘油之后,他成功地發現硝化甘油能夠擴張血管,并且把握住了應該的劑量。現在硝化甘油成為了緩解心絞痛的標準藥物。
三
鮑爾·海斯德是美國一位研究蛇毒的科學家。他得知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萬人被毒蛇咬死,就決心研究出一種抗毒藥。他想患過天花的人,會產生免疫力,而讓毒蛇咬后能不能也產生免疫力呢?從此他就在自己身上注射微量的毒蛇腺體,并逐漸加大劑量與毒性。每注射一次,他都要大病一場。各種蛇的蛇毒成分不同,作用方式也不同,每注射一種新的蛇毒,原來的抗毒物質不能勝任,又要經受一種新的抗毒物質折磨。他身上先后注射過28種蛇毒,自身產生了抗毒性,眼鏡王蛇、印度藍蛇、澳洲虎蛇都咬過他,但每次他都從死神身邊逃了回來,藍蛇的毒性極大,海斯德是世界上惟一被藍蛇咬過而活著的人。他一共被毒蛇咬過130次,每次都安然無恙。海斯德對自己血液中的抗毒物質進行分析,試制出一些抗蛇毒的藥物,已救治了數萬名被毒蛇咬傷的人。
四
一百多年前,美國醫生克勞德·巴羅為了對血吸蟲有所了解,親自吞了一些血吸蟲幼蟲,但是發現并沒有排出成蟲。他認為是胃液破壞了幼蟲,于是服用了大量的小蘇打中和消化液,然后再服用幼蟲,最后發現排出成蟲。接下來,巴羅嘗試了服用成蟲,并加大劑量。這次他的運氣就沒那么好了,開始的三個月,頭暈目眩,食欲下降。后來陰囊出血,并在血中發現了有血吸蟲卵,原來血吸蟲能將卵排入到血液之中。為了檢測皮膚里是否有蟲子,巴羅切下一塊皮,并拒絕麻醉——害怕麻醉影響寄生蟲。最終發現皮下也有很多血吸蟲。再后來,便血,膀胱日日夜夜巨疼不止,每20分鐘就得排尿。體溫一直在40度左右,并且無法行動。巴羅每天排出12000顆蟲卵,血尿不止。最后巴羅不得不接受治療——銻治療。這種重金屬毒性極大,注射到血液里毒死寄生蟲,同時對身體器官造成極大危害。巴羅以心律失常、急性血管塌陷、心臟受損為代價終于解決了體內的蟲子。
五
導管插入術現在是一項普遍的醫療措施,但在上個世紀初期,在心臟中插入東西被認為是致命的。1929年,德國醫生韋爾納·福斯曼開始嘗試在臨床上進行心導管檢查的可能性,并首先在自己身上進行了人類首例心導管檢查術。在同事的協助下,福斯曼將一根導管從自己的左肘前靜脈插入,借助熒光屏監視,將導管送入了右心房,并拍下了醫學史上第一張心導管胸片。從此拉開了人類心導管檢查的序幕。之后,他相繼九次在自己身上進行右心導管術。這種行為在他所在的醫院引起了轟動,但是由于傳統觀念的強烈譴責,他被迫離開醫院,并中斷了工作。但他的勇敢使他在1956年獲得諾貝爾獎。
六
1979年4月,澳大利亞生物學家沃倫在一位胃炎病人的胃黏膜活體標本中,意外地發現了一條奇怪的藍線,他用高倍顯微鏡觀察發現有一種螺桿菌緊貼著胃上皮,有規律地存在于黏膜細胞層的表面及黏液層下面。沃倫意識到,這種細菌和慢性胃炎的發病可能有密切關系。為了獲得幽門螺桿菌引發胃炎的證據,生物學家馬歇爾和一位名叫莫里斯的醫生,自愿進行人體試驗。1982年他們在服食培養的細菌后,都發生了胃炎。結果馬歇爾大病了一場,莫里斯費了好幾年的時間才治好。這種大無畏的獻身精神,使螺桿菌引發胃炎的機理得以探明,沃倫和馬歇爾因此獲得2005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諾獎評委會主席約蘭·漢松感慨而言:“今天的諾貝爾獎可以說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換來的!”
(何建偉薦自《當代青年》)
責編:水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