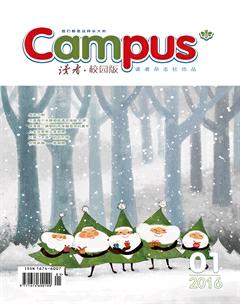你會長大,我會回來
路明
小時候,鄰居家有個大我兩三歲的男孩,我叫他小哥哥。在我眼中,小哥哥見多識廣,簡直是無所不知。
有一天,小哥哥給我講了一個機器人打架的故事。聽著聽著,我有點迷糊了。我問他:“什么是時間機器?什么叫核戰爭?”
小哥哥說:“你別管了,講了你也不懂。反正就是兩個機器人。一個長得跟人一樣,是好的;另一個可以變形,是壞的。”
我問:“是好機器人厲害,還是壞機器人厲害?”
小哥哥想了想,說:“壞機器人更厲害一點,但好機器人塊頭更大,更威風。”
每到關鍵的地方,小哥哥就不講了,對我說:“天太熱,我口渴。”
還不知道機器人打架誰輸誰贏呢,真是急死人了。
我捧出小豬儲蓄罐,倒出3角錢,然后飛奔出門,買回兩根冰棒。小哥哥剝開冰棒紙,高興地舔一口,繼續說下去。
我10歲那年,小哥哥家橫遭變故,他跟著家人離開了小鎮。臨走的時候,我問小哥哥:“還能再見到你嗎?”
小哥哥說:“I will be back.”我問他:“這是什么意思?”他說:“我會回來的。”
從此,我再沒見過他。
幾年后,小鎮的文化館附近開了一家錄像廳,我常在周末的下午偷偷跑去看錄像。但大人說:“好學生不會去那種地方。”
十幾平方米的房間,大白天也拉著窗簾。房間里擺著一臺舊彩色電視機、一臺二手索尼錄像機和十幾條板凳,地上到處是煙頭和瓜子殼。
有一回,我居然看到了會變形的液體機器人和威風凜凜的大塊頭機器人,跟小哥哥講的一模一樣。
飛車、重機槍、直升機、核爆,兩個機器人貼身肉搏,上天入地,誰也打不死誰。
我在黑暗中張大嘴巴,心突突地跳個不停,我口干舌燥、血脈賁張,激素含量一定是爆表了。
忘不了最后的畫面,大塊頭機器人把自己沉入沸騰的鐵水之中,此時我身邊的小流氓已泣不成聲。
散場后,我問老板這部片子叫什么名字。老板不耐煩地說:“《終結者2》,香港人叫《魔鬼終結者》。”
走出錄像廳,明晃晃的陽光照得人恍惚。我突然很想念那個每年夏天都來我家給我講故事、騙我冰棒吃的小哥哥。
后來我也離開了小鎮,生活按部就班,波瀾不驚。
北京奧運會那年,我喜歡上了一個姑娘。她應該也有點喜歡我吧,雖然誰都沒有說。
姑娘對我說:“你一直說《終結者2》好看,我還沒看過。你去買一張碟,陪我在電腦上看吧。”
那時我在準備一個光伏電站項目,需要去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考察一段時間。臨走的前一天,我去姑娘家道別,順便帶了那張碟。
看完電影,我發現她的臉色很奇怪,兩只手死死地揪著衣角,像在竭力控制著什么。
一滴淚流下臉頰,又是一滴。她開始嗷嗷地哭。
我驚呆了,從沒見過一個外表文靜的姑娘會這樣哭。本能告訴我,該出手了。
我抱住了她。她徒勞地掙扎了幾下,鼻涕、眼淚糊了我一脖子。
第二天,她沒來送我,說受不了這樣的離別。
15天后,在巴顏喀拉山的風雪之夜,我差一點就化作一面經幡。我在-15℃的黑暗中瑟縮著,感覺熱量在一點一點地流逝,于是努力回想那些讓我溫暖的名字以及她的面容。
后來我問她:“你那天為什么哭?”她說:“看到T800被鐵水吞噬,我害怕你也會像這樣消逝在風雪中。”
有人告訴我:“《終結者5》拍得很爛,施瓦辛格老了,別看了。”
去看一部大家都說好的電影,是跟風。
去看一部大家都說爛的電影,是情懷。
所謂“情懷”,或許不過是:曾經好過一場,不知你忘沒忘,總之我還記得。
在屏幕上,我又見到了施瓦辛格。曾經的健美先生,如今已肌肉松弛、皺紋橫生。那張被地心引力拉扯的臉,寫滿了衰老和不甘。
健身或許是最虛妄的運動,再強健的肌肉,也得交給歲月去摧毀。
我看著他一次又一次向比自己更強壯、更先進的機器人發起沖鋒,被狠狠地摔在地上,爬起來,再被摔。
“我老了,但并不過時。”施瓦辛格說。
我在健身房,多少次肌肉行將崩潰,快堅持不下去時,我告訴自己:“施瓦辛格都快70歲了,還在練。”
就像跑步跑得精疲力竭的時候,我在心里默念:“科比已經恢復訓練了。”
就像幾年前看《變形金剛1》,當第一聲汽車人變形的聲音傳來時,黑暗中的我忍不住熱淚盈眶。
有時覺得,“如約而至”是個多么美好的詞,等得很苦,卻從不辜負。
謝謝你們,老男人,一直燃燒到現在。
謝謝你們,我兒時的英雄,穿過漫長的時光,來到我的身邊。
謝謝你,T800。你總是說“I will be back”,然后每次都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