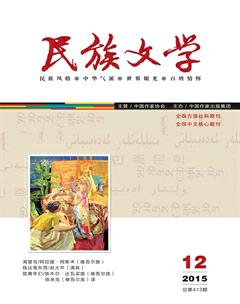多元文化中草原書寫的身份焦慮
王妍
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的轉型伴之以經濟結構的“突變”,以及社會文化結構的“突轉”。這對于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學而言也意味著某種深刻的或者說根本性的變革:西方文明對東方文明、城市文明對鄉村文明、主流文化對民族邊緣話語都產生著巨大沖擊,這是一次由多元文化取代一元文化,由現代文明顛覆傳統文明的一種徹底的變革。雖然,這種變革也并非一蹴而就,但多元文化所代表的城市文化、現代文明、西方話語等多重意蘊逐步滲透到草原文化之中卻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多元文化、經濟結構處處顯露出文化優勢、文化特權之時,草原文化呈現的是散落一地的精神殘骸:邊緣、互涉、斷裂、焦慮乃至缺席屢屢出現在草原文學的書寫之中。因此,與其說草原文學作家關注的是經濟現象本身,不如說他們更關注現代化進程中邊緣民族的精神困境。如何在多元文化中,既保持草原文明發展進步,又保持草原民族的獨特民族精神,避免被主流文化同化,是擺在草原文學作家面前至關重要的精神生態問題。
在日益繁榮的經濟大潮之中,身份的焦慮這個業已困擾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在中國也日益凸顯。隨著現代性車輪的滾滾前行,浩莽草原也無法保持遺世獨立的高潔姿態。阿來一直以一種動態的眼光對嘉絨藏區進行俯瞰式的文化記錄,他把目光放在了曾經安寧,卻在多元文化的侵襲之下蠢蠢欲動的鄉村。在他寫于1982年的作品《紅蘋果,金蘋果……》中,就部分展示了尚未完全萌動的鄉村景象。20世紀80年代初,文學主流還沉浸在不可遏抑的“現代性沖動”之中,這時諸多的老一輩草原民族作家在積極擁抱時代大潮,并努力將個體的民族身體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雖然,阿來的寫作也沒能脫離“文革”結束之初公式化、口號化尚未從文學中褪盡的特征,但是在文本的縫隙之中,卻展示民族認同和身份焦慮的端倪。作者用頭發“不是……而是……”;“才不穿”這樣孩子氣的語氣描述少女澤瑪姬對城鄉、民族、文化的對比與選擇。這個敏感又自強、自尊又自卑的藏族農民少女,在某種意味上成為了20世紀80年代之初的草原民族身份焦慮的縮影,誠然,結尾空泛口號展示了頗具浪漫理想的未來,但自我身份的認同是建立在“他者”(尤其是有優勢的文明)的認同之上。這篇“清新的短篇”[1] 有著缺乏現實說服力的貧弱與迷茫。但那種邊界民族敏感、踟躇、孤立、流浪的感覺卻是如此的深刻動人。在他的另一個短篇《獵鹿人的故事》中,主人公身份的焦慮被書寫得壯烈而兇猛。桑蒂因為女友在漢族家庭中跟他分手,并罵他是“蠻子”,一怒之下割掉了女友的鼻子。在這種血性的爆發背后,隱藏著多重“他者”的認同危機:民族認同(桑蒂是藏族,女友是漢族)、文化認同(桑蒂是“藏蠻子”,女友是“文明人”)、城鄉認同(桑蒂家在鄉村,女友家在城市)的多重危機。藏邊青年桑蒂在愛情中的激越與苦痛,也可以理解為相對弱小的民族/文明面對主流/強大文明時的無所適從與脆弱。阿來在遵循個體生命存在體驗的基礎上,揭示多元文化之中民族精神的存在困境。
然而,這種表達在當時單薄而微弱,很快就被淹沒在“現代敘事”的洪流之中,但焦慮作為現代人普遍面臨的難題在阿來日后的書寫中得以延續。無論我們承認與否,伴隨著多元文化和現代性進程,草原民族傳統價值的斷裂與被顛覆都是不爭的事實,草原民族身份的焦慮也日益凸顯。文化定位、地理位置、民族生態的懸殊都會導致生命個體的焦慮。在《芙美,通向城市的道路》之中,阿來并沒有正面書寫城鄉、民族、文明之間的對照和沖突。但芙美在奔向城市道路中的那種失根的懸浮感,以及為擺脫鄉村/民族命運的奮不顧身,都展示了消費世紀對草原民族的異化作用,“商品的邏輯得到了普及,如今不僅支配著勞動進程和物質產品,而且支配著整個文化、性欲、人際關系,以至個體的幻想和沖動。”[2]無疑,芙美是作者夢想系列的一員,只是她的夢想很實際,也很卑微:擺脫貧困、落后的鄉村生活,被城市接納,而且身份的焦慮時刻困擾著她。誠然,在阿來筆下也不乏美麗的鄉村烏托邦想象,但由于文明進程不同,相較之落后、弱小民族面對撲面而來的多元文化時,那種理性審視、復雜痛楚以及無可奈何,卻是如此的真切動人。“我們講漢語的時候,是聆聽,是學習,漢語所代表的……是城鎮、是官方、是科學,是一切新奇而強大的東西”[3]。在阿來的筆下,有完全漢族做派的混血(藏漢)表弟瞿增富(《電話》),在部隊中把自己名字改成漢族名字的王成(《孽緣》),迷失在權力認同之中的賢巴(《遙遠的溫泉》)……他們在多重文化互涉中丟掉自己的民族之根。我們也不難在閱讀中發現,阿來對現代/城市文明的保留乃至懷疑的態度,在他看來城市只是“很貼近的遙遠”,失去了民族根脈的“芙美們”只能在“虛空中飄蕩”。他在《夢魘》中用意識流的手法深邃地展示了奔向城市后的道路,在似夢如幻的氛圍之中那種在城市文明中無處藏身又無處逃遁的焦灼與壓迫有著切膚的質感。可以說,阿來獨特的漢藏“文化流浪”的經歷,使得他對于漂泊、孤獨與身份的焦慮有著更為深刻而切進的認識與表達。
時代在進步,民族也在發展,甚至在自覺不自覺中被同化,當民族抑或農民身份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蒙昧、落后與低人一等時,身份的焦慮由此而生。達斡爾族女作家薩娜也曾用“力不從心”、“述說的困惑”、“寂寞無音”[4]來敘述保有民族純粹時的惶惑無力。事實上,全球多元的語境之下,民族/鄉土的劣勢日益凸顯,而鄉土中國對現代文明的想象,就是“到城里去”。 劉慶邦曾以《到城里去》為題,書寫了鄉村進入城市的漫漫崎嶇之路,及文化沖突所誘發的身份焦慮。遺憾的是,鄉村對于城市而言是底層的“他者”身份,而民族身份自我認同又進一步加重了這種隔膜,城市/現代文明以高蹈的姿態,在精神上摧毀了草原民族的“自在”的超穩定文化結構的同時,卻不會完全接納它。阿來在《空山》中寫道“無論是在外來的游客眼中,還是當地人的心目中,漢與藏,已經不是血緣的問題,而是身份的問題。”[5]在“我”與城市的女博士的相處之中,女博士“沒來由的優越感”[6]彰顯著民族認同的潛在不平等,女博士代表著先進文明對所謂落后文明的態度:好奇卻不接納。而林軍的身份確認則更進一步地說出了身份多重關聯域:漢藏、血統、城鄉。即便如此,阿來依然在《血脈》中堅守著民族身份的自我確認:“父親踱到我面前……問:‘你以為你是藏族,是嗎?‘我是。‘你真的想是?”在這段貌似哲學論辯的敘述中,顯示作者對純潔民族身份的堅守。阿來自覺地保存關乎民族回憶與情感的本真記憶,保持本民族原始的生命狀態,來對抗“影響的焦慮”。
在阿來的創作之中,既有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問詢,對現代文明的向往;也有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堅定守望。我們發現,阿來并沒有回避身份認同的焦慮、民族精神的掙扎、現代性的失重等問題,但他卻能在書寫處于劣勢的民族的艱難處境之時,沒有焦慮的愁苦、控訴命運的不平,而是用立足于民族個體生命的生存經驗,透明而自然地面對和書寫似乎本該如此的生活,來應對文化的挑戰和身份的焦慮。阿來的作品滲透著濃郁的人文關懷,流淌著夕陽的光芒,他的書寫不是熾熱,而是溫暖。
責任編輯 安殿榮
注釋:
[1]阿來:《幸運與遺憾》,《民族文學》,1991年
第1期。
[2][法]讓·波德里亞著;劉成富,全志鋼 譯:
《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第225頁。
[3]阿來:《漢語: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語言》,
《當代文壇》,2006年第1期。
[4]薩娜:《沒有回音的訴說》,《作家》,2002
年第3期。
[5][6]阿來著:《空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570頁,第6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