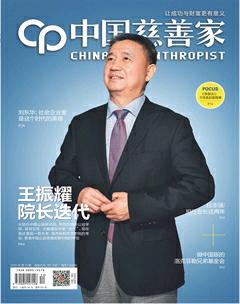創業者基因決定著企業的生存與傳承
甘德安
隱藏在生命里的基因是決定個體差別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決定家族企業傳承的本質是否也是企業的基因?
家族企業傳承最多的話題是,第一代傳承到第二代只有30%,第二代傳承到第三代不過13%,而再傳承下去不過3%。人們普遍認為,家族企業傳承“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似乎只糾結在代際之間。其實,從企業基因理論的角度看傳承,“富不過三代”的家企傳承命運在第一代的創業者身上就基本決定。我們借助東星航空破產的案例,看創業者是怎樣把自身的雄心萬丈或狂妄自大作為基因注入到自身創辦的企業中,并決定家企代際傳承的成功與失敗的。
媒體報道,在過去的數年間,東星創始人儼然是中國版的理查德·布蘭森(維珍航空創始人)。東星航空做大旅行社業務后,其創始人非常渴望能控制航班來掌握旅游業的主動權。在政府的力挺下,東星很快拿到了夢寐以求的航空牌照。
如同當今許多野蠻成長的創業者,有錢就任性,沒有把國家發展的機遇與政府的扶持,看成是時代或者上帝賦予的機遇,反而更顯示出迫不及待的瘋狂與不可一世的狂妄一樣,東星亦未能擺脫這一運行軌跡。當一般民營航空公司都采用租賃方式引入1到2架飛機時,東星航空則一舉引入20架飛機。2000年前的劉邦都知道,“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但東星航空開始與飛機租賃方進行談判時卻沒有邀請航空專業人士參與,視專家如糞土,結果是談判時一頭霧水,并主動簽訂了一個內行欺負外行的合同。
按生物遺傳學的說法,隱藏在生命里的基因是決定個體差別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決定家企傳承的本質是否也是企業的基因?企業基因理論認為,企業基因是決定企業長成形態與成長的內在的根本性要素。企業基因的核心是創業者的DNA,創業者的DNA決定了企業戰略、行為與結果,也決定了企業的核心價值觀。比如說淘寶的江湖氣息,Facebook的校園風格,Google的工程師文化等等。
其實,一個公司的基因早在它最初的18個月就被決定了,此后公司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改變。如果DNA是對的,它就是一塊金子;如果不對,就毀滅。紅杉風投認為一個公司的基因在創辦的一個月內就定型了,這也許有些夸張,但是一個成型的公司改變基因的可能卻非常小。
吳軍博士在《浪潮之巔》一書中專門撰寫基因決定定理。他指出,改變公司的基因和改變人的基因一樣困難,可以看到一個公司的基因幾乎決定了它轉型的失敗是必然的,成功反而是偶然的。他的結論是,一個在某個領域特別成功的大公司一定已經被優化得非常適應這個市場,它的文化、做事方式、商業模式、市場定位等等已經非常適應,這使得該公司獲得成功的內在因素會漸漸地、深深地植入該公司,這就是公司的基因。當這個公司在海外發展分公司時,它首先會將這一基因帶到新的地方,克隆出一個新的公司。微軟在中國的分公司一定還是微軟的風格,中國的谷歌一定繼承了 Google 的文化。同時,它們又都像美國公司,而不是日本公司。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曼弗雷德寫了一本我們企業家不是十分熱心閱讀的書:《至高無上的囚徒》。他指出,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精英的階層之一,企業家正越來越成為社會注目的中心,然而,上帝之手在賦予他們名譽、財富和事業的同時,也順手拿走了阻擋精神洪水的閘門,讓他們在運籌帷幄的同時,也成為自我心理障礙的囚徒。
曼弗雷德指出,創業者的行為都受“向上意志”的支配,因此羨慕別人、勝過別人、征服別人等行為都是追求優越的人格表現。在追求優越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兩種結果:既可能保持向上的動力,激勵人去追求更大的成功;也可能由于耽于追求自己個人的優越,而忽略他人和社會的需要,變得驕傲、專橫、虛榮自大、妄自尊大。
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創業者從不被社會接受和認可,到成為受人尊重的財富擁有者,他們再也沒有以前的自卑,取而代之的則是自豪和自傲。但是,過猶不及,迅速的拔高也讓他們陷入了過度的自戀之中,造神運動、企業英雄主義、輕度妄想癥和賭徒心理均在他們身上得以呈現。
看看近40年來如流星一般隕落的企業,哪個的利潤不是曾經幾十倍、幾百倍地增長,哪個沒有上演過侏儒變巨人的神話?可就在他們無節制追逐利潤的時候,企業危機四起,陷入困境。這在東星航空的毀滅過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得到展現。
當時的東星航空掌門人最終要實現的就是打通旅行社、酒店、景區、旅游車隊和航空業,創造一種全價值鏈條的商業模式,進而引入戰略投資者做大上市,迅速完成資本積累。這符合野蠻成長的創業者的本性,穩扎穩打做實業并不符合他們張狂的性格。
曼弗雷德指出,有20%的人由于經歷了艱苦的童年,在缺乏關注中長大,或是太嬌生慣養,從而無法將內心的自我形象與外部真實世界相聯系。當他們進入成年,就很難保持穩定的自我意識,可能一生都在追求被人欣賞和尊重的感覺,他們決心要證明自己的價值,形成自戀型人格特征。
東星航空的創立者對于聲名乃至財富的追逐或可以解釋為其對貧困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也有對極致成功的終極欲望、對軍隊式忠誠服從的向往以及對建立領袖般個人崇拜的渴求。當東星航空2006年突然名聲大噪時,掌門人的書架上盡是《總裁言論》《關注東星》這類小冊子,其樂于把這些印著“內部資料,嚴禁外傳”字樣的小冊子送給前來拜訪的客戶或自己的下屬。2006年,當他以20億元身價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70位時,他向外界宣稱:福布斯把我低估了。或許這不過是揶揄、幽默,但卻讓人看到其背后的過分自戀。
可見,企業不過是創業者自我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有什么樣的創業者,就有什么樣的企業。經營企業,本質上是經營自我。如果“自我”出了問題,無論采取什么辦法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創業成功外求是迷、內求是悟。創業者欲走出迷局,獲得成功,首先就要從自我修煉開始,保持謙卑之心,把謙卑之心作為企業的基因沉淀并傳承下去,這樣才能走出失敗、邁向輝煌。
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創業者身上都具有一種特質,即謙卑。有謙卑之心,才能自省與求索,才能自知與自變。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些巴西人致信給美國的多位折扣零售連鎖店的首席執行官,希望向他們取經,最后,僅有一人和他們見了面。見面后,此人不停地向他們詢問關于在巴西和拉美開展零售業的情況,甚至在廚房洗碗碟的時候還在咨詢。巴西人后來發現,這個人原來就是沃爾瑪的創始人山姆·沃爾頓。
猶太人有格言:你需要在口袋里經常放兩張字條,一張寫的是“我只是一粒塵埃”,另一張寫的是“世界為我而造”。對中國創業者來說,他們不缺精進之心、戰斗之心,但缺謙卑之心,或者說“初心”。這個初心就是謙卑之心、一顆空的心、一顆準備去接受的心、一顆虛懷若谷的心。
謙卑之心就是能用上帝的眼光或者說用浩瀚的宇宙與綿綿不斷的歷史長河觀看待自己及自己創辦的企業。成功的創業者到了一定階段,一定是異常謙卑低調,企業做得越大,越是修身顧忌,日本、德國、美國的創業者莫不如此。
宋厚亮先生在《告別土豪:中國慈善新時代》一書中談到采訪黃怒波時,黃怒波說,在德國,他學到這個民族的內斂、不張揚。以企業家為例,德國的一些古堡、教堂,都是企業家家族在捐贈維修,但他們并不會大肆宣揚。與他們交流時,黃怒波看到的是紳士做派、是謙和。
不把自己看得太重,其實是一種修養,一種風度,一種高尚的境界,一種達觀的處世姿態,是心態上的一種成熟。用這種心態做人,可以使自己更健康,更大度;用這種心態去創業,才可能把成熟的心態轉化成企業健康的基因并使其得以傳承。為了讓自己創辦的企業生存與發展,為了讓自己的家族企業傳承過三代,為了讓自己創辦的家族企業基業長青,首先就應該在創辦的企業里注入進取與謙卑的基因,而不是冒進與狂妄。
企業基因決定著企業的發展與傳承,但基因也是可以演變與突變的。基因突變也是一種普遍的自然現象。東星航空的締造者與毀滅者現在已開始新一輪創業,應該說,現在是中國歷史上創業的最好時代,政府創業環境也在不斷改善,特別是李克強總理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更體現政府為創業者服務的決心與態度。如果創業者把謙卑與進取的基因注入新創的企業,那么,神話可以再現,企業可以傳承。從巨人到盛大的史玉柱與從紅塔山到褚橙的褚時健是我們共同的榜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