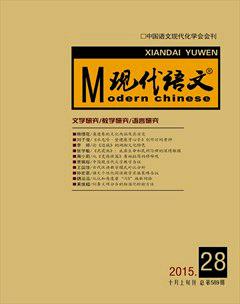論《邊城》的湖湘文化特色
摘 ?要:《邊城》是沈從文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上奏響的一曲田園牧歌,其淡雅的風格、清婉的筆調、纏綿堅定的愛情和純凈臻美的山水,使得多年以后,湖南茶峒的人仍覺得自己還生活在沈從文的小說里。湖湘文化是誕生在湖湘大地上獨具特色的鄉土地域文化,沈從文作為湘西世界的締造者,其小說在地域風情、道德執守和哲學品質上無疑都打上了深深的湖湘文化烙印。
關鍵詞:《邊城》 ?湖湘文化 ?特色
關于湖湘文化的界定,學界爭議頗多,其中最為學術界認可的是:湖湘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起源于戰國時期的楚文化,近代湖湘文化源起于古代湘楚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特征、相對穩定并有傳承關系的湖湘地域范圍之內的文化形態,湖湘文化的內涵在學界歷來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湖湘文化特指近世湖湘文化,即濫觴于南宋時期以王夫之為代表的湖湘學派及其文化現象;廣義的湖湘文化指濫觴于先秦周楚文化并綿延至今的湘楚民眾在生產與生活實踐中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屈原的詩歌藝術、馬王堆的歷史文物等都具有鮮明的楚文化特征,及至南北朝、唐宋,特別歷經宋、元、明的幾次朝代更迭和大規模移民,湖湘士民在人口、習俗、風尚、思想觀念上均發生過重大變化,歷朝民眾都在本土特有的地域生活實境中,組合、建構出過不同內質的湖湘文化。近現代文化大變革中,湖湘民眾與湖南境內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共同締造了新的湖湘文化。湖湘飲食嗜辣,民眾性情也較暴烈,湖湘文化也具有不喜約束、正義感強、勇猛尚武、淳樸重義等特點,表現為在生活中比較重視現世生活,不好高騖遠。
沈從文出生的湘西,地屬武陵山脈,在歷史上屬于“楚南”。楚南之地歷來民風彪悍、勇武蠻橫且重巫蠱鬼神,生活中又追求本性自由。沈從文少年時有行伍經歷,因而性情中耿直和沖淡相協,其文學作品也多呈現不喜約束的精神追求。尤其是小說中多充滿原始生命的神秘感與盲目感。湘西作為湖湘文化的一個根基和承載體,用具有特殊地域特征的風俗點綴著湖湘文化的世界。沈從文立志成為湘西生活的敘述者和歌者,將其歸為京派小說家是就其文學個性、創作風格和敘述藝術而言,略去了其主題與人物的地域性特點。北京大學學者曹文軒教授認為,在中國眾多的地域性作家中,沈從文是其中的一個經典。他的代表性作品全部都源自湘西——一個湖湘文化浸潤的地方。《邊城》是其中尤為特出的一篇,沈從文在如詩的行文中用沖淡的心態,寫滿了濃郁的湖湘地域風情、哲學品質和道德執守,也表現了沈從文念念心系的湖湘哲學觀照。
一、湖湘文化的地域風情
現當代文學史上孫犁、汪曾祺都是寫地域生活情態美的高手。孫犁寫的是勞動人民,因與抗日戰爭相關而染上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寫的是市井小民,有些過度生活化,小說和散文中敘寫的生活景物與人情美都有種奇特的色彩。沈從文的與眾不同在于其獨立自守的一份恬靜與自然。他對山村生活的情有獨鐘。《邊城》寫的亦是山村的淡雅,也是用如詩如水的文字描繪了極具湖湘文化特色的地域風情。
湖湘自然景觀中多水,三江四水的地理風貌孕育了別具一格的湖湘文化。追求浪漫與自由是湖湘文化之魂,從幾千年前的楚文化承襲而來,至今未絕。從屈子汨羅江畔行吟至今,湖湘文化浸潤的文學無不極具浪漫情懷。可隨物賦形又包容萬物的水,其實也象征著一種無拘無束極其自然的生命狀態。沈從文作品中的水元素,已經有諸多學人大加研究。沈從文曾在《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一文中說:“我學會用小小的腦子去思索一切,全虧得是水。我對于宇宙認識得深一點,也虧得是水。”《邊城》也是水邊的故事,水上人的生活,水上人的言語,水上人的感情和追求。白河、沅水、小溪、繩渡,這“邊城”就是一個水的世界。水是柔的,柔也是女人與水共有的特性,更是一種最高貴、最雅致的情致。《三三》中城里來的先生和女人被水邊長大的靈秀女子三三身上的那種無法言說的神韻所深深懾服。因為有了水的滋養,便有了不急不躁、不溫不火的一份活潑的靜雅,生活也多是水樣靜美。《邊城》中船夫、少女、古渡、白塔、斜陽,凝成一幅亙古的邊城山水畫,更是一種淳樸的純美生活圖景。
《邊城》中的人文景觀也多具湖湘文化深意。白塔是《邊城》中一個令人印象頗為深刻的人文景觀。白塔是佛教中常見的物象。佛教崇尚靜心與淡泊,與湖湘文化中推崇自由平淡的觀念相契合。沈從文素來重視人的生存與生命尊嚴,這也與佛教素來尊重生命的本真相契和。因而這白塔的意象直接指向人的生命本質。船夫死時,白塔突然坍塌。這平日里可有可無的白塔突然變得重要了。人們覺得白塔與風水有關,大家就都捐了些錢在冬天修好了,更多的是表明大家依然認可這渡船的所屬和存在,依然關心這需要依靠渡船生存下去的人。在小說中白塔驟然成為生命存亡的象征,人們通過尊崇白塔來表達對翠翠失去祖父后生活的扶持,樸素的鄉民用一種淡然無痕的方式表達著對生命的尊重。
湖湘民俗活動往往文化涵義豐富。在湖湘飲食民俗中,“吃”具有豐富的社會意義,也是人們社交的重要手段之一。比如去哪家做客,看菜式的多寡和桌席排位,往往能看出主人對客人的態度。《邊城》描寫端午節的龍舟競渡時,團總女兒被安排在順順家“當中窗口”最好的地方,這便讓所有的鄉民都一看便知,順順家對團總女兒身份的認可,甚至是婚姻關系的承諾。而儺送將翠翠請到自家堂屋里最好的位置與團總女兒并排坐下,也是用行動表明了自己對翠翠的態度和承諾。這也才有了翠翠知道了儺送對她的心意而產生牽掛。在小說中民俗活動不僅僅是純風俗,它們既是人物的生活環境、作品的情調氛圍,也是故事情節的推手。《邊城》中,民俗活動爭渡是情節的銜接,繩渡是翠翠的生活環境,而走車路和馬路則是愛情故事的氛圍渲染。民俗的意蘊也常令故事情節錯落多姿,文化氣息濃郁厚重。端午節的爭渡就是湖湘民俗文化中爭先與霸蠻風氣的集中表現。湖南湘西民俗中的“走車路”請保山是請媒人提親,婚前要經過六禮或八禮。而若是自由戀愛,則可以采取“走馬路”用唱歌的方式自行定親,婚約意識也簡便自由。這樣的婚俗文化是湘西開化精神和浪漫情致所孕成。
沈從文的語言具有非凡的洞察力,這使其小說具有外在語言美和內在人性美。方言不僅是豐富生動的口頭語匯,而且富有深厚的地域文化內涵。沈從文在《邊城》中也點綴了幾句湖南方言,寫翠翠在爺爺小憩時牽船渡人用了“溜刷在行”一詞,就是一種自然的熟悉,往往用來形容人做事又快又好,看著令人舒服。這在湖湘文化中是一種很高的稱贊。這方言在清新淡雅和形象生動之外,也平添了活潑的生活氣息和民間的質樸與淳厚,能充分表現人物性情的張力。
二、湖湘文化的道德執守
《邊城》里的人們重情輕生、重義輕利、守信自約,“凡事只求個心安理得”,這是湖湘文化中寶貴的道德執守。《邊城》是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其中還埋藏了翠翠母親的故事,在邊城里演繹得美麗而憂傷、純凈而古樸。在哀怨糾纏的三角戀里,翠翠重走了母親的戀愛之路。當多年后的愛情故事重演時,天保遠走水路遇難,儺送不堪負疚,也駕舟遠行。一個沒有結局的尾聲也凝滯了永恒的等待和山水,將神圣的愛情襯托得自然純美。故事中雖然沒有心情激蕩的批判與爭論,但沉靜的道德氛圍潛伏在故事情節和人物言行中,有一種堅定的道德力量使人長久地為之感動和震撼。中國傳統的善良、慷慨、誠信、助人等諸多道德行為歷來為邊城民眾所崇服,因此小說也自然帶有一種超越時空的感人力量。翠翠的父母因為婚姻與愛情不可兼得而雙雙殉情,翠翠為等待生死未卜的儺送堅守渡船,這種愛情的忠誠與執著也歷來是湘西人的道德準則。
小說中有明確的道德評判。《邊城》開頭的渡船,說是公家的,船夫便會將客人給的錢收齊還回去,有還不回去的便買了草煙送還,買了茶葉燒茶供路人取飲。這些行為凸顯了湖湘文化中重義輕利的本色。還有碾坊與渡船也是一種隱性的道德力量較量,即義與利的較量。儺送的愛情就是義與利之間的選擇。最終他選擇了渡船,是堅持義利取舍的標準,也是對湖湘文化中重義輕利傳統的精神堅守。在湘西,哪怕是妓女這樣的行當,也不僅經得住道德的考驗,而且也遵循義字先行的規范。《邊城》中寫到:“有些娼妓的熟客,錢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情義卻是十分重要的。”靠情義維系的那份看似淺薄的感情,因為湘西女子的守信自約而多了幾份溫暖。
三、湖湘文化的哲學品質
楚地及湖湘文化中最原始的“巫儺文化”很重視人生、關注生命與生活,又充滿幻想與激情,表現在人性中為浪漫、堅韌而大膽。湖湘文化因遠承楚文化的浪漫精神,形成了一種自在自為的生存態勢和追求自由的哲學稟賦。因而在沈從文小說中行云流水般的故事與文化,其實是湖湘大地上自由生存哲學的表現。在茶峒安靜的日子里,人事的紛雜是極少的。人們都埋頭于簡單的日子,滿足于當下的生活。《邊城》里也有商業和河街,是小城的商業中心和娛樂中心,在那里多是隨意交換的自由,少了許多經商得利的油滑與奸詐,也就少了許多錢財的煩擾和外物的拘束。船夫很熱誠地邀人喝酒,河街上很多鋪子的商人會送他粽子、紅棗與其他東西,以示對他看守渡口的謝意。
生活中的自由無拘也表現在感情上。湖湘文化中將婚戀看得很重。尤其在湘西等少數民族地區,更是追求自由戀愛,甚至將愛情看得重過生命。因為對青年男女來說,愛情是生命本能的需要,是性情的本真所在,若愛情與族規相違背,多是選擇用生命祭奠愛情。因此湘西地區多有趕歌會、歌節等節日來歌頌愛情,以歌交友。山歌既是任何場合通行的愛情試金石,也是頌揚愛情的最普遍形式,其中有很多頌揚忠貞愛情的故事。《邊城》中“走馬路”這種自由的婚俗文化也是湖湘文化哲學精神追求的現實呈現。
湖湘文化最明顯的霸蠻性情在沈從文筆下能流淌成一片靜與淡,實在是一個值得參詳的話題。這也許更多地與他不平凡的人生經歷相關,是鉛華洗盡、大悲大苦之后的心靈逃遁,還是看透人世滄桑、放下得失的超脫,我們不得而知。但沈從文看待湘西的人和事,一直是用一種無比溫和的目光,仿佛那里就是他心底里最柔軟的角落。為此他不惜用無數精美的語言和信來向張兆和描述他的“世外桃源”。對沈從文來說,湘西是他最鐘愛的故土,張兆和是他最鐘愛的人,他便用了二者的結合,將張兆和的影子映照在湘西的山水之間,合為一個他的“湘西世界”。他對最鐘愛的人與情用了最舒緩的方式慢慢敘說,一段從容,一份持握;一段平和,一份執守。
(本論文為武漢商學院職業人文素質教育研究所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胡光凡.湖湘文化與文學“湘軍”[J].岱宗學刊,1993,(3).
[2]劉玲,米華.湖湘文化研究綜述[J].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9,(7).
[3]蘭永平.論《邊城》的地方色彩[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10,(4).
[4]蔣偉.湖湘之水與湖湘文化[J].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12,(11).
[5]金蘭芬.鄉土文化中的人性美[J].無錫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3).
[6]丁平一.試論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J].求索,1998,(5).
[7]沈從文.沈從文文集[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
(李婷 ?武漢商學院人文教研室 ?430056)